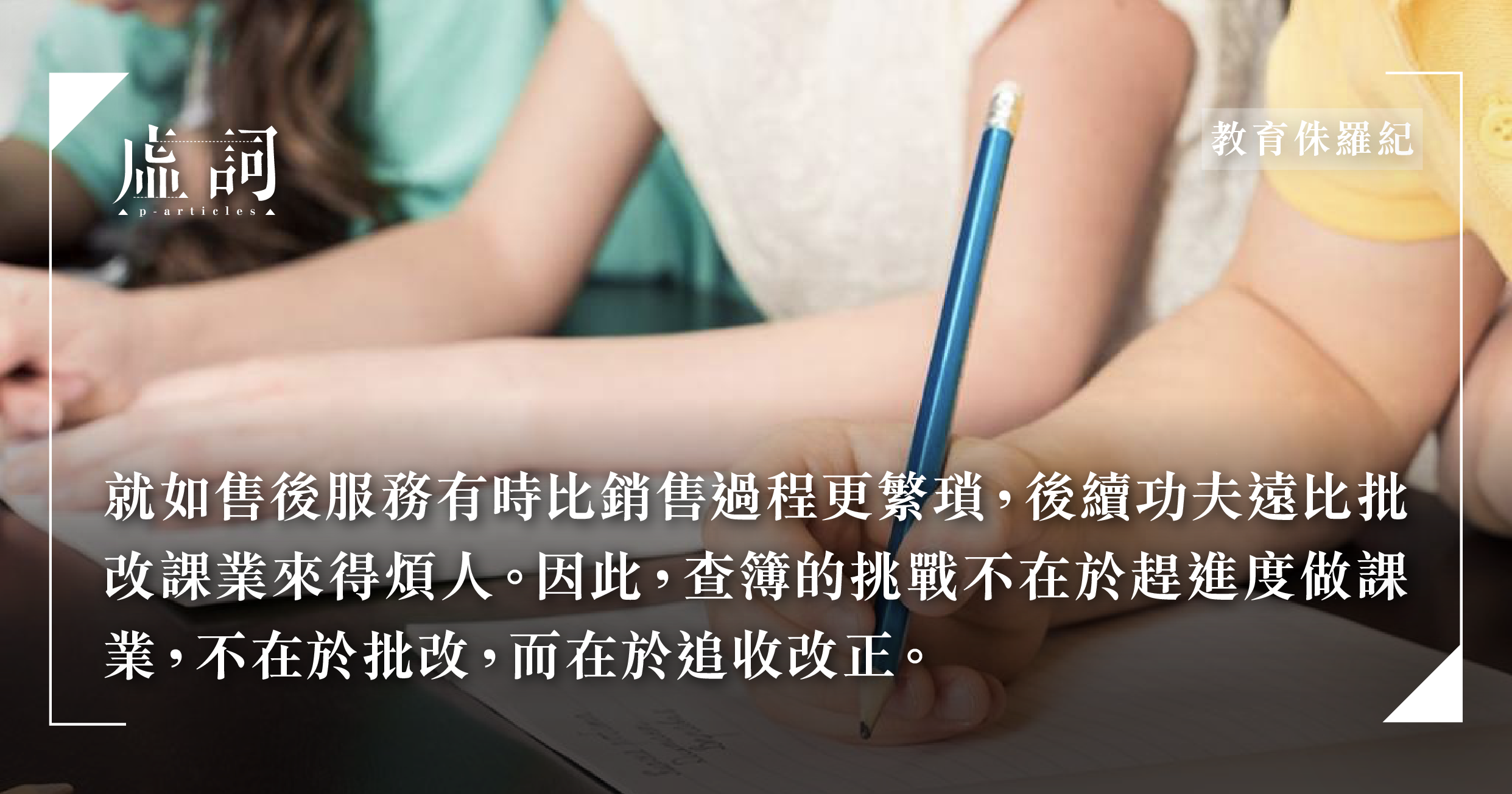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查簿
假如學生的噩夢是考試期,那麽,老師的噩夢是查簿期。
查簿是通過老師間的互相審查,保障每位同事的批改質素和教學進度良好。老師需要收齊足夠數量的習作,完成所有批改,然後呈交科主任審核。除了美術、音樂和家政等術科,大部分老師每學年都要經歷兩至三次查簿。
就如售後服務有時比銷售過程更繁瑣,後續功夫遠比批改課業來得煩人。因此,查簿的挑戰不在於趕進度做課業,不在於批改,而在於追收改正。為了確保學生從錯誤中學習,文章裏的錯別字、小測裏錯誤的題目均需逐一做改正,今天派發的習作,我一般要求學生第二天交改正。翌日早上,科長氣急敗壞地前來教員室向我匯報,同學中有幾位欠帶、欠做者,通常是幾位慣犯。無論怎樣予以懲罰,他們善忘的個性始終不變。
更重要的是,遞交了的改正不必然告一段落,我一天尚未過目,還不確定裏面藏著多少份渾水摸魚的。學生的改正總是甩漏甚多,改了第一頁又忘了第二頁,説好了配詞改正,總有人吝嗇筆墨,只把錯的字抄寫十次。改正的漏洞可謂層出不窮,害我消耗一張又一張的便利貼,狠狠蓋下通紅如血的「改正」印章。希望學生能從蓋章的力度,體察我的不耐煩,日後再不要閉著眼睛做改正。
除非課上能騰出時間讓這批學生即時重改,否則大多要拖至明天課上跟進,後天收回。在課時緊拙的情況下,課上做改正太奢侈,何況並非每位學生要重改,改正的多寡也不同,難以估算時間。可是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瞄向辦公桌上的小鐘,距離小息尚有五分鐘,我連忙放下手中工作,拿起需要重改的課業,趕到課室門外,靜待鐘聲響起,生擒這些學生,要求他們明天遞交改正,便不必拖至後天才收回。我甚至在腰間扣上麥克風,打算以聲量抵擋他們小息解放的噪音。走廊的風很猛,鐘聲響徹全校,鄰班學生紛紛湧出。然而,我班房門數分鐘後仍然緊閉,我有點焦躁,隔著門上的小窗子瞄進去,同事説得手舞足蹈,似乎未有停下來的意思,而小息只剩兩分鐘。我看這群學生白白喪失了小息,强行撈起他們也不人道,還是放學再來吧。
放學追改正也不順遂,總會碰上諸多不測,要麽老師未準時下課,要麽學生分組在不同教室上課,要麽學生去了禮堂聽講座,要麽完成體育課後更衣需時,緊鎖的大門困住一片漆黑。但我不能久候,因為課後仍有另一班學生找我補默。
老師到底什麽時候活得像高利貸,窮追不捨,追課業追改正像追討債務。高利貸尚且能耍無賴,淋紅油灑火水宣泄憤怒,老師卻只能好言相勸,將種種厭倦和不甘的情緒藏在心底。
查簿是噩夢,另一原因是遺失,情況在學期尾最後一次查簿尤其常見。九月開學時,我千叮萬囑地提醒,收來的課業需要統統放進一個文件夾,這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重要的依據,必須妥善保管一年,千萬不能丟失。學期尾查簿,需要收集全班學生的文件套,總有那麽一兩位神色平靜的學生,敲響教員室的門,召喚我,然後向我匯報:吳老師,我整個文件夾不見了。平靜的話掀起我心中洶湧的波濤。那怎麽辦呢?反倒是我問她。她默然不語。我讓她重寫幾篇文章,但我不會眉批了,畢竟已經批改過,而且打了分。她嗯嗯的點頭,依舊平靜地離去。
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查簿的準備功夫費時得很,過程倒是很快完成。收集好所需文件、填妥表格,然後把沉甸甸的批改成果捧起,搬到指定的場地,一周後就能收到科主任回饋的評鑒表。A4膠文件套色彩繽紛,裏面藏著的筆跡更是絢爛,厚厚的一曡很沉重,沉重得實在,讓我瞬間察覺到,曾手握紅筆批閲的文章,竟那麽多,原來已經走了那麽一段路。前行的路途,文件套持續摩挲我的前臂,心情因為得到進展性成果而感到愉悅。一不留神,文件套鋒利的角刮到我的手,白色的刮痕漸漸透紅,但我必須撐持著,到達收集點才能放下它。
畢竟,肩頭上的責任再重,我也不能輕易將其卸下或委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