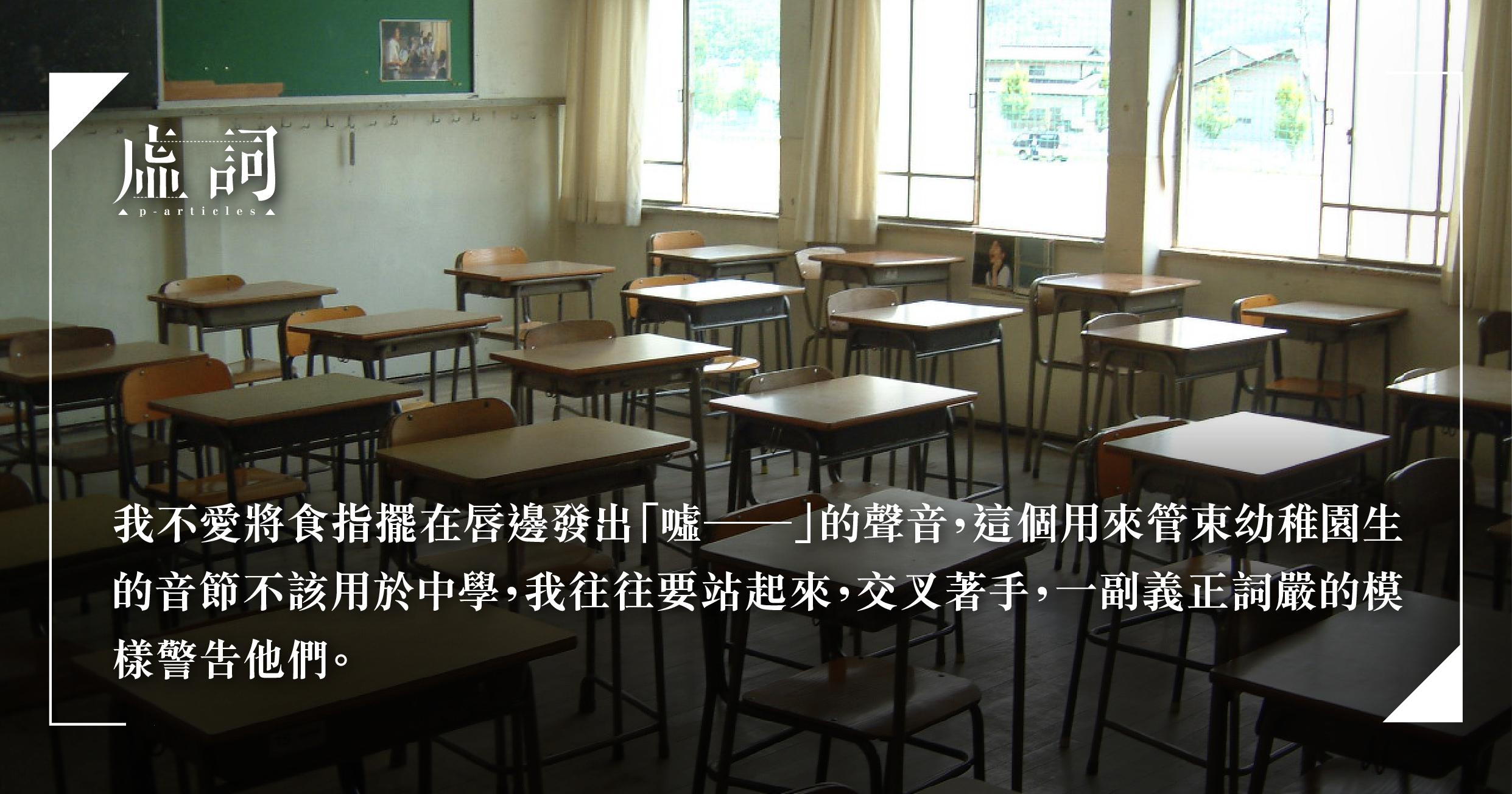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另類的際遇
顯然,大部分時候,我不認識你們,跨過門檻便嗅到違和的氣味,看到陌生的臉孔、新穎的壁報板、不怎親切的窗外景色。不禁訝異,縱使每間課室的格局和設備大致相同,但每個房間都有獨特的氣息。這時,不論是在小息的餘韻中聊談甚歡的中一生,還是低頭思考着算術題的中六準考生,在我登堂入室的一瞬間,他們都會抬頭,與我對視兩秒,遲疑片刻,小則議論紛紛,大則整個課室同時爆破出連串歡呼聲。
而我只覺得,這歡呼聲無比刺耳,亦毫無意義,它不是運動場上的吶喊和打氣,也不是對我熱烈的歡迎,它與我的個人風格和受歡迎程度絕無關係,任何一位教師(只要不是他們這節課的科任教師)踏入課室,也能觸發這群學生強烈的亢奮情緒。我本以為Band 1學生求知若渴,渴求的程度達到教師患病時會憂慮教學進度停滯,為了多出來的一節空堂惴惴不安,但事實顯然沒有,他們非常樂於在這片淺淺的小池塘裡,享受短暫的暢遊時光。
於是他們開始三五成群聊天,乘我不在意時,悄悄離開原來的座位,以討論專題報告為名,與友人竊竊私語起來。我再三巡視和警告:「這課是自修,不是小息的延伸時間!」他們才沒趣地散去。每次代堂,我也會攜帶習作前往陌生的課室批改,手裡拿一疊紙,一支紅筆,踏進未知的領域,顯得很瀟灑,誰不知耳畔嗡嗡的閒聊聲有如深宵的蚊蠅,干擾心緒,使人沒法安下心來,陷入深沉且甜美的夢。我不愛將食指擺在唇邊發出「噓——」的聲音,這個用來管束幼稚園生的音節不該用於中學,我往往要站起來,交叉著手,一副義正詞嚴的模樣警告他們。班中頓時肅靜,鴉雀無聲,多言者自知理虧,胡亂翻揭書頁佯裝溫習。
復坐下,板著臉面,爭取這片刻的寧靜多批幾份卷子,因為我知道,聲浪的苗頭很快又再湧動,然後諸浪伺機掀起,合奏出一首洶湧澎湃的樂曲。我適時放下紅筆,再次警告,課室再次陷入寂靜。如是者不斷重複,我像個頻頻從淺眠中醒來的人,總沒法安穩地睡眠。直至救贖的鐘聲響起,才驚覺自己才批改了寥寥數篇文章,效率比在教員室低了許多。這些習作還是在心神紊亂的狀態下改好的,不論如何公允,心情或多或少會影響評分,這些不幸者只能怪命運不公,於不恰當的時辰展示我眼前。我帶著罪疚感踏出課室,打一個哈欠,像個一宿未眠的人,匆匆朝熟悉的教室走去,追趕下一節課堂。
因此我討厭代堂,每天早上工友或校務處秘書步入教員室,我總畏懼他們手裏會握著小小的紙條,微笑向我走近。紙雖纖薄,卻如刀刃般,切割我本應寧靜美好的空堂,削去寶貴的工作時光。然而,作為助理教師的我,授課時間較其他教師少,因此代堂和監考的職務遠比其他同事多,避無可避,躲也躲不了。監考是在安寧中發掘内心的湧動,靜謐的環境容許我放慢步伐思考,代堂恰好相反,是在繁雜瑣碎的氛圍中竭力尋求寧靜,卻往往索求不得。
疫情嚴峻期間,缺席或需要居家隔離的同事甚多,助理教師不敷應用,一般教師也被傳召,前往不同課室代堂,默默扮演一位疏離的旁觀者,監督自修的學生,更多是監督自我。如此下去,到底何時才能把手中的課業批改完畢?
我不知道,問題應該歸咎於欠自律的學生,還是應怪罪自己過度敏感和容易受影響的個性。我討厭嘈吵,更討厭在眾目睽睽下,鎖緊眉頭佯裝專注工作。我逐漸厭倦了代堂時低效率的我,便索性暫時擱置工作,觀察起這群萍水相逢的學生。代堂時由於沒有科任老師的恆常監管,學生面對突如其來的閑暇,多會顯得鬆懈,真性情表露無遺。有的學生靜靜地繪畫,旁若無人地進入創作的世界;有的學生耐不住寂寞,總愛轉身與友人搭訕幾句。教我佩服的是,班上有幾個頭顱由始至終俯下,默默書寫,心無旁騖,仿佛身旁的湧浪不曾沾染他們。我敬佩他們,能夠以頑强的意志築起牢固的屏障,出淤泥而不染,顯得清高脫俗、不落俗流。
既然無從專注工作,無從躲避代堂的噩夢,我只好換個角度來看待這段流離於不同教室的時光。我發現每間課室窗外的景色都儼然拼圖的一片片板塊,只呈現局部的校園特徵。我學習倚在教師椅上,根據桌上擺放的座位表,嘗試辨認學生的容貌,並與其名字對應。有些流傳於教員室的名字,如今有了堅固的落點,久仰大名,今天我終於看到其廬山真面目。也經常能找到熟悉的,任教過的學生,相隔一兩年再次相遇,他們展現出熟悉卻有點遙遠的臉孔,這無疑在我的心湖擊出小小的漣漪。他們或許不會再主動向我點頭問好,未必會表現得如初中時那麽青澀和率真,但我始終喜見他們的成長,慶幸自己曾是他們路上的一位過客。
任教主科的優勢,是與學生的牽絆較多、感情較深,偶爾代堂重遇,真空的時間恍惚間與記憶中的上課時光重叠起來,讓人赫然分不清班別、課室編號、學期,甚至年月。生命貴在相知相遇,這樣想來,代堂何嘗不是一場另類的際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