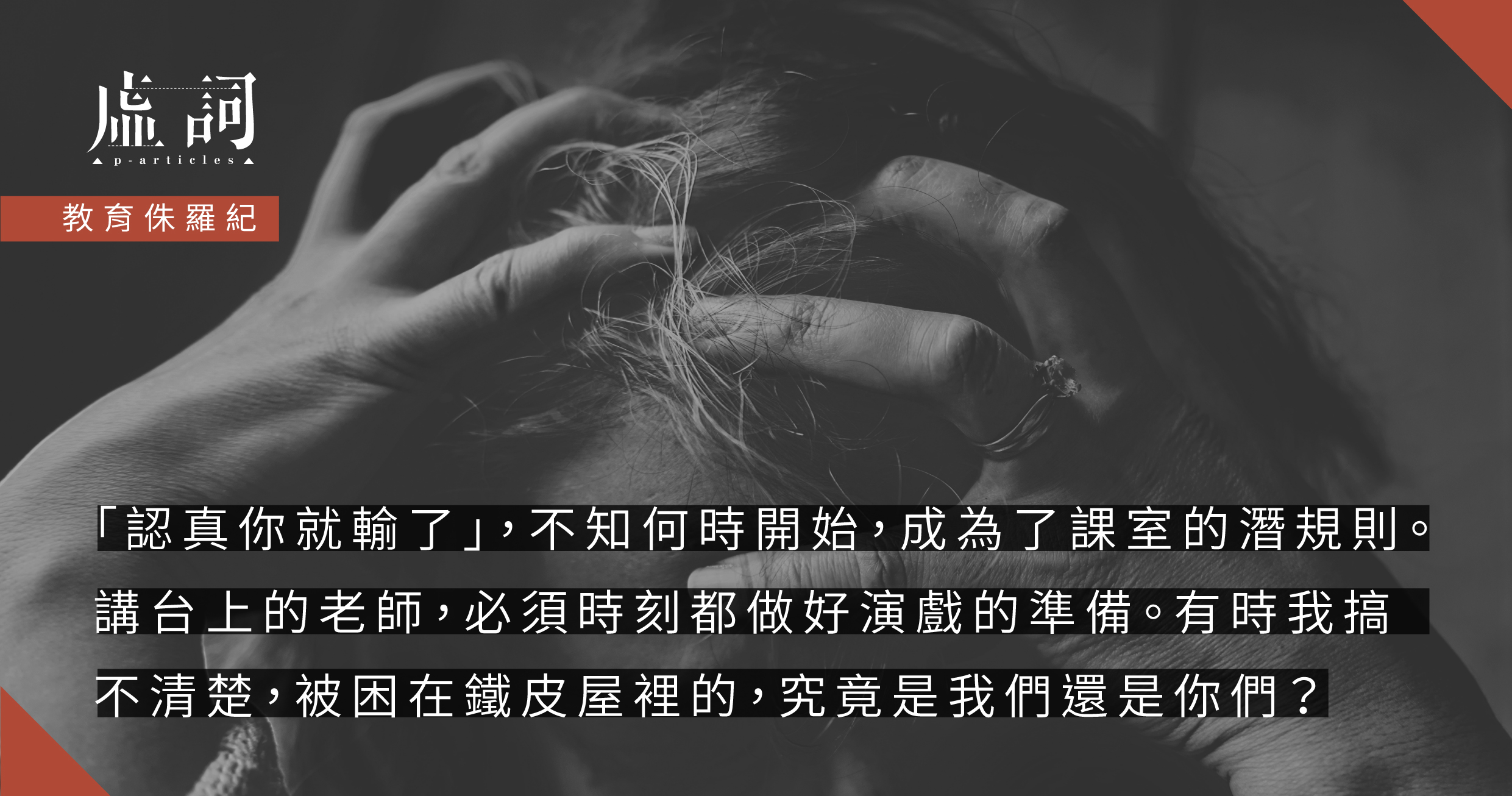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師生關係】「 X!係咁㗎啦。」
教育侏羅紀 | by 陳諾笙 | 2018-12-11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眼前。你沒半點訝異,也沒一點歡喜,可我不會在轉瞬間消失了蹤影,卻要彼此相對13節課。作為漂流教師快10年,我流浪在各大專院校之間;每個學期服務的客仔皆不同,有考上第一志願學系的勝利組,也有僅達「毅進」水平的制度失敗者。我不敢說他們日後的前途如何,目下惟一可以總結的,是兩批學生都是同一種臉孔:懨懨欲睡、愛理不理,天下再大都沒勾起半點好奇,世情再屈機都沒燃起一點星火。「 X!係咁㗎啦。」「 X!係咁㗎啦。」字沒有冒犯的意思,語意大概等同我來自的那個火星年代,所慣用的助語詞「吓」字。
這就是我每次行入課室前,預先調校好的認知模式。如果沒戴上這副有色眼鏡,我有50%機會在課堂中途按捺不住喊:「 X(吓)!你哋瞓醒未?」另外50%機會,我會不斷質疑自己的教學熱誠,以至教育的意義。為甚麼最近兩三年開始,我站在講台上會變得如此吃力,而台下的表情又是如此的金屬疲勞。是我失去了愛的能力,還是他們失去了接收愛的能力?
老師都係臨時演員
記得九月開課,我在堂上請同學介紹一下自己。讓港生談這個話題,通常只落得一種下場,就是:「我叫XXX,最鍾意瞓覺囉/最想做廢青/想hea囉。」因此我多加了一句指引:「可否講一件最近令你覺得快樂的事情?」並且由自己開始,先認真的向同學介紹自己。故事說完,一如所料,他們表情木訥,但我在心裡大聲提醒自己,不要被他們的撲克臉擊倒。
「來,到你們了!」沒有反應,正常。
「有沒有人想先講呀?」當然沒有,正常。
「那麼由最後一行的同學開始吧!」全班只得我一個雀躍,正常。
「我叫XXX,最開心就係可以瞓成日囉。」答題有些偏離,正常。
「那你最近一次瞓足成日,是幾時的事?」甫問出口,連我都覺得自己語言乏味。跟這種對手演戲,做老師的也很難為。
同學,其實我相信你們擁有比這種陳述稍為精彩少少的生命,只是沒有人覺得要認真對待眼前老師提出的問題。呀對,「認真你就輸了」,不知何時開始,成為了課室的潛規則。講台上的老師,必須時刻都做好演戲的準備,表情over一點、動作誇張一些、說話好笑一啲,因為我們跟年輕人之間的一扇門已然愈來愈重。有時我搞不清楚,被困在鐵皮屋裡的,究竟是我們還是你們?
由「講書書」到「 X X 聲」
下課回家,推開門,兩個孩子跑出來相迎。我發現自己用同一副臉孔,跟四歲和六歲的孩子溝通:表情over一點、動作誇張一些,媽媽跟你們講好笑的笑話。孩子接招,正手抽球,乒乓波又來到我的面前,我繼續打出一條拋物線,球來球往,終覺元神歸位。
最近一位同事跟我說,他家裡那個兩歲多的孩子,無時無刻纏著要他「講書書」,叫他莫名感觸。「細路天生就喜歡看書的,但為何我班上的學生,想他們睇多幾隻字都咁難?」我聽著笑了,心裡爆出了一句:「 X!係咁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