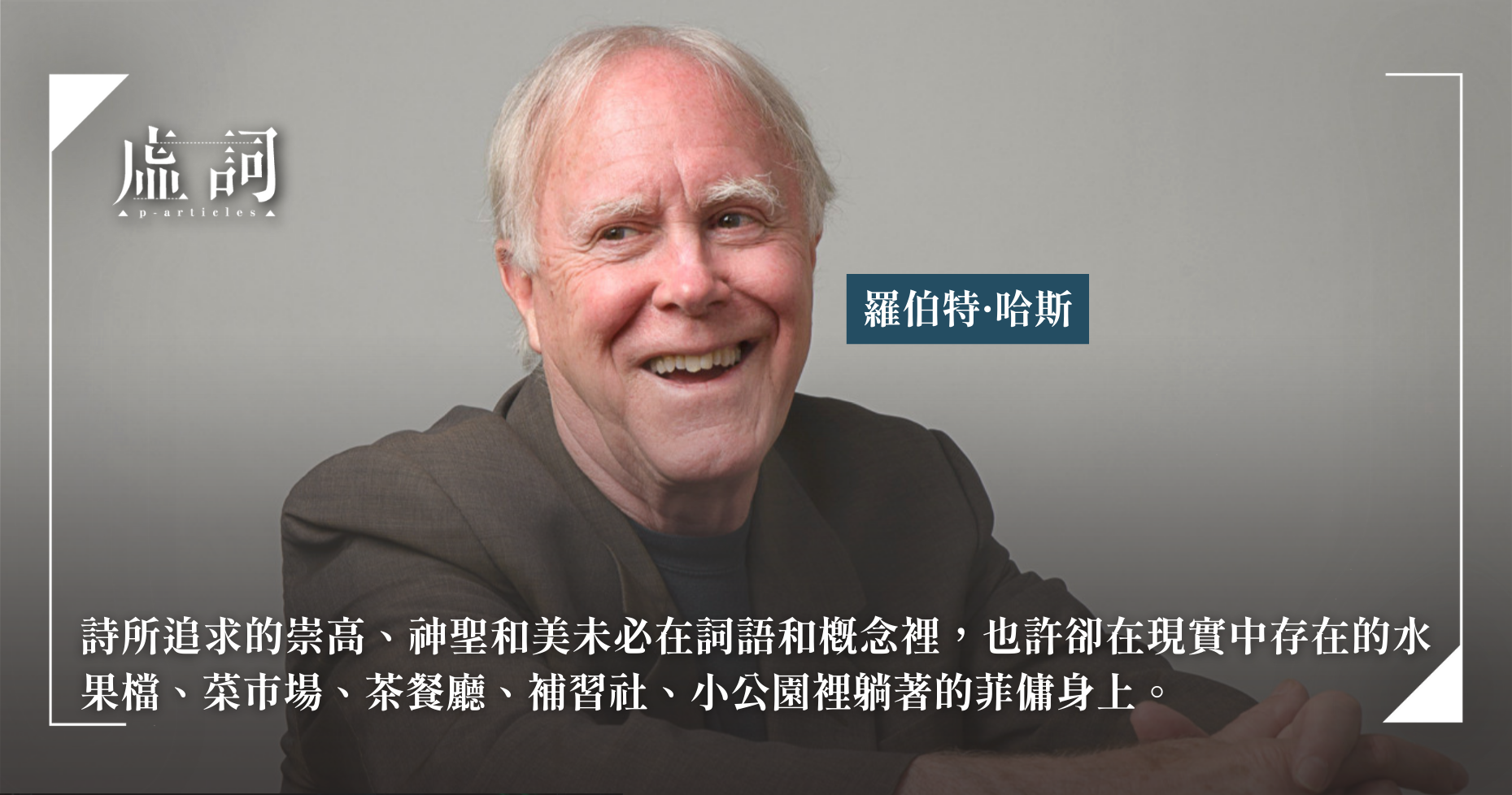讀詩筆記——淺談羅伯特. 哈斯〈在拉貢尼塔斯沉思〉
讀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哈斯 (Robert Hass) 的《夏季雪》,不由想起哈斯的名作〈在拉貢尼塔斯沉思〉(Meditation at Lagunitas)。重讀此詩,對其深深折服。自問對哈斯其人其詩所知甚淺,無力作嚴謹的詩論,只能寫一點鬆散的筆記:
哈斯開門見山,開首便是一句:「所有新思想都和失去有關,就像所有舊思想。」這直白的一筆,表面上似乎是在說——失去是人類生命裡一個歷久常新、永恆的體驗。從古至今,我們都曾擁有過什麼,又失去過許多。但接下來,哈斯描述了他與朋友夜間傾談的內容,給我們介紹了兩種迥異的看法。
1.「每個物象,都會讓概念的光芒變得黯淡。」
2.「每個詞語,都是對它所描述之物的輓歌。」
熟悉柏拉圖理型論的人,對第一種看法想必不會陌生。柏拉圖揚理念而抑具體,認為感官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因此我們所感覺到的具體事物,都是不完美、次等的,而真正的完美只存在於理念身上。哈斯以他所觀察到的啄木鳥為例——「用尖利的喙叩擊枯死的黑樺樹幹」,說明這種看法會使那真實存在、有着鮮活生命的花臉啄木鳥,成了一種「悲傷的墮落」;而第二種看法呢?似乎把這種主次關係倒轉了過來。反倒是詞語「殺死」了具體事物。這是怎麼回事呢?
在我看來,這種想法近似早期的維根斯坦,意識到語言有其界限。語言這簡陋的工具,並不足以把我們豐富的現實、我們的所知所感,拍照似的忠實顯影出來。就如我們每個人見過的啄木鳥,儘管都被稱為「啄木鳥」,但其實忽視了每一隻啄木鳥間的差異;以及我們作為觀察者,在觀察時所注意到的細節、所喚起的情緒......正如辛波絲卡那句「沒有一塊石頭或一朵石頭之上的雲是尋常的。」
第二種看法認為,活生生的物象比詞語更豐富,也更完美。語言或概念,只能是交流和思考的工具,而不能成為事物本身存在的根基。單個詞語所指代的、所能喚起的聯想是有限的,並不足以囊括該對象對書寫者的意義,也不能傳達書寫者對該對象的情緒和感覺。現實並不總是清晰明朗如詞語,在字典中有精確的定義;而常常是複雜多義、曖昧不清的。
哈斯的前輩、美國大詩人威廉斯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作品〈便條〉:
我吃了
李子
那些在
冰箱裡的
那可能
是你
留作
早點的
原諒我
它們是那麼可口
那麼甜
那麼冰涼
沒有繁瑣刁鑽的譬喻,只有明朗沉實、直白如口語般的賦體,結尾連用三個形容詞:可口、甜、冰涼,旨在喚醒我們的感覺,突顯李子是物質,而不是象徵。威廉斯向我們揭示:冰箱上的便條也可以有詩意,詩意就在日常中。威廉斯此詩,可看作現代詩人拉近日常與崇高之距離的一次嘗試。二者不是對立的。
移居美國的波蘭詩人米沃什在一首名叫〈意義〉的詩裡寫道:
——是否,這世界並沒有裏層,
是否樹枝上的畫眉鳥並非徵兆,
而只是樹枝上的畫眉鳥?是否,
日夜相繼並沒有什麼意義,
地球上除了大地也沒有什麼別的?
和威廉斯一樣,這兩位二十世紀美國大詩人不約而同地宣稱:世界沒有裏層。真正的神祕是可見的,是我們的眼睛可以捕獲、舌尖可以觸碰的。這種態度是否意味着自二十世紀往後的詩人們,不再關注崇高、神聖和美,甚至否定它們,開始同乎流俗了呢?
不。他們只是遠離了概念與抽象,而更親近了具體可感的物象,向我們描述感官所能接觸的「表象世界」。詩人黃燦然那首著名的詩〈全是世界,全是物質〉,便向我們證明了——詩所追求的崇高、神聖和美未必在詞語和概念裡,也許卻在現實中存在的水果檔、菜市場、茶餐廳、補習社、小公園裡躺著的菲傭身上。
國學大師王國維評《紅樓夢》時寫道:「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從個體經驗出發,反而能達致經驗、情緒的共通共鳴。這正是哈斯在詩的後半段中做的——像同時代美國詩人傑克・紀伯特自傳式的書寫。哈斯寫他童年的那條河、河裡橘銀色的小魚和他愛過的女子,卻使遠在千里之外的我們,真切地感覺到那種誠摯的溫柔。任何神聖的概念,在現實的重量面前都顯得飄忽輕盈、黯然失色起來:
我曾和
一個女人做愛,記得有時捧著她瘦小的肩膀,
會突然為她的存在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
像渴望鹽,像思念童年那條河——
河心小島垂柳依依,遊船漫出俗氣的樂聲,
我們在泥濘的岸邊,釣起橘銀色的小魚——
叫「南瓜籽魚」。這幾乎與她無關。
我們說「渴望」,因為慾望裡總橫亙著
無盡距離。我對她而言大概也是如此。
但我記得那麼多細節:她掰開麵包的樣子,
她父親說過的令她傷心的話,她
做過的夢。
美國現代詩人們從漢語古詩中發現了:厚實的物性(materiality)、深刻的賦體傳統,參透了其中的技藝。佼佼者如蓋瑞·施耐德,在〈八月中旬沙斗山瞭望哨〉中寫——「用鐵皮杯喝寒冽的雪水」,便能讀出幾分漢語古詩的韻味。哈斯詩中的這一段亦然。
早在18世紀,諾瓦利斯這位浪漫主義的先驅者早已斷言:「世界必須被浪漫化····這項工程還完全不為人知。當我給卑賤物一種崇高的意義,給尋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樣,給已知物以未知的莊重,給有限物一種無限的表象,我就將它們浪漫化了。」給已知物以未知的莊重,注重日常中的細節——正是這些美國現代詩人的共通之處。他們以詩提醒我們,謙遜面對自以為熟知而乏善可陳的日常。他們筆下提鍊出的詩意絕非詩人的美化、矯飾,而只是發掘本來就存在於庸常裡面的神奇。不是旨在粉飾一個一無可取的世界,而是啓發我們改變思想,摒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重視效率、功利的世界觀,還世界以本來面目罷了。
至此,我們才恍然明白開篇「新思想」和「舊思想」所指的究竟是什麼。詩中呈現兩種思想的衝突——一種是蔑視此世,信仰一個超越表像的「理念世界」的主張。那是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在斐多篇裡闡述的:「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我們得甩掉肉體,全靠靈魂用心眼兒去觀看。所以這番論證可以說明,我們要求的智慧,我們聲稱愛的智慧,在我們活著的時候是得不到的,要等死了才可能得到。」這與後來基督教輕鄙身體、重視靈魂的來世觀遙相呼應,受近代哲學家如尼采的批評;而另一種則是現代美國詩人和哲學家們對西方傳統哲學的省思和反叛。顛覆了自柏拉圖以降西方哲學注重本質的傳統,呼應了沙特「存在先於本質」的思想,展現出一種詩學的存在主義——詞語先於其本質而存在,可以通過自由的選擇來塑造。
在詩的最後,哈斯寫道:「有些時刻,身體和詞語一樣散發著神性的微光。」此句可看作兩種看法的和解,也是物象和詞語的和解。肉體與靈魂本是同一。當兩者地位比肩時,這就夠了。為什麼非要走到對立面,把對方貶得一無是處呢?
回到哈斯在詩的中段所舉的例子:「因為這世上沒有任何一樣東西,能完全對應『黑莓叢』這個詞。」正因如此,詩所追求的不該是物理公式般的精確,而是以文學的邏輯賦予「黑莓」嶄新的涵義。在現代,科學取代了邏各斯(或上帝)的位置,走到了感官的對立面。哲學家梅洛龐蒂在《知覺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中寫道:「我們需要重新喚醒對世界的體驗,因為我們藉着自己的身體在世界上存在,因為我們用自己的身體感知世界。」梅洛龐蒂在其演講集《知覺的世界》(Causeries 1948) 中,拆解了客觀、規律的「科學世界」比主客混融、多變的「知覺世界」為優的迷思,指出那客觀冷峻的「科學世界」中人的缺席。概念僅僅是物象的「近似值」,物象唯有與人連結才能產生意義。
於是,在哈斯的主觀經驗裡,「黑莓」這個詞便超越了字典所框架的定義,而成為一種溫柔回憶的代稱。他在詩的結尾三次吟詠「黑莓」這個詞。從愛情的甜蜜到童年的美好,從前午後與傍晚溫柔的時光,就都蘊藏在了「黑莓」裡。這也許也和後期維根斯坦提出的「語言遊戲」——這一反本質主義哲學有共通之處。
而說起黑莓,便不由想起二十世紀愛爾蘭大詩人希尼的名作〈摘黑莓〉:「每年我都期望它們長存,但我知道它們不能。」同樣以黑莓為主題,也是關於失去。驀地發現,哈斯這首詩其實也是在探討語言的意義——為了成為記憶的載體,描述那些已經失去、即將失去,或終將失去的——昨日的雲、消逝的愛情、童年的河、米沃什的故土、杜甫的長安......或我們的香港。
是的。所有思想都和失去有關。唯一的天堂是我們失去的天堂。哈斯說的沒錯——一切都會消解,這也許正是佛家說的「夢幻泡影」。而詞語就是輓歌。那麼從現在開始把世界浪漫化吧,趁我們還沒有失去得更多。世界本來就是浪漫的。那些在時間裡佚失的人、事、物,像白雲消融在藍天的臂彎裡,把我們的生命滌蕩成一種空闊的藍。在這樣的藍裡,有時能看見飛鳥似的詩,負青天,摶扶搖而上。
附:〈在拉貢尼塔斯沉思〉
所有新思想都和失去有關
就像所有舊思想
有一種想法:每個物象,都會讓
概念的光芒變得黯淡。那花臉的
啄木鳥,用尖利的喙叩擊枯死的
黑樺樹幹——它的存在本身
彷彿是一種悲傷的墮落,背離了最初那
完整而明亮的世界。或者另一種看法:
因為這世上沒有任何一樣東西,
能完全對應「黑莓叢」這個詞,
每個詞語,都是對它所描述之物的輓歌。
昨夜我們聊這個話題聊到很晚,朋友的嗓音裡
有一絲細微的悲傷,幾乎
帶著點怨懟。過了一會兒,我才明白:
這樣談論下去,一切都會消解——正義、
松樹、頭髮、女人、你和我。我曾和
一個女人做愛,記得有時捧著她瘦小的肩膀,
會突然為她的存在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
像渴望鹽,像思念童年那條河——
河心小島垂柳依依,遊船漫出俗氣的樂聲,
我們在泥濘的岸邊,釣起橘銀色的小魚——
叫「南瓜籽魚」。這幾乎與她無關。
我們說「渴望」,因為慾望裡總橫亙著
無盡距離。我對她而言大概也是如此。
但我記得那麼多細節:她掰開麵包的樣子,
她父親說過的令她傷心的話,她
做過的夢。有些時刻,身體和詞語一樣散發著
神性的微光;有些日子,是鮮活的肉體延續。
那些午後與傍晚,那樣的溫柔
反覆念著:黑莓,黑莓,黑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