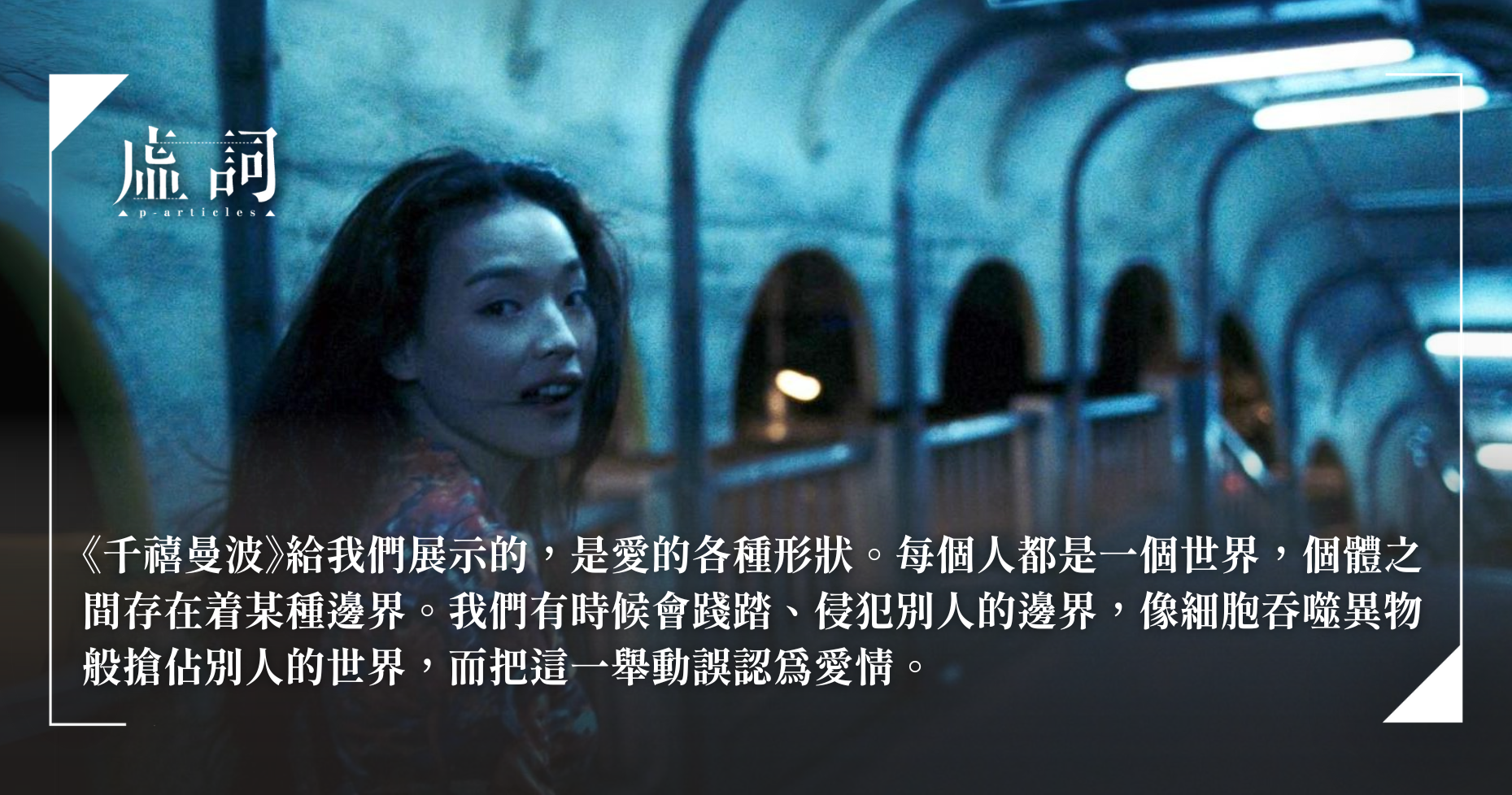愛是? ——談《千禧曼波》及愛的哲學與詩
「竹內康說夕張的冬天很冷,零下三十幾度,她想那是雪人的故鄉吧,雪人最後在太陽升起的時候融化不見了。有一次她跟豪豪做愛,她覺得他就會像雪人一樣,在太陽升起的時候,消失不見。」
《千禧曼波》給我們展示的,是愛的各種形狀。豪豪自私冷酷,愛自己多於愛別人,訴諸行動上的,是言語和肢體暴力。豪豪的愛是一種無止境的索取,渴望透過佔有另一獨立的個體,填滿自己內心的空虛。侯孝賢以安非他命和時刻在Vicky耳邊縈繞的電音暗示我們:豪豪的愛就像幽深的黑洞——吞吸、牽扯,吃掉所有的光,使人受困。豪豪不斷向Vicky強調:「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Vicky從咖啡店工讀生那種「正常大學生」的世界,掉落到夜店、夜總會裡。但我還讀出了另一重含義:每個人都是一個世界,個體之間存在着某種邊界。我們有時候會踐踏、侵犯別人的邊界,像細胞吞噬異物般搶佔別人的世界,而把這一舉動誤認為愛情。
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在《善的脆弱性》中說:
「我們自己最早也是最愛的玩具往往是那些可以打開的東西。甚至在我們會說話之前,我們已經嘗試著把東西打開了。我們會坐在地板上幾個小時,全神貫注地把木頭或塑膠球打開兩半,在裡面找藏著的鈴鐺和小人。阿爾西比亞德斯用這樣的玩具作比喻,其目的是要表明我們最早的、最強烈的一個慾望就是要『打開』東西,想要深入探究被外表所掩蓋的內部;在這樣一個慾望中,性需求和認知的需求被結合在一起,顯然是不可分離的。我們都渴望揭示和闡明那些被隱藏起來的秘密的東西;每當我們看到一道裂縫時,我們也看到了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的大好機會。我們期待著能夠打開裂縫,展現裡面隱藏著的美,探究在我們的想像中應該存在的世界,並透過感覺、感官、情感和理智去理解這世界......我們很容易看出,在對性的慾望與對智慧的慾望之間有一種結構上的相似性。兩者都指向外在世界的對象,都以把握和擁有那些對象為目的。而每當充分地掌握了那些對象時,這兩種慾望都會有暫時的滿足感:就像圓球不再誘惑我們,『神不再需要苦苦追尋真理』(204A)那樣。(對真理的沉思當然是另一個問題。)這兩種慾望都為美和美德所喚起,又都試圖去理解美德的本質。它們所尊崇和鍾愛的對象是分離的和獨立的實體,但同時又渴望能夠與那些實體合而為一。」
我們可以把愛視為不完滿的個體對完整的渴求,就像阿里斯托芬在會飲篇裡說的那樣。「打開」這個動作具有肉體和心靈上的雙重含義。愛就是渴望去打開另一個人的衝動,這種衝動驅使我們去揭開、去看見隱藏的風景——不只窺探身體,也是去目睹每個人隨身攜帶着的那個世界。
與對玩具和狗那種把愛人視為所有物相反的愛,是像愛山海、愛星空那樣去愛一個人。在愛的對象中感受到美與某種可愛、崇高的特質,因認識到對方是至少與自己同等的存在,而發自內心地尊重、欣賞。自然界裡,有樹冠羞避這一現象。樹與另一棵樹的枝葉之間,總會留有一絲空隙。佛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中寫到:「如果不是愛的第三個因素——尊重,責任就會很容易地墮落為統治和佔有。尊重並不是懼怕和敬畏。根據它的詞根(respicere,注視),尊重意味著能夠按照其本來面目看待某人,能夠意識到他的獨特個性。尊重意味著關心另一個人,使之按照其本性成長和發展。這樣,尊重意味著無利用。我希望所愛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為他自己而不是為著服務於我的目的而成長和發展。如果我愛另一個人,那麼我就會感到和他或她是一體,但他還是他,並非把他作為為我所用的對象而需要他。很顯然,只有我實現了獨立,只有我不需要枴棍就能站立和行走,不統治也不利用任何他人,尊重才是可能的。」把愛視為佔有的人,事實上都是無法獨立生活、需要拐杖才能行走的人。
與豪豪的索取和佔有相反,捷哥的愛是沉默寡言的給予。在Vicky喝得爛醉時為她披上毛毯,帶着一種成年男性對年輕女性的憐憫,帶着淡淡的距離感。也許他把對染上毒癮的女兒Pauline的感情,投射到了Vicky身上,像是在呼應佛洛姆所說:「不是說我們要為別人犧牲生命,而是把生命裡面活生生的事物給予出去。像是把我們的喜悅、興趣、知識、憂愁給予出去。在這種給予當中,我們豐富了別人,用一種增強自己生命力的方式,擴大了別人對生命的感受。」《罪與罰》裡的索妮婭就是這種愛的一個極端例子,為供養繼母與妹妹而淪落為妓,不求回報。
現代人習慣把愛視為一種商品式的等價交換。佛洛姆認為,當代社會是以一種互利交換的觀念為基礎的。一個人在一段感情裡投入了多少,便希望得到同等價值、甚至價值更高的回報,彷彿愛是一種投資、一種恩惠。愛是甚麼——是我從看〈Drive My Car〉後就開始不斷思考的問題。在〈Drive My Car〉裡,家福的妻子音是愛家福的嗎?如果是,音又為什麼會出軌、傷害丈夫呢?家福的遭遇向我們揭示了愛的不穩定性。努斯鮑姆提出,善之所以脆弱是因為它是和外在的偶然性——外在世界賦予我們的境遇緊扣在一起,像葡萄藤的生長受氣候影響。因此,當我們遇到可以觸發「愛的感覺」的第三者,原有的愛情便有可能遭受考驗。
愛首先是一種體驗,一種自然而然發生、說不清道不明的衝動,像剛下鍋的蛋,在熱油中流動、膨脹,迅速升溫。隨着時間推移,蛋白和蛋黃凝固成形,熄火,起鍋,冷卻。愛於是從衝動變成一種責任,從液態、不穩定的蛋清進入固態。愛就像煎一個蛋。如果把愛純粹看作是一種衝動、一種感覺,愛便永無穩定的可能。
佛洛姆說:「導致關於愛沒有什麼可以學習之看法的第三種錯誤在於,人們通常把『墮入』愛網時的最初體驗和置身於愛之中的持久狀態混淆起來。如果兩個像我們大家現在這樣素不相識的人,突然打破了把他們分隔開的那堵牆,感到親近起來,合為一體了,這種合為一體的時刻乃是人生中最令人激動、最令人興奮的體驗之一。這對於那些一直處於封閉、孤立、沒有愛之狀態中的人來說,尤其是妙不可言、驚喜莫名的,這種突如其來的親近的奇蹟如果又是與性的吸引和結合相聯繫或是由它所引起的話,就更加容易發生。然而就其本性而言,這類愛是好景不長的。兩個人之間愈是熟悉,他們之間的親密愈是失去其神祕性,直至他們的對立、失望和彼此厭倦終於扼殺了殘存在心中的那一點最初的興奮,然而他們開始並不知道這一切。他們並不懂得,所產生的那種強烈的迷戀,那種證明他們相愛之深的彼此『發癡』的狀態,實際上可能只是證明了他們先前的孤獨程度。」渴望重溫最初的狂喜和怦然心動,或許能夠解釋出軌者的心理。
我們愛的往往不是那個活生生站在我們面前的人,而是那人在我們心中的形象。這形象的誕生,結合了我們的經驗和想像。辛波絲卡寫過一首詩〈僅此一次〉:
昨天,當有人
在我身邊大聲說出你的名字
我感覺,好像玫瑰
從打開的窗口掉了進來
今天,當我們在一起
我把臉轉向牆壁
玫瑰?玫瑰長什麼樣子?
那真的是花嗎?還是石頭?
愛的不穩定性就在於:我們所創造的形象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着記憶而淡化、扭曲。而最終,所有的可愛和美被倦怠擠開,沉入結滿蛛網的深邃角落,像墜毀在深海裡的潛水艇——舷窗破裂,氧氣耗盡,壓力猛然放大。最後的燈光在心的海床上微弱地閃爍着,螺旋槳的葉片從此停止旋轉,不再製造另一次心動。
「有一次她跟豪豪做愛,她覺得他就會像雪人一樣,在太陽升起的時候,消失不見。非常悲傷的做愛過程,其實在多年後她還記得。這都是她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是2001年。那年夕張大雪。」整部電影其實是Vicky的回憶。電影中段,捷哥的車在公路上飛馳,Vicky打開車頂天窗,站立着,兩側是串珠似的、散發着迷離光暈的路燈。白襯衫在風中翻飛,以一片雪花、一隻白粉蝶的輕盈,展臂迎向永恆呼嘯的風。在時間的單向道上,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這段時空留下無形的印跡。
夕張的雪最終掩蓋了一切年輕時的悸動和不安、笑聲和眼淚。太陽升起時消失的,不只有豪豪。在黯淡、杳無人跡的雪景中,我想起紀伯特(Jack Gilbert)的兩句詩:
他意識到他們用盡了那段特別的時間
在宇宙中所有地方,永永遠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