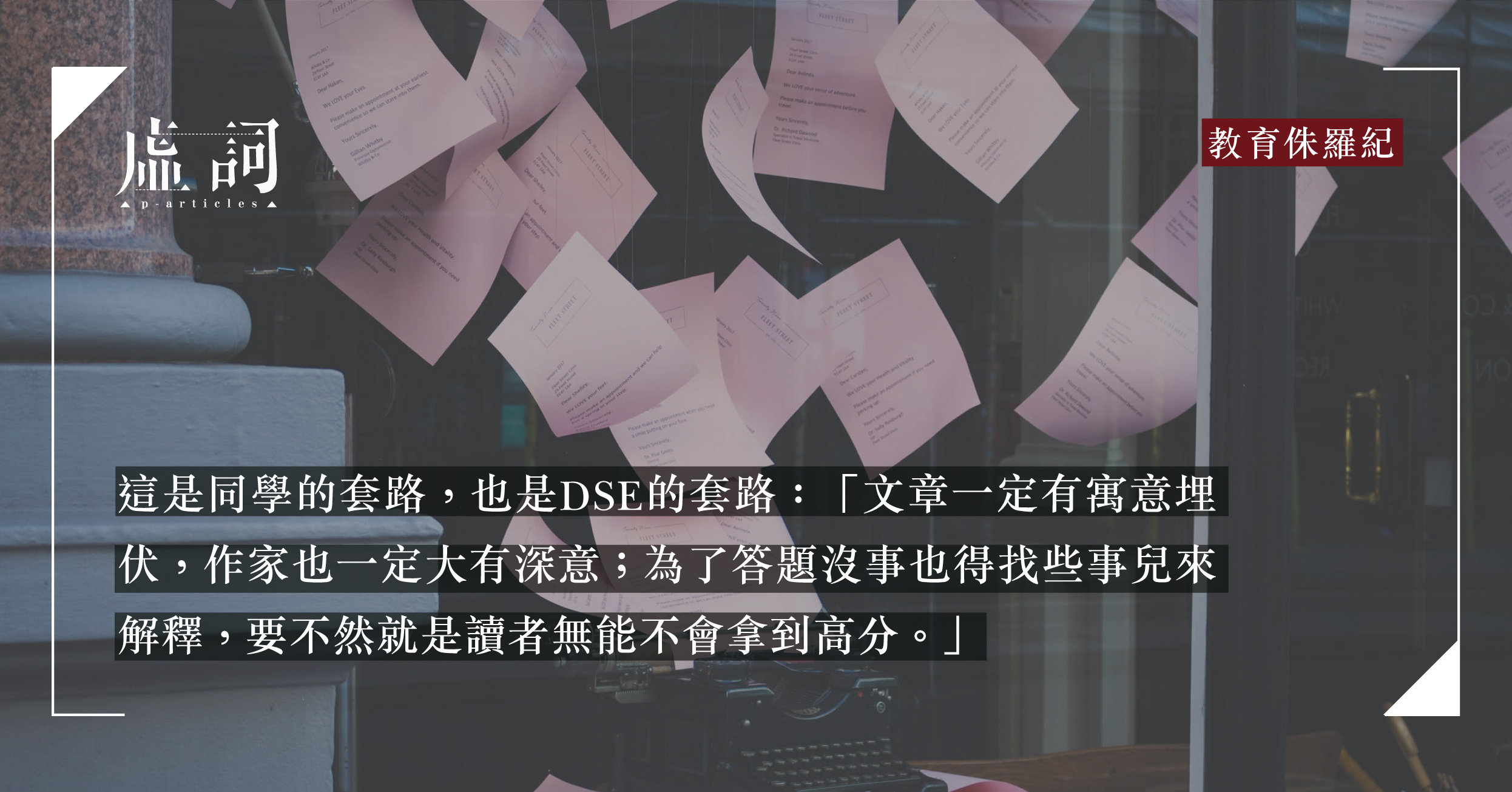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大學語文】巴金,與my little airport(下次可能是其他)
今天這個小組要報告的是巴金《猴子的悲哀》。巴金作品繁多,這一篇不算出名,但篇幅短小,適合非中文本科生閱讀;其內容表面顯淺,能討論的角度也很多。
對大部份同學來說,巴金是個與他們無關的人。於是他們在網上找來跟巴金的生平與評論資料,挑選些看上去厲害的字眼來誦讀,例如「民族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五四運動」等;文章中出現的外國人,也自然被視作「帝國主義」、「西方列強」等象徵。 這是同學的套路,也是DSE的套路: 「文章一定有寓意埋伏,作家也一定大有深意;為了答題沒事也得找些事兒來解釋,要不然就是讀者無能不會拿到高分」,這是大學一年級同學的共同閱讀意識。課程第一堂,我就已經說了:「DSE所教的不是錯,而是文章解讀之法不只一種。現在你們已不用考公開試了,可以放心大膽地說自己想說話了。」耶穌來,是要叫羊得生命;我來,是為了叫人排毒洗白。然而經歷了六年肉搏、好不容易擠進大學門檻的精英們,又怎會輕易放棄自己一身的(也是惟一的)招式。我的標準與林鄭口中的紅線一樣,一年比一年低;一個學期後,但求他們發現「中文原來有別的讀法」,也就算階段性勝利了。
好了,按著DSE的政策路線,同學們規規矩矩不過不失地報告完畢。不能說他們不用心也不能說他們沒準備,只是耶穌行走江湖三年尚落得個釘十架的下場,一個學期三個月自然也不能讓人輕易悔改。以前的我大概會言正辭嚴地教訓他們一頓:「人云亦云」、「照參考資料照讀」、「這裡其實是……(下刪三千字)」,但現在的我不會這樣作。我先問他們:這篇文章可以單純寫一隻猴子,而不牽涉到國仇家恨嗎?這不但是因為我關注動物,也因為我關注同學如何理解閱讀。然後我以巴金的另一篇文章《小狗包弟》來比較,看看以動物為題材的文章可以有多少寫法,而巴金真正的價值又在哪裡;我又請他們想像:如果不用報告,就把《猴子的悲哀》當成雜誌專欄文章,不看參考資料也不理作者是誰,又有何讀後感﹖結果他們說:猴子是想要自由的打工仔,香港人;而圍觀的外國人就是與國籍無關的「花生友」。我沒有評論這樣的聯想正確與否;畢竟課室不是試場;我事前也無法預測他們給出怎樣的答案。此刻我想起的,是My little airport的兩首歌:〈給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和〈西西弗斯之歌〉。
「放給你們聽,」我說,「第二首有粗口的哦。」
在金鐘地鐵站擠上車的是甚麼人?擠不上車的又是甚麼人?西西弗斯是誰?他是瘋子還是阿Q?可以有許多答案,也可以沒有答案。我來,不是為提供答案,而是提出問題。
文章讀完了,報告完了,歌也聽完了,課堂自然完了。我走出課室,無法想像另一班,另一組同學,在報告同一篇文章時,會想起甚麼,而我又可以如何應對。或許教學本該如此:五分規矩,五分彈性。就像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