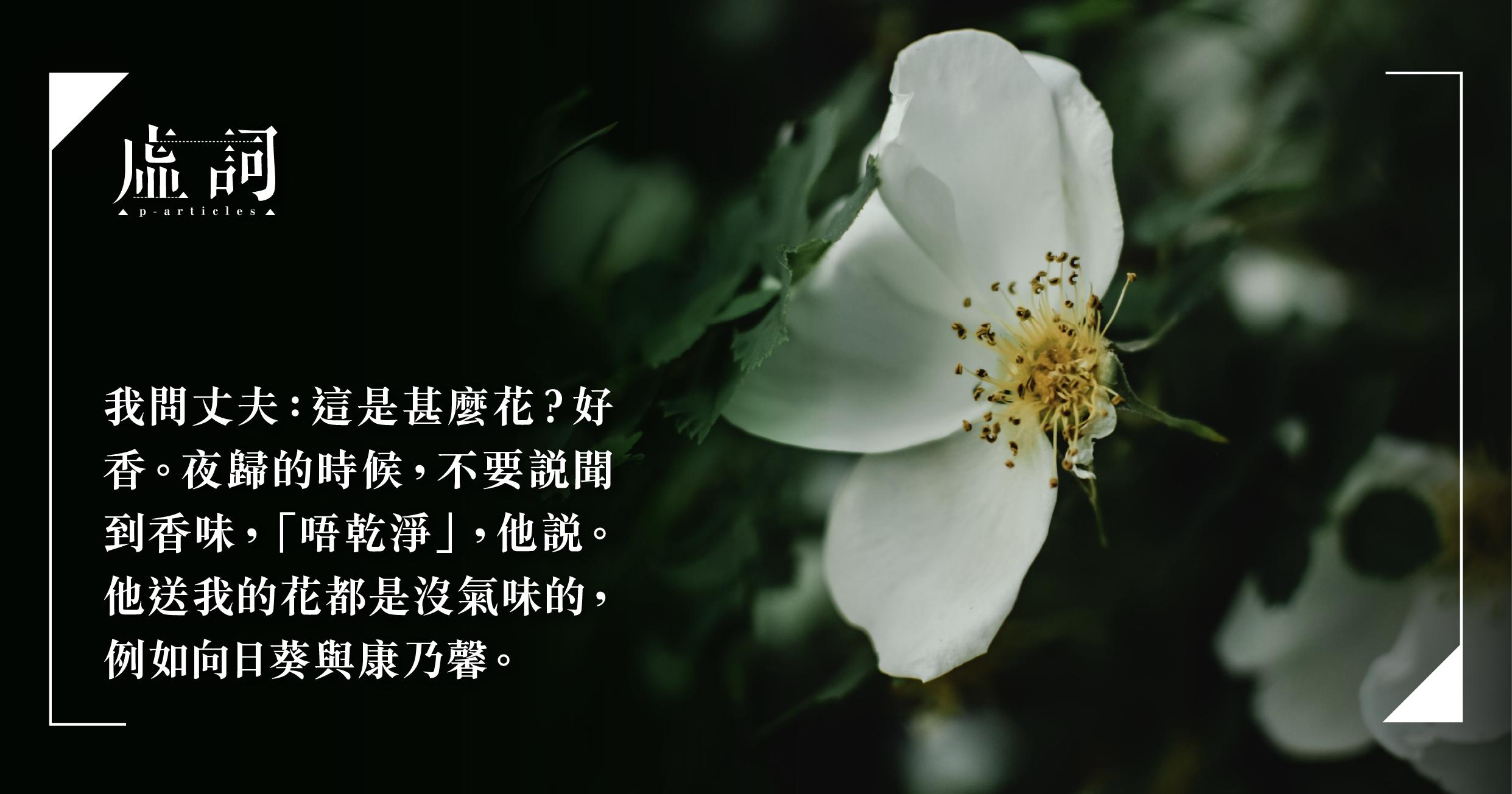金枝玉葉
我家附近有一幅爛地。那是私人屋苑與公共屋邨之間的地方,四周用鐵絲網圍起,網後是橫生的雜草,說不出名字的樹;蚊蟲亂飛,野貓走過。也有狗。一隻天真的黑色幼犬,曾向我咧嘴而笑。據說也有野豬。在某些寧靜的夏夜,路過這裡,我會嗅到一陣花香,隱約而清幽,像白蘭,也有點像薑花,粗長的野種,慷慨地向路人招手。我問丈夫:這是甚麼花﹖好香。夜歸的時候,不要說聞到香味,「唔乾淨」,他說。他送我的花都是沒氣味的,例如向日葵與康乃馨。
我總說不出這香的名字,就像我說不出她的名字一樣——我從來沒知道過。
在我母親口中,她就是「嗰個女人」,詳細一點的話,就是「我哋個度嗰個女人」。有一次,我和母親到街市買菜,母親忽然用手肘撞我。
「呢,就係嗰個女人。」
我順著母親的目光看去,不遠處有個女人正從樓梯上來——那其實就是個極普通的中年婦人,電過的頭髮綁上一條彩色的髮帶;幼框眼鏡,沒化妝的臉,嘴角因法令紋而往下垂。那張臉隨著上樓梯的步伐往上升,令人有一種肅目的錯覺。
關於這個女人的故事,母親是在我家的客廳告訴我的。我常覺得,母親如果生於宋朝,應該是個說書人。
「我哋個度有個女人。」母親開始她的敘述。
「甚麼女人﹖」我熟練地接話。天氣太熱了,我家沒有宋朝市集的樹蔭,我只好給她開了冷氣。如果我也生在宋朝,應該就是剃了個榪子蓋頭,淌著鼻涕,等著故事開始的街邊細路。
「我都係聽啲街坊講,我只係見過嗰個女人幾次。」母親先表明立場:她跟這個女人不熟悉,對接下來的內容不負責。我一邊收拾晾乾的衫褲,一邊聽她說下去。
「嗰個女人呢,其實我都同佢一齊晨運過一排既。佢見我哋成班街坊朝頭早晨運,佢都落嚟玩過幾朝。佢同黃太講,話呢兩年無得上深圳揼骨,周身唔舒服。」
「很多人喜歡上深圳揼骨。」我答。
「不是正正經經揼骨啦,」母親覺得我太天真,「佢同黃太講,話嗰度啲後生仔好力啲,服侍得好喎。」
「哦…」我想了一想,覺得價錢才是最重要吧,雖然深圳的物價也不會太低。「其實這些事也不用刻意向別人提起。」
「呢樣都未算。」母親果然是鋪墊的高手,「佢其實有老公,佢同佢自己阿媽,仲有個女一齊住。佢老公呢,好慘既,中咗風,要坐輪椅。」
「哦……」
「佢索性叫另一個男人返來,一齊住係個公屋單位入面。」
「為甚麼不索性離婚呢﹖這樣她老公不是更難受嗎﹖」
「唉,佢話要照顧佢老公喎。聽啲街坊講,有次佢地幾個食完晚飯係度睇電視,個女人忽然叫個男人入房,閂埋房門唔知搞乜。」
「那……」我是個寫小說的人,但自問寫不出這種情節,寫出來也沒有人相信。
「係呀,佢個女嬲到死呀。」
「她的女兒多大了﹖」
「中四啦,好大個了。」
我只覺得這一切實在太過奇情,忘記追問這種閨房秘事為何會洩露,「中四是敏感的年齡,她一定很痛苦。」
「但係後來嗰個女人趕走咗個男人。」
「這又是為甚麼呢﹖」
「因為個男人打她老公。佢話,我叫你嚟住係一件事,你唔可以打佢喎。」
「哦…」我消化了一會,「那麼她也不是毫無原則…」
「你可以咁講既,」我媽點點頭,不反對我的點評。
「嗯……」
「啲街坊都同嗰個女人既阿媽講過,叫佢勸下個女唔好咁。」我媽開展另一條故事線,「你知唔知佢阿媽點答﹖」
「她怎樣回答呢﹖」我順從敘事者的引導。
「佢阿媽話:車﹗我個女咁後生,鬼叫佢滿足唔到我個女呀﹗」
「……」我對於老太太的坦白無從辯駁。
「後來啲街坊同我講,佢阿媽好鍾意打牌,成日周圍撩啲男人同佢打牌,一坐低就拉低件衫露個心口出嚟,搞到啲男人輸哂啲錢。」
「但是她的母親應該年紀不小了吧﹖」
「六七十啦﹗男人係咁架啦﹗有得睇點會唔睇﹖」我媽大概覺得我少見多怪,話題就此結束。
我一直記住這個女人的故事,直至後來,我在街市上跟她聊起來—應該說,我再度成為聽眾。
那是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下午。街市電梯門打開,我媽口中的「嗰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已經在裡面。我內進,電梯關門。他們本身在聊天,彷彿是某個小孩子的讀書問題。
電梯到達頂層,我、男人和女人相繼離開。男人走向另一個方向;這個時候,我看了女人一眼。她也看到了我看了她一眼。
「我認為,而家啲教育制度,係好唔合理。」女人說。
「嗯。」我回答。
「其實細路仔係唔應該一味做功課。佢哋應該多啲時間出去玩,做多啲運動,見下個世界。」
「的確是。」我由衷地同意女人的話。
「我個女細個嗰陣時,我成日教佢,唔好剩係掛著做功課,要多啲去玩,先知自己鍾意啲咩。」
「嗯嗯。」我想不到任何反對的理由。
「所以,你哋都唔好一味谷啲細路,谷到佢地呆頭呆腦。」
「嗯嗯嗯。」我保持禮貌。
「我自己主張教細路要因材施教……」她忽然看我一眼,聳聳肩,轉身離去——大概是看到我臉上客套的微笑。
在那之後我碰見她幾次。她再也沒有跟我說話,就像一切從來沒有發生過。
某個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又嗅到那種香味。那是颱風的前夕,蟑螂在路上倉皇亂竄,我跕起腳快走,恐防牠們爬上腳來。悶熱的空氣像塊巨形保鮮膜把世界重重包圍,然而我知道半空正在蓄積暴雨和風;它們在世人的頭頂盤旋,等待適合的時機爆發能量。
一陣溫熱的氣息吹過,花香忽然撲向我。
在距離大廈閘口還有幾步的地方我停下來。這次我決心要找到香氣的來源。眼前黑影掠過,是一隻芥末黃的飛蛾,靜靜地降落在燈柱上;雙翼上兩顆黑色的圓形圖案,像一雙渴睡的眼睛。
忽然,飛蛾起飛了;在混濁的空氣中牠穿過鐵絲網,飛到爛地上。昏暗的街燈下我看見牠撞向一叢灌木的花上;那花小而白,幾朵撮成一團;飛蛾撲上去,花便搖動起來,迎向蛾的吸吮。
我想像那花蜜的滋味。
風起了,帶著雨水與草青,如殺戮的腥。我急步走進大廈中。
「你回來了。」丈夫給我開門,「颱風到了。」
我走到窗前,看見平台上的樹不住搖晃。雨開始打在玻璃窗上,愈來愈激烈。天文台說,這是個超級颱風,風速超過過去五年的所有風暴。
風從窗戶的隙縫中閃進,我又嗅到那花的香味。
「好香﹗」我大聲說。在室內的光亮的安全的家裡,我被排除在所有的不潔以外。
我想起那飛蛾,覺得牠未必捱得到明朝,忽然明白牠那飛行的姿勢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