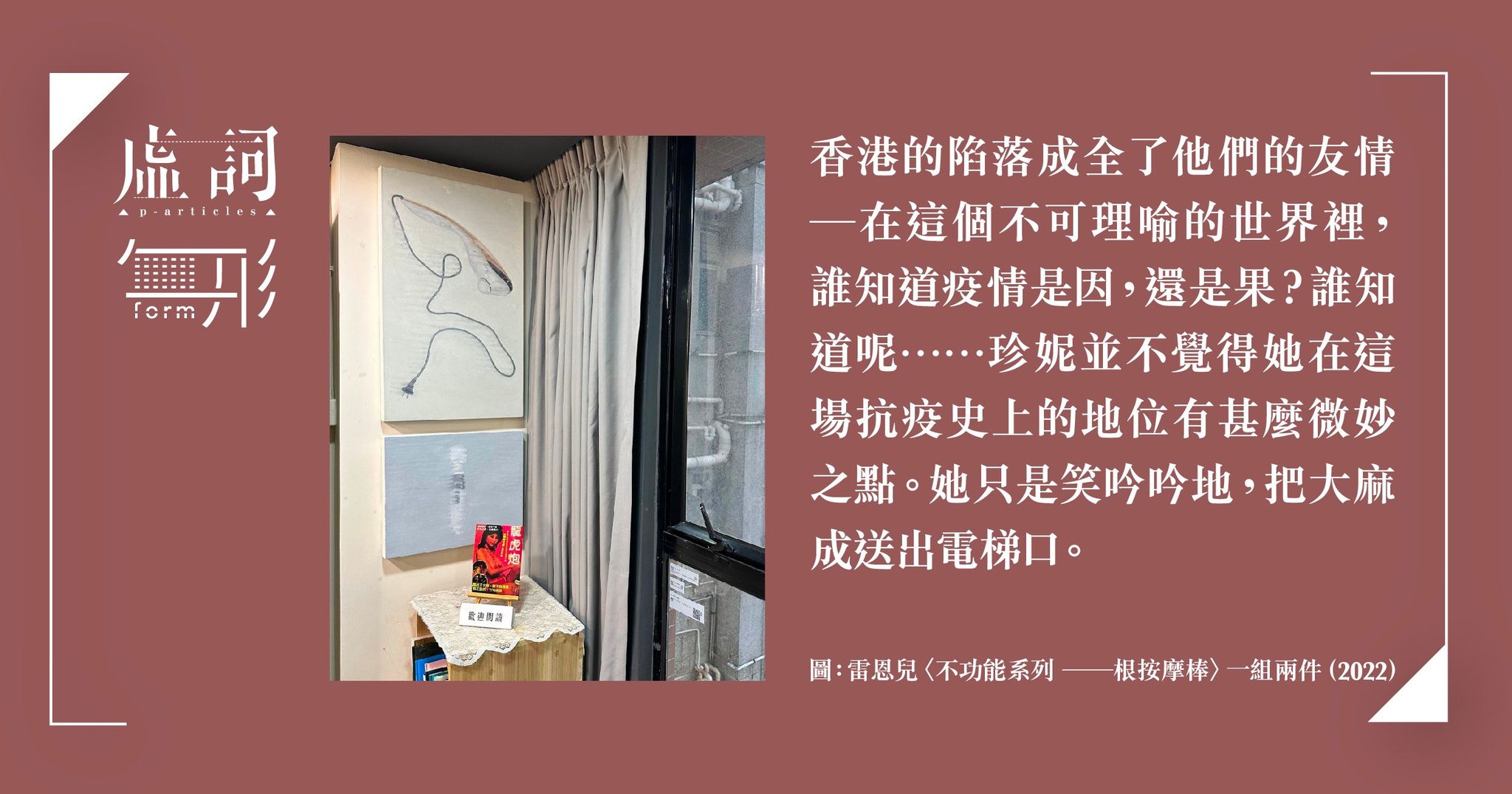【無形.在水中央】傾城之戀2022
(一)
這天早上,大麻成下班了,回家的途中,看見手機內的新聞:他住的那座公屋有人中招,半夜被圍封了。
媽的!就說返工不要烚眼瞓!現在才知道實在太遲了。大麻成當夜更保安,這種工作你唔做大把人做,被圍封幾日無法返工的結果,一定是無咗份工。大麻成住單人公屋,家裡別說貓狗,連仙人掌也沒一棵;於是他決定找個地方落腳,過了這幾天再算。
能去哪兒呢?大麻成阿媽在老人院,朋友也不多,即使有,人家有妻有兒,哪有地方讓一條有中招嫌疑的麻甩佬入去住幾日啊?站在街口前面的垃圾桶,他拉下口罩,點起香煙。後面的小食檔已經開了檔;旁邊「不准泊車」的路牌前一輪豐田停下,拉下車窗,向檔主嗌了聲「三條腸粉,五粒燒賣」。老闆把熱騰騰的食物袋好,走過來遞到車裡。司機看了大麻成一眼,跟老闆說:
「你叫佢戴返好個口罩啦。」
老闆也看了大麻成一眼,說:「佢食緊煙。」
大麻成覺得自己在哪裡都是錯的。他把煙蒂抿熄,想到一個地方:珍妮的家。
珍妮是鳳姐,疫情前,大麻成間中會幫襯,覺得她不多話,很文靜。疫情已兩年,沒見珍妮也兩年了,她還在老地方嗎?會不會忘記自己呢?想到這裡大麻成覺得自己真沒良心—不過是肺炎,他就把珍妮徹底忘了,怪不得當鳳姐的都說男人靠不住。想到這裡大麻成也買了幾條腸粉,廿蚊魚蛋,廿蚊燒賣,兩枝豆漿,上了往廟街的巴士。
(二)
「咯咯咯。」
大清早便有人叩門?會不會是大廈有人中招要強檢?珍妮心裡狐疑,從防盜眼一看,只見熟面口的男人站在外面。
「咦,成哥?」珍妮此刻的訝異比被通知強檢更強烈,「這麼早啊?」
「哦,是。」大麻成嘻嘻笑,「剛好經過這區,想起很久沒見你了,於是買了早餐上來,看看你。」
珍妮看看大麻成手上,果然揪住些食物。但今日還未開工,自己還未化妝,身上T shirt睡褲,牙也未擦。
「啊……有心了,先進來吧。」
大麻成入屋,很慶幸這裡不用嘟APP。珍妮匆匆地梳洗過,給他倒了一杯茶。
「看,我買了些腸粉、燒賣甚麼的,不知道你愛不愛吃。」
珍妮有點感動又有點奇怪:給她額外打賞的客人是有的,但從來沒有人給她買食物。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還是邊吃邊看著辦好。微暖的腸粉沾上足夠的甜醬,燒賣也沒有太多的粉和肥肉。他們默默地吃著新鮮的早餐,一時無話。
大麻成是不知道該怎樣開口。兩年無見,一見面便有求於人,臉子有點過不去;他也沒甚麼能回報的,頂多就是交上這兩天的房租。還有,如果他在的時候,珍妮有客人,他該如何安置自己呢?這些問題都得跟她商量。
「是這樣的。」大麻成喝一口茶,「有件事,想請你幫幫忙。」
借錢?這是珍妮首先想到的。她僅有的兩件金器就在床頭櫃的盒子裡,那裡面還有些現金。大麻成雖然是曾經的熟客,大概還不知道盒子裡的乾坤。
「哎……」大麻成想說,又不敢說。他猶豫的這幾秒鐘,珍妮已經想好了:一千元之內,送給他。一千至三千,寫借據。三千以上免問,她實在沒有。大麻成那時對她客客氣氣的,也有出手闊綽的時候,這是珍妮能力範圍內能幫他的了。
(三)
「係咁既……」大麻成終於想到開場白,「你今朝有看新聞嗎?」
珍妮聞言,便打開電視,只見一大班穿了保護衣的人在某幢大廈出出入入,三數路人則在外面指指點點談論。
「我沒有中招。」大麻成先澄清,「我沒有發燒,也沒有喉嚨痛。我進來前在電梯大堂量了體溫的。」
珍妮看著他,等他繼續說。
「不過…我住的大廈有中人了。」大麻成愈說愈細聲,「就是新聞報道的這一幢。」
珍妮回頭,看見大廈外圍已被圍上橙色膠帶。膠帶隨風飄揚,其實一扯便斷;可是,比膠帶更堅固的,似乎是周遭的氣氛;閘內好些人往外看,眼神空洞,好像橙帶外面是個大原野,看不見盡頭。
「所以,你沒辦法回家,是嗎?」珍妮問。
「嗯……是的。」大麻成本來想說「我把你的家看成自己的家一樣」,但實在太肉麻說不出口。
珍妮不作聲,站起來往房間裡去了。大麻成獨自坐在這小小的客廳,覺得無比的窘迫:會不會是房間裡還有客人未走(雖然通常沒有人過夜),又或者珍妮拿出堀頭掃把來……
珍妮出來了,遞上一包煙。兩個人,各自點火,一人一枝。早上八點半,淡泊的晨曦從窗外照進來,大麻成這才發現,沒化妝的珍妮,吸煙時嘴唇四邊泛了淡淡的幼紋。
(四)
電視傳來輕快的音樂,早晨新聞結束了;大麻成嘴角煙蒂上的煙灰愈來愈長;等這枝煙燒完我就走,男人老狗。這是大麻成在疫情下最後的尊嚴。
珍妮忽然把香煙按熄,隔著一張飯桌的距離,看著對面的大麻成。大麻成覺得這個眼神彷彿從天邊看過來。
「一千元,五天,包食,不包上床。」珍妮說,「如果有客人來,你到街上走走。」
「好好好。」大麻成忙不迭答應。
「一場相識,我也不收你市價的租金。」珍妮又說,「不過是用來多買一份被鋪,煲個湯。」
「這當然是我自己負責。」大麻成也把香煙按熄,好顯得誠意些,「有甚麼地方讓你破費的,你告訴我便可。」
「客甚麼氣,一場相識嘛。」珍妮點點頭。這半年來,鳳樓的生意簡直慘淡;不論大麻成給多少,都是幫補,還讓他欠下一個不小的人情,將來可能用得著。想到這裡珍妮拿起茶杯喝了口茶,為這飛來的運氣慶祝一下。
「你也累了,先洗個熱水澡。」穿著米奇老鼠T 恤的珍妮款款站起,撥一撥頭髮,「抽屜裡有紙底褲,你先用著。我到樓下買套新睡衣。你穿大碼是嗎?」
「是是是。」大麻成也連忙站起來。
「啊對了,企缸去水有點慢,我也沒心思理。或許你順手通一通。」
「好好好。」
「你慢慢洗。」珍妮把風衣穿上,「我買報紙上來給你看。」
掩上大門後,珍妮禁不住掩嘴偷笑起來。
(五)
就這樣,大麻成和珍妮開始了同居(不同床)的生活。
打從老母死後,大麻成就沒跟女人同住過了。至於珍妮,男人如流水,從沒留下來的;也算是新鮮經驗。平時的日間,她多數睡覺;現在,陽光照進這殘舊的房子,她忽然發現原來牆角發黃已久;天花板有水漬;床頭櫃面的防火板撓起了一角。她有點不好意思,只好裝作若無其事,把新買來的床單鋪好在海綿爆了的沙發上,放好枕頭,還在上面灑了點花露水—灑上了她才想起大麻成現在不是恩客的身份,只是手勢慣了。
「你先打個盹,我煮好飯來叫醒你。」
珍妮把窗子打開一條隙,讓空氣流通;然後拉上窗簾,擋著光,好讓大麻成在上班前能睡一覺。大麻成躺在那裡,看著珍妮的背影,覺得有點陌生。之前每次來都匆匆忙忙,幹完就走;加上燈光昏暗,他根本沒看清楚珍妮的身材樣貌。現在,他才看清楚:穿著家常便服的珍妮,看起來比穿喱士睡袍時倒還年輕些;大概四十歲,五呎兩三吋,屁股有點大,顯得腰細。喱士睡袍下的珍妮通常不戴胸圍;大麻成抬頭看看,一個胸圍兩條內褲就晾在窗邊,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款式。
花露水的香味掩蓋了牆角的霉味。大麻成矇矇矓朧地睡著了。
(六)
上班前,大麻成在珍妮的家裡吃了晚飯。平時,他不是茶餐廳解決,便是自己在家煮麵吃;今晚,他看見廚房裡的珍妮忙碌地操作,便自動自覺地把摺枱上的報紙雜物收拾好;清理煙灰盅;抹好桌面,鋪好膠枱布。這些事以前都是老母做的,老母走後他一個人住也不動手。做起來其實也不難嘛,大麻成想。然後幫忙開飯,遞這遞那。珍妮沒有跟他客氣。她知道大麻成有點過意不去;畢竟,像他這樣的一個麻甩佬,對女人客氣並不因為心地特別好,而是臉子上過不去;她必須讓他有點難堪,讓他時時想起自己處於求助的姿態;那麼,五天後,他住的大廈解封了,他的荷包也可能對她解封。事實上,珍妮並不常做飯;她也是獨居,一日三餐隨便應付過去。對上一次煮飯給男人是甚麼時候的事呢?她已經忘了。女人的青春,不是消逝在廚房裡,便是消逝在床上,沒甚麼分別。
當大麻成把蕃茄煎紅衫魚、蒸水蛋和芥菜肉片鹹蛋湯一一放好時,他不由得有點感動。開始的時候,不過是借宿,竟然附送住家飯,也可算是意外之喜;那種感覺,就像在超巿結帳時,才發現買滿二百元有優惠券贈送似的。
「麻煩你了。」大麻成扒了一口飯,說。
珍妮微微一笑,給他勺了些蛋。這一頓晚飯吃得有點沉默。他們好像認識了許久,又好像認識不深;而且,已許久沒跟別人一起吃飯了。這頓飯到底像尷尬的搭枱還是靦腆的初戀?他們兩個都說不上來。
(七)
這晚,坐在保安崗位的大班椅上,大麻成不時提醒自己腰骨要端正,口罩要戴好,向每個進入大廈的人問好,禮貌周周地讓他們量體溫,搓酒精。大部分人都沒理他,也有一兩個太太向他點點頭——這時,大麻成就會起身替她們按電梯掣,方便的話也閒聊數句:「買餸啊?」、「煮飯啊?」,之類。
「肺炎個案數字今日再創新高,錄得二千五百一十二宗案例,其中葵涌嘉港邨嘉喜樓,因進入被圍封的第二日。居民陳先生在電話中向記者表示,他已經向任職的機構說明處境,但老闆表明,如果陳先生仍然無法上班的話,公司必須另覓人手取代。陳先生慨嘆,自己幾次檢測的結果都是陰性,不明白為何要與患病者一同被困,現在更要擔心生計問題。他說,希望政府能體諒香港人搵食艱難,讓他出去上班。下一則新聞……」
大麻成把收音機關上—這幾年,哪裡還有「下一則新聞」?全部都是疫情、疫情、疫情,聽得人都麻木了。這個姓陳的大概是鄰居吧?不知道他住哪個單位?和自己的單位近不近?大麻成想。申請到公屋的時候,所有人都替他慶幸。現在,大家都想逃離公屋,逃離這個城市,去一個可以正正常常上班返工的地方—有沒有肺炎,人還是得吃飯;要吃飯,就要開工。有一句老話:「雷公不打吃飯人」,想著吃飯就是不想死,這樣的人雷公也敬畏幾分。想到這裡,大麻成主動拿起掃把,把電梯大堂的幾張紙巾掃掉,又拿起裝酒精的噴壺,往電梯按鈕和空氣中猛力地噴幾下。
不知道珍妮有沒有開工?有沒有提醒嫖客要先洗手?大麻成並不知道,此刻的珍妮正在換牆紙。她忽然發現牆角發霉的部分很礙眼,便到上海街的裝修店買些零碎的牆紙,自己動手。業主不會理會這些小事,她也懶得跟對方交涉;反正沒有客人,就當是打發時間。
讀書的時候,珍妮喜歡上美術科,繪畫、做手工,都難不到她。美術科老師是唯一一個會稱讚她的老師,也是唯一一個跟她說實話的老師:單單手工好是不夠的,在這個社會中,中英數的成績比美術重要得多。於是珍妮從沒想過能憑手工藝養活自己和家人。能讀完中三,已是珍妮的極限;做過收銀,做過速遞,到頭來是鳳姐的工作做得最長久。打工打得再好,都不過是聽命於人;反而做一樓一,獨門獨戶,誰也管不了誰。這個城巿裡,甚麼人也有,她遇過吃霸王餐的、一邊幹一邊覆手機信息的、幹不成把她罵一頓的、幹不成跟她談心事的……這些年來,累積了客人和經驗,珍妮覺得自己能夠應付的事情愈來愈多。這兩年,生意慘淡,姐妹們有不少早已轉行炒散,或是隨便找個人嫁掉;只有珍妮還守得住,靠的就是經營——很早她便知道賭博和毒品是無底深潭;而儲蓄和投資相當重要;趁著現在清閒的日子,把該維修的地方維修一下,搞好外觀與衞生,也算是出於對工作的尊重—要不,疫情過去了,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準備好過好日子。
珍妮其實沒有想太多。做手工的時候,她的心很安靜。
(八)
平日的下午—「平日」指還沒有疫情的時候—珍妮多數睡午覺,養好精神晚上開工。現在,晚上也空閒得很,日間只好眼光光坐著。大麻成在客廳的沙發上睡得鼾聲如雷,珍妮只好戴上耳機看配音韓劇。
電話傳來響聲,是珊珊的短訊。
「打咗針未?」劈頭便是一句。
「食咗飯未?」珍妮回覆。
「 ???」
「以前問候就係食飯未,而家就係打針未。」
「邊個得閒問候你,我真係問你打咗針未。」
被上司非禮的女主角獨自在房間裡飲泣,男主角在外面趕來。
「無客,打嚟做咩?」
「打咗先有客丫嘛。」
「車!咁個客有無打我鬼知?」
男主角猛力拍門,拍得鬼哭神嚎的。就不知道按門鐘?
「生意難做呀,你幫我寫幾隻字貼門口。」
「寫咩?」珍妮的一手字在行內算整齊,廟街上的「十八佳人」、「三百蚊全套」、「風騷少婦」等,不少是她的筆跡。
「打足三針,任你開心,得唔得?」
「使唔使呀你,做壞哂規矩。」
女主角開門了。
「我三個月無工開啦,就快無錢交租啦。」
「我……我得自己好污穢……」女主角哭訴。
「 ??」
「好啦好啦。」珍妮隨便回覆。男主角摟著女主角,安慰她。
「咁我而家嚟。」
珍妮終於可以專心煲劇了;這才猛然想起:大麻成在這裡!不可以讓珊珊知道!這條財路怎可隨便公開?她跟珊珊還沒好到那個地步。
珍妮回頭看了大麻成一眼,只見他還是睡得死死的。珍妮拔下耳機,過去拍醒他。
「成哥!成哥!」
「啊?」鼻鼾聲停下來,房間忽然很安靜。
「你往我房裡睡去。」珍妮替大麻成拿過被舖,「你睡我的床吧。」
大贈送?不是說不包上床的嗎?大麻成突然清醒過來。
(九)
躺在這張之前已躺過的大床上,大麻成忽然產生嶄新的感受:以往,帶著幾許微醺,大麻成總以為這張床很大很大,是他身為一個男人,蛟龍也似地翻滾的大海;卻原來,沒有了粉紅色的床頭燈與酥軟身軀,這就是一張普通的床,只比單人床大一點,絕對不足以兩個人並頭而睡;被鋪洗得有點舊,也因此很舒服,有淡淡的洗衣粉的清香。枕頭上留有珍妮的氣味—既不是香水也不是胭脂水粉,是皮膚獨有的,溫暖而略帶混濁的氣味。在這氣息中,大麻成想起了一樁樁往事,彷彿謎底一層層揭開—原來,那時完事後,珍妮總是馬上起來洗澡,從來沒跟他一起入睡過;原來那時他上來,珍妮沒給他遞過一杯茶。原來那時他要走了,只是放下錢,沒有說「再見」,也沒有捎點點心甚麼的給她……他們的關係就是單純的生意買賣,貨銀兩訖。
現在,一個疫情爆發的下午,她讓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他聽到外面另有一把女聲,隱約在說「打針」、「嘟機」甚麼的。會不會是有人收到消息,知道自己躲在這裡呢?想到這裡大麻成側起耳朵,只聽到珍妮說「不用擔心」、「不要緊張」、「沒事的」,似乎在安慰也在隱瞞對方…大麻成一陣感動。珍妮,如果確診數字到達兩萬,也許我對你會有一點真心,你對我也會有一點真心……
等到珍妮把珊珊送走後,大麻成已經在床上重新熟睡了。珍妮看著他。男人睡覺得的樣子她見多了,不論高矮肥瘦猥瑣斯文,一旦睡著了,便總是一臉疲累。在這個城市,活著並不容易。現在是下午三點,大麻成的疲累在日光中更是明顯:睡眠不足讓他兩頰起了色斑,而吸煙者的毛孔又特別地大而下垂。珍妮倒是佩服大麻成到哪裡都睡得著。手機上傳來信息,今日確診數字二萬宗,政府和許多大機構要求員工必須打針才能上班,出入商場會抽查疫苗證明。珍妮往窗外望,樓下的露天菜攤比平日熱鬧。還是趕快下樓買餸,省得超巿的客人也來搶一份。
(十)
「葵涌嘉港邨嘉喜樓進入圍封第三日,已經有三份之二的居民完成了強檢,總共尋獲一百五十名陽性個案,其中有五名患者屬於復陽個案。圍封期內,政府派員到訪45戶,當中5戶無人應門,政府提醒沒有應門的居民,在看到政府張貼的告示後,應盡快聯絡政府進行檢查。有居民拍下大廈內的照片,顯示電梯大堂的垃圾車塞滿垃圾,清潔工人來不及清理,衞生情況不如理想……」
大麻成關掉收音機,抹一抹櫃台,跟接更同的同事點點頭,步出大廈門口,才嘆了一口氣。大麻成很少在別人面前嘆氣;以前他覺得這樣做不太吉利,現在簡直是喪氣—一會兒見到姑媽,也不要在她面唉聲嘆氣。
姑媽是大麻成在香港唯一的親人了,不過姑姪的感情一向不算很親密。去年,堂哥移民的時候,曾在電話裡叮囑過大麻成多點去探望她。大麻成聽完也就算了:做兒子的都走人了,他這個做姪兒的又能作甚麼呢?頂多就像以往那年,過農曆年時往老人院一趟。然而,昨天晚上,大麻成卻想起姑媽來了;不知她知不知道要打針?有沒有人給她拿主意?
昨晚,珍妮告訴他,珊珊無法說服在老人院的母親打針,很是苦惱。
「你怎麼看?」大麻成問。
珍妮喝一口清補涼,「都八十多了,或許她情願快點死,總比被關在老人院不見天日的好。」
大麻成在路口的生果檔買了幾個橙,然後跳上往老人院的小巴。
「通融一下可以嗎?」大麻成跟職員說,「我只說兩句,放低兩個生果。」
「不可以,政府規定的,」職員只打開了一點門縫,露出半邊塑膠面罩,「這些時候,誰敢犯規?抗疫是第一要緊的事!」
「怎麼了?我現在不抗疫嗎?」聽著那種口吻,大麻成有點生氣,「我就是來看看我姑媽要不要打針的,你說我不抗疫嗎?」
「總之不行!」職員的聲音隔著口罩與面罩傳來,像低飛的轟炸機,「政府說的了,誰敢犯規?我們擔不起這個責任的!」
大麻成被膠面罩上的反光閃了一下,往後一縮,「彭」的一聲門便關了。大麻成「呸」了一聲,氣息都吐在口罩裡。想了一想,他只好站在老人院門口,給姑媽打電話。
「姑媽!」大麻成對住電話大吼。姑媽已經九十歲了,撞聾,「阿成呀!」
「哦,哦。」姑媽答。大麻成不太肯定是否知道自己是誰。
「你有打針嗎?」大麻成又問,「有沒有人幫你打針呀?」
「甚麼柑?沙糖柑?好呀好呀。」
「不是沙糖柑呀。」大麻成覺得自己快斷氣,「你打唔打針呀?」
「打金?我都無哂啲金囉,打乜?」姑媽在電話那頭咭咭笑,像個小孩。姑媽是有點癡呆了吧?大麻成有點後悔沒多來看她。
一輪無效的溝通後,大麻成只好掛上電話;唯一的收穫是知道姑媽還沒死,聲音聽上去也算精神。大麻成有點心煩,又掏出口袋的香煙;見兩個警察從街尾走來,也就放棄了。
(十一)
圍封已經第三天了,也迎來了大麻成的例假。一覺醒來,天已近黃昏,珍妮正好從外面回來。
「成哥,睡醒了?」珍妮手上挽著幾袋菜,把報紙和一個小膠袋放在餐上,便轉身走進廚房。大麻成打開小膠袋一看,裡面是一隻菠蘿包、一隻雞尾包。
「怕你醒來肚餓,買了麵包,轉頭沖杯咖啡給你。」
大麻成看著蹲在雪櫃前的珍妮:一袋袋餸菜放在她的腳邊,長鬈髮紥成馬尾拖在風衣上;沒有化妝的臉,只有兩道紋過的眉顯出淡淡的青藍色。其實她晚上有沒有客人呢?有沒有別的男人坐過自己用來睡覺的沙發?大麻成忽然為自己的想法吃驚;珍妮的生意跟自己沒關係,不是嗎?
「今晚我放假。」大麻成說,「我們……我們到外面走走,好嗎?」
珍妮轉過頭來,看著他。大麻成穿著背心內衣,孖煙囪,夾著一雙人字拖。珍妮提醒自己,這個男人跟其他男人沒兩樣;他們大多數心腸不壞,有時會有突如其來的善意,只是這些善意多數無法持繼太久。
「現在外出很不方便呢。」珍妮關上雪櫃門,「餐廳沒有夜巿,其他地方即使開了門,也要打針,嘟app,量體溫甚麼的。」
大麻成一時間搞不清楚,珍妮算是答應了還是拒絕自己的邀請。
「不過既然成哥有興致,那就去吧。」珍妮站起來,走進房間換衣服。經過大麻成身邊的時候,她不忘向他微微一笑—可能是出於職業上的習慣。
大麻成和珍妮沒想過,這一晚的假期,原來一大考驗。
(十二)
大麻成已許久沒跟女性出外約會了。在他幾十年前的記憶中,跟女士約會,應該由男性作主的。於是他帶珍妮到戲院,到達的時候才知道戲院關了門。
「哎呀,」珍妮嘆口氣,「太可惜了,我很久沒看電影了。」
珍妮的失望倒是真的。因為工作,大麻成和珍妮見過各式各樣的人;但除此以外,他和她平時沒甚麼社交生活,並不知道戲院因為疫情的緣故停止營業。
「那麼……唱K也是不行的了。」
「唱甚麼K呢?現在流行曲我一點也不懂了。」珍妮笑道。
大麻成騷騷頭。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安排好節目。
「先吃飯?」
「餐廳沒夜巿呀。」
「那……我們做甚麼好呢?」
「急甚麼呢?」珍妮撓住大麻成的手臂,「我們有的是時間,索性邊走邊想,不好嗎?」
大麻成其實有點不好意思;珍妮既不是女朋友更不是老婆,讓熟人撞見的話該如何解釋呢?可是他也捨不得推開她。畢竟,珍妮為了跟他外出,換上了連身裙,頭髮梳成一個髻,而且塗了一點脂粉;他總不能辜負她這份心意。
以往,來找珍妮的時候,都得穿過廟街夜巿。兩排開滿大排檔,鑊氣與人聲混在一起,滿街鬧哄哄的。現在,大排檔都不營業了,煲仔飯與薑葱蟹變成廿八元一盒的兩餸飯。燈火照樣通明,門外也有人排隊;大家戴著口罩買完就走,比以前安靜多了。
「其實如何想出這麼多菜式?」大麻成找些話題。
「再多十來樣也無所謂呀,反正都是同一個湯勺同一個芡。」珍妮答。
話雖如此,大麻成聞到這油膩的氣味,還是不爭氣地肚餓了—可是他不想吃兩餸飯—平時還吃不夠嗎?今晚大麻成想體面些。
「聽說剛開了間新的西餐廳,外賣八折。」珍妮彷彿知道他在想甚麼,「就在前面的後巷。」
珍妮口中的「西餐廳」其實是一間咖啡店:店名是英文的,米白色的門口掛上木製的風鈴;旁邊一排花圃,插上幾枝乾花草。門上的玻璃透出一點微黃的光,好像稍為大聲的說話也會把這光碰碎。大麻成和珍妮站在門口,覺得這間店與廟街格格不入,而自己又與這間店格格不入。
大麻成小心翼翼地推開門;沒有客人的店面,只得兩個後生,一個在水吧後工作,一個在掃地。裡面的兩個與進來的兩個對望了一會。
「買外賣嗎?」掃地的問。
「嗯……是的。」大麻成答。
「吃甚麼?」後生把掃把放好。
「嗯…你們有甚麼?」
「你可以試試我們的手工意粉、手工咖啡和手工啤酒。」
哦?大麻成又愣住了。
「不如你介紹吧,我們第一次來。」珍妮說。於是後生給他們說了些菜名。
「我覺得都很好呢,不如就讓他們拿主意吧。」珍妮轉向大麻成。其實他們都聽不懂那些意大利名字。
拿著兩盒有點貴的意粉與兩枝啤酒,大麻成和珍妮在榕樹頭天后廟前坐下來開飯。食物的味道不錯;人少,坐在這裡,竟也感到樹下吹來的涼風。
「平時這裡有個唱粵曲的。」
「上個月返鄉下了。」
「噢。」
「夠飽嗎?要不要加點牛雜?」
「夠了,不用了。」
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話題漸漸地寥落了;沒有性愛,沒有消費的地方,甚至沒有柴米油鹽,這一夜遂成為一雙男女最漫長的光景。然而,就像珍妮說的,他們有的是時間;十字路口的汽車,閃著紅色白色的車頭燈,一輛一輛地駛過;路口的排檔開檔了,沒有遊客途人也很少,但生活還是要過下去;於是,各種莫名其妙的雜貨、玩具、衣物,在白色燈光照耀下便顯得份外俗艷,像要盡力向世界展示其自己的存在。一個老伯經過,手裡拿著一個背心膠袋—全香港的老伯都愛拿著紅色的背心膠袋,裡面是銀包、長者電話,與揉成一團的心事。背著燈光,大麻成看不清老伯的樣子,但心裡卻不期然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這樣。
「我想去算命。」珍妮忽然說。
大麻成看著啤酒,看著她。
「會不會有點儍呢?幾十歲人。」珍妮在夜晚的空氣中微笑。
大麻成想了想。
「就是因為幾十歲人才去儍一次,不然就沒機會了。」大麻成對自己睿智的回答十分驚訝,彷彿是那個貴價的意粉在產生了作用。
(十三)
榕樹頭的算命攤檔,並沒有因為疫情而減少;相反好像還多了幾檔。也對,走運的時候,誰想到算命呢?現在,珍妮眼前的攤檔,有看掌的、看相的、看八字的、紫微斗數、星座星盤,還有塔羅和水晶球。甚麼「男人斷掌千斤兩,女人斷掌過房養」、「眼秀睛紅潤有砂,睛圓微露似桃花」,她有點聽膩了;剛好前面有個塔羅攤檔,坐著一位看起來頗時髦的女郎,綁著頭巾,領口有大幅的荷葉花,一雙耳環垂下來搖晃;珍妮便在她面前坐下來。
「想問甚麼?」女郎問。近看才發現她年紀不算小,眼睛細長,眼皮有點腫,嘴巴在口罩下,看不到。
「嗯……」珍妮一時間竟想不出有甚麼想問,「自身?」
女郎洗好牌,把牌攤開成扇形,讓珍妮抽一張。
「不用思考,憑直覺抽一張,塔羅牌讓你聆聽內心的聲音。」
珍妮想笑,但還是忍住了,隨便抽了一張牌。女士把牌翻開。
「Lovers,戀人。」
珍妮忍不住回頭,看了大麻成一眼。大麻成拉下了口罩,在不遠處的垃圾桶前抽煙,似乎沒聽到她們的對話。
「是甚麼意思呢?」
「很多人都以為戀人牌一定跟戀愛有關,其實不一定。」女郎的手指尖在牌子上劃過,「戀人牌也可以解作結盟、合作的關係。」
珍妮把戀人牌拿在手中細看。
「這是一雙赤裸的男女,分開站著,」女郎說明牌上的畫面,「他們對彼此坦誠,但又不算很熟絡親熱。上空是天使,看著他們。」
「哦……」
「短期內,你可能要作出重要的選擇。」女郎盯著珍妮的眼睛,「你要做好理性與情感之間的平衡。」
風有點熱,也有點垃圾的氣味,提醒珍妮自己正身處現實。她站起來,說聲「謝謝」,付錢離開。
「來吧,我請你吃甜品。」珍妮回到大麻成身邊,「買外賣,回去吃。」
他們來到鵝記門口,珍妮一口氣叫了喳咋、涼粉和芝麻湯圓。大麻成覺得她算過命後,心情似乎很好。
大麻成和珍妮回家後,吃了甜品,洗過澡,互道晚安,各自睡了—沒有想像中的纏綿悱惻;對珍妮來說,跟男人吃喳咋,比上床浪漫得多了。至於大麻成,他對於自己這個晚上的表現有點驚訝:即使稱不上風度翩翩,也總算斯文有禮吧?這種自覺令他吃完甜品後自動自覺地洗好碗,看見珍妮從浴室裡出來時打著呵欠,主動跟她道晚安。他好像第一次發現自己也能細心,能體會別人的感受。躺在沙發上,大麻成一時間睡不著;轉過身來,看見自己的底褲和珍妮的底褲晾在窗邊輕輕地擺蕩;渾圓的月光在擺蕩中時隱時現,好像要穿過這個塵世,微笑著,看著渺小的凡人。事實上,剛才風吹過,隱約把珍妮與塔羅師的對話,吹到大麻成的耳邊;他不知道塔羅靈不靈,反正「舉頭三呎有神明」,總有一個天使或觀音甚麼的。從前,大麻成以為這話叫人不要做虧心事;現在他覺得,這話大概還有「命中註定」的意思;如果不是疫情,不是圍封,他怎會到珍妮這裡來呢?他怎會發現自己能照顧人,也能被人照顧呢?
疫情前,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人。但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只能容得下一對平凡的男女。
「嘉港邨嘉港樓在圍封五日後,將於今日下午解封。有居民表示心情十分興奮,會馬上返工,希望僱主能體諒;也有人表示已經習慣圍封的生活,對於政府在圍封期間派發的罐頭、飯盒大致滿意,不過如果能送上新鮮蔬菜就更好……」
大麻成「噗」一聲笑出來,幾乎把菠蘿包皮噴在珍妮臉上。
「唔好意思。」大麻成連忙喝口茶,把麵包送進胃裡。珍妮也笑了。
「夠飽嗎?給你煎隻蛋?」珍妮伸出沒有寇丹的指尖,把嘴角的牛油抹進嘴裡。這個動作到底是誘惑的性質還是知慳識儉的舉止?大麻成沒有多想。
他們沉默著。大麻成盯著桌面上的麵包碎。下次還是應該用小碟托著吃,不然至少用手,他想。他心裡明白,圍封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下次坐在這張餐桌前吃早餐,會是甚麼時候呢?想到這裡,大麻成感到胃酸有點上湧;他又喝了一口茶。茶包泡得久了,茶水有點苦。
「你這裡的租金,一個月多少?」大麻成鼓起勇氣,問。
「六千五。」本來七千五,我跟業主說,這半年生意實在差,不減租我就走佬。他答應了。」
珍妮回答的時候,眼睛盯著電視新聞。她不是不記得,當初大麻成要來暫住時,她千方百計地讓他以為自己會影響鳳樓的生意;只是經過了這幾天,她覺得事情其實也瞞不過去—大麻成又不是儍子。況且,像大廈圍封這種事,一生人中會發生多少?下一次會是甚麼時候?可能是下星期,也可能以後也不會發生;大麻成還會不會來暫住?可能是下星期,也可能以後都不會。
「租金不便宜呢。」大麻成又說。
「差不多啦。」
電視繼續播放疫情新聞。主播說,政府準備了大批福袋,在嘉喜樓解封後送給居民,裡面有罐頭鮑魚、冬菇、臘腸等。
「你有份嗎?福袋。」珍妮回頭,目光恰好碰上大麻成的眼睛。空氣忽然凝固了;主播的聲音變得遙遠,好像一個不相干的人,對著遼闊的草原,訴說自己與別人無關的生活片段;一陣乾燥在兩人中間漫延開來;晨曦照進,好像要把這乾燥燃燒。
「不如你搬來,跟我住吧。」大麻成吞下一啖口水,「公屋,租金便宜。」
珍妮看著他。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分擔租金,」大麻成覺得自己好像說錯了話,著急起來,「租金,我會付的。我的意思是……嗯……把你的名字加入戶口……」
珍妮看著大麻成,看著他鼻頭冒出的一滴汗珠。感動啊!活到這把年紀,感動本身就是稀罕的,不管甚麼原因。單憑這一點,珍妮會記得這名恩客,永遠永遠。
「成哥。」珍妮坐直了身子,「這幾天我過得很開心。」
大麻成低下頭來。眼前的菠蘿包碎,在陽光下閃閃動人。
「你知道,我是獨門獨戶,慣了的。」珍妮仔細地考慮用語,「怎麼說呢,就好像,出入自由,不會被人圍封,也不會圍封別人的,那種。」
大麻成想了一會,先是跟自己點點頭,然後抬起頭,看著珍妮,臉上掛上無聲的笑容。
「我明白的。」他說,「即使有福袋,也不會有人想被圍封。」
話畢,大麻成覺得自己好像在這幾日間變聰明了!在這種不免尷尬的情景中,他竟然接上了珍妮的話!這個既大方又幽默的自己,是他以前想也沒想過的。
「謝謝你這幾天的招待。」大麻成站起來,由衷地說,「我真心希望你的生活開開心心,啊,應該說百毒不侵。」
「大家咁話。」珍妮也站起來,伸出手。兩個人的手握著,像一宗合作的結束,雙方都感到十分滿意。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們的友情—在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疫情是因,還是果?誰知道呢……珍妮並不覺得她在這場抗疫史上的地位有甚麼微妙之點。她只是笑吟吟地,把大麻成送出電梯口。
到處都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電視新聞的消息還是嘩啦啦地吵著,在沙發上未摺好的被單表面,流過來,又消失了,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完)
水字部:文學 X 藝術 計劃
漬|雷恩兒 x 張婉雯
閱讀時代
太子道西162號華邦商業中心1102室
日期:2022 年 12 月 10 日 至 2023年 1 月 10 日
時間:星期一至日下午 1 時至晚上 8 時
張婉雯〈傾城之戀2022〉
作家簡介:
香港作家,著有散文《參差杪》、《你在——校園貓的故事》;小說《那些貓們》、《微塵記》、《甜蜜蜜》。曾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奬。
雷恩兒〈不功能系列 ——根按摩棒〉一組兩件(2022)
藝術家簡介:
1997年生於香港,目前於香港生活與工作。她於2020年在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獲得學士學位。透過素描、繪畫和錄像裝置等媒介,她目前的實踐大多關注於日常世界和生活經驗的現成物件及其物質文化,並體現了物件的存在價值及人與物件之間的親密和聯繫。
她的作品曾在香港、瑞士和台灣展出,包括布朗畫廊(香港)、李安姿當代空間(香港)、德薩畫廊(香港)、Wure Area(香港)、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香港)、Kino Roland(瑞士蘇黎世)和靜宜大學藝術中心(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