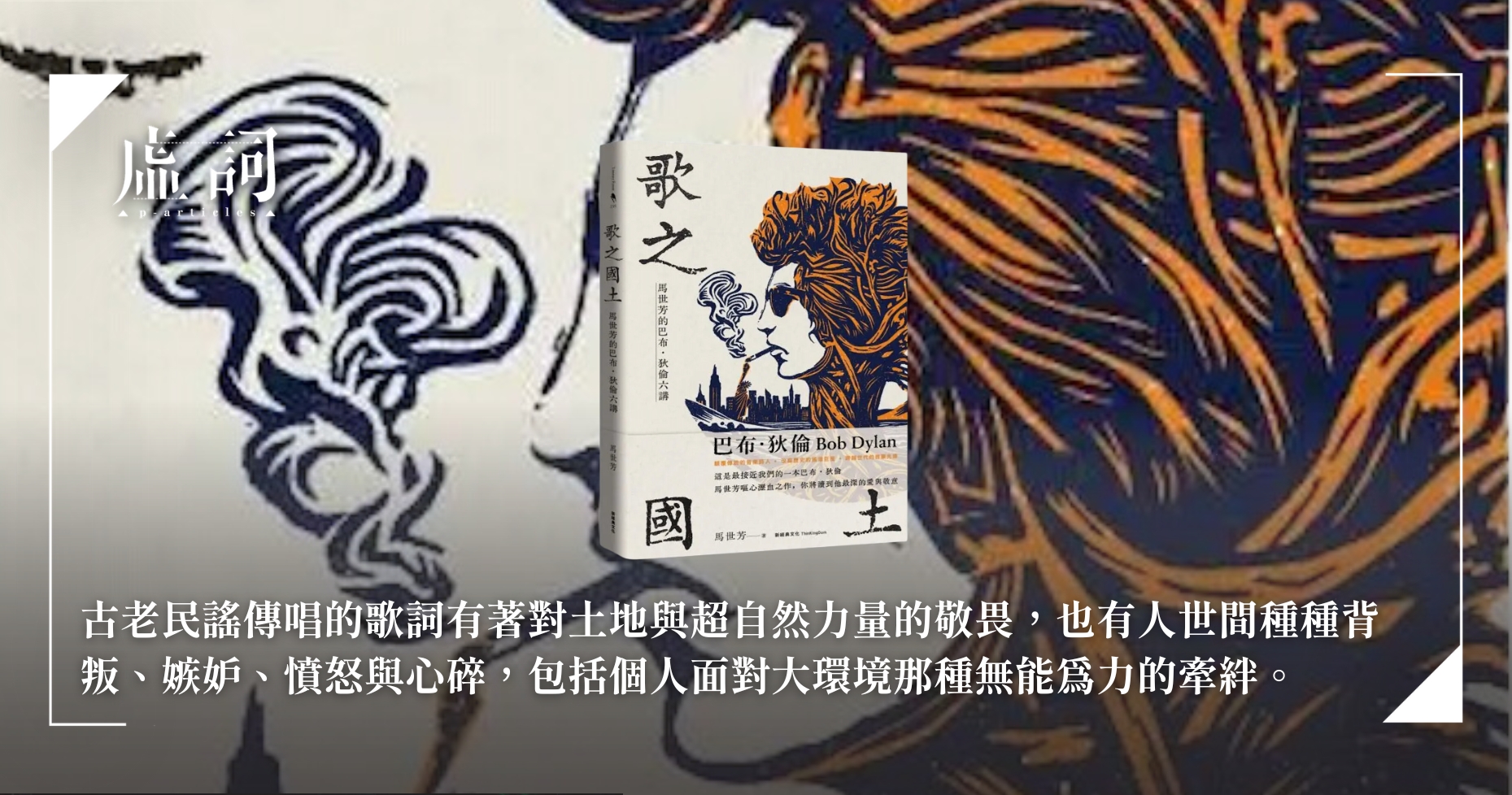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雙城記 ─序郝譽翔《城市異鄉人》
書序 | by 陳芳明 | 2025-02-03
重新回望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隨著運動而陸續浮出歷史地表的作家,距離今天已經整整一百餘年。這樣的歷史縱深,確實需要一定的洞見,而且也需要在眾多史料中慢慢爬梳。 (閱讀更多)
離散時代再思香港身份:新讀李宇森,舊憶阿巴斯
書序 | by 羅永生 | 2025-02-01
筆者在2020年首次為李宇森的新書《主權在民論》寫推薦序,繼後在2022年,他接著出版了《主權神話論》。今年2024,李宇森又推出新著《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短短四年之內,作者已迅速完成了「否想主權三部曲」的系列,證明了他用功之深,涉獵之廣,實在可喜可賀。 (閱讀更多)
《康拉德手札》導讀——人生故事裡現身的主人翁
書序 | by 鄧鴻樹 | 2024-12-29
《康拉德手札》是康拉德唯一一部沒有扉頁獻詞的作品。肯定還有一個真正的「他」不願在現實世界曝光。不過,本書刻劃他的各種分身,皆以不同面貌掙脫往事的漩渦;他們的目光共同指向一名呼之欲出的主人翁。這名主角雖然在自己的人生故事裡缺席,卻早已現身於作家寫下的千百頁故事裡,在遙遠的異域落地生根。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