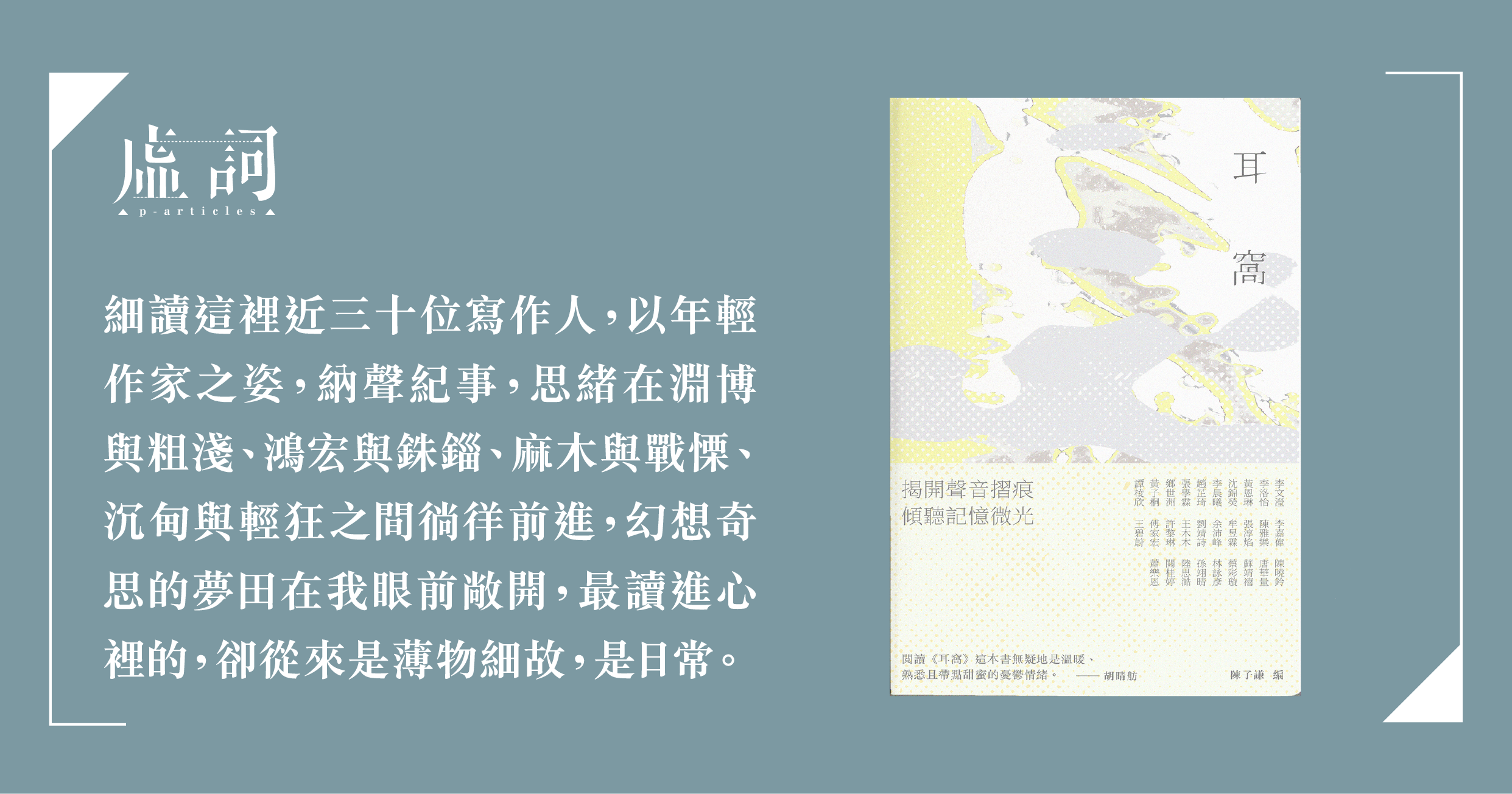【新書】《耳窩》序——一種脫序的紀事:囚豢窩內,考掘聲音
以聲入文,關切的卻不止聲音本身的事體,書寫聲音,實在是我們如何觀察日常。
三十位年輕寫作人的聲音合集,以犀利的筆觸擊透浮躁現實,將可能是我城的、個人的最深層的紊亂和雜音,鉅細無遺抖落給同處這個時代的你和我看──傾聽的、竊聽的、隨聽的、落聽的,聲聲入耳。
以窩入題的聲音宏篇
以窩入題,指的是聽覺感官的天然凹隱──耳窩,窩廣義上又指洼陷藏匿之處,洞穴,我們每個人都有心靈藏匿的洞穴。在窩裡,我們梳順自己的肌理,找方式與世界相處。在窩裡,有人造出桀驁不馴、與外面世界扞格不入卻劃穿時代的設計。在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這本紀錄城市碩大而無常的「神話之書」《譫狂紐約》對「窩穴」有一段書寫。十九世紀被譽為「上帝的建築師」的安東尼奧.高迪(Antonio Gaudi)在巴塞隆拿受到美國一群商界巨賈的委托為曼哈頓設計一棟大型酒店,當時委約的階段連建築地點都未有定案,商人們對這項目的豪言壯語和寄願洋洋滿耳,對當時困圄在封閉歐洲的高迪來講,無異於向「住在柏拉圖洞穴寓言裡的男子」傾訴建築理想。而他能做的就是以建築師的本能直覺,盡於捕風捉影中挹注想像,重新築構一個洞穴外的現實。高迪最終交出的設計圖,讓大樓看來是一綑神秘的石筍,既是正格的摩天大樓,又是包涵劇院、展覽廳、瞭望球與辦公空間五臟俱全的圓錐體塔樓,展現了高迪的歇斯底里與曼哈頓的癲狂的契合。「窩穴」般的大樓設計因種種理由沒有被實現是後來的事,這個逸出常軌的設計卻被經年轉載,讓一代設計者盡情乖張。《耳窩》所載的近三十篇作品,有著不同的文學辭令,抱揣不同的聲音臆想,每篇獨立成章,扣住「窩」字一義,濁世環伺裡找一個容得下以傾聽為觀察方式的角落,卯盡文字,挑戰書寫的條條框框,藏掖在不停咀語難以觀聽的囚豢之窩以內,放心對域外妄想乖絕,因為有了「窩」的束縛,寫作才自由,思疆不受限。文字是一種聆聽的延伸,二十多位城市觀察者,以書寫訴說想像之契闊。
最大的聲音是靜
以聲入文,從來是一體兩面,我們以為述寫聲音總是不停地、巧舌如簧地交纏著,詩意地、聒噪地進行著,卻回溯過去,我們注意到聲音的那刻,往往是聲音戛然而止的那一瞬。眩光處處,萬籟俱寂,腦海有聲遽然而來,「寧」與「聽」,總是交織。無論是〈家常〉裡「呼嚕嚕呼嚕嚕 / 出逃 / 刻意疏遠又無處不在」的聲音、〈傾聽蜻蜓〉裡「散著燃燒殆盡的音波」、〈葬語〉裡「如時間一般滑溜地離開」或聲或影,又如〈門外〉裡「密匝匝的 / 兵荒馬亂 / 殺個滿目瘡痍」的吵鬧,援引不盡,所有聲音都因為消弭了,不再迴盪於一室空廓中,卻在記憶的夢田裡愈發清泠,悠遠而來。蕭紅最為人熟知的作品《呼蘭河傳》有那麼一段記述了故土的龍王廟,廟的東隅有一條「東大橋」,因冤魂枉鬼的傳說,晚裡繞惹怖慄的鬼鳴,有若「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的哭」,蕭紅這樣寫:
有人問她哭什麼?
她說她要回家。
那人若說:
「明天,我送你回去⋯⋯」
那白兔子一聽,拉過自己的大耳朵來,擦擦眼淚,就不見了。
若沒有人理會,她就一哭,哭到雞叫天明。
靜,是深沉的蟄伏,再鋪天蓋地的囂躁,在奇雄幻變的世間,都不能被服膺消化,只能落為餘贅,只有聲音得到了在意,於是靜。
細讀這裡近三十位寫作人,以年輕作家之姿,納聲紀事,思緒在淵博與粗淺、鴻宏與銖錙、麻木與戰慄、沉甸與輕狂之間徜徉前進,幻想奇思的夢田在我眼前敞開,最讀進心裡的,卻從來是薄物細故,是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