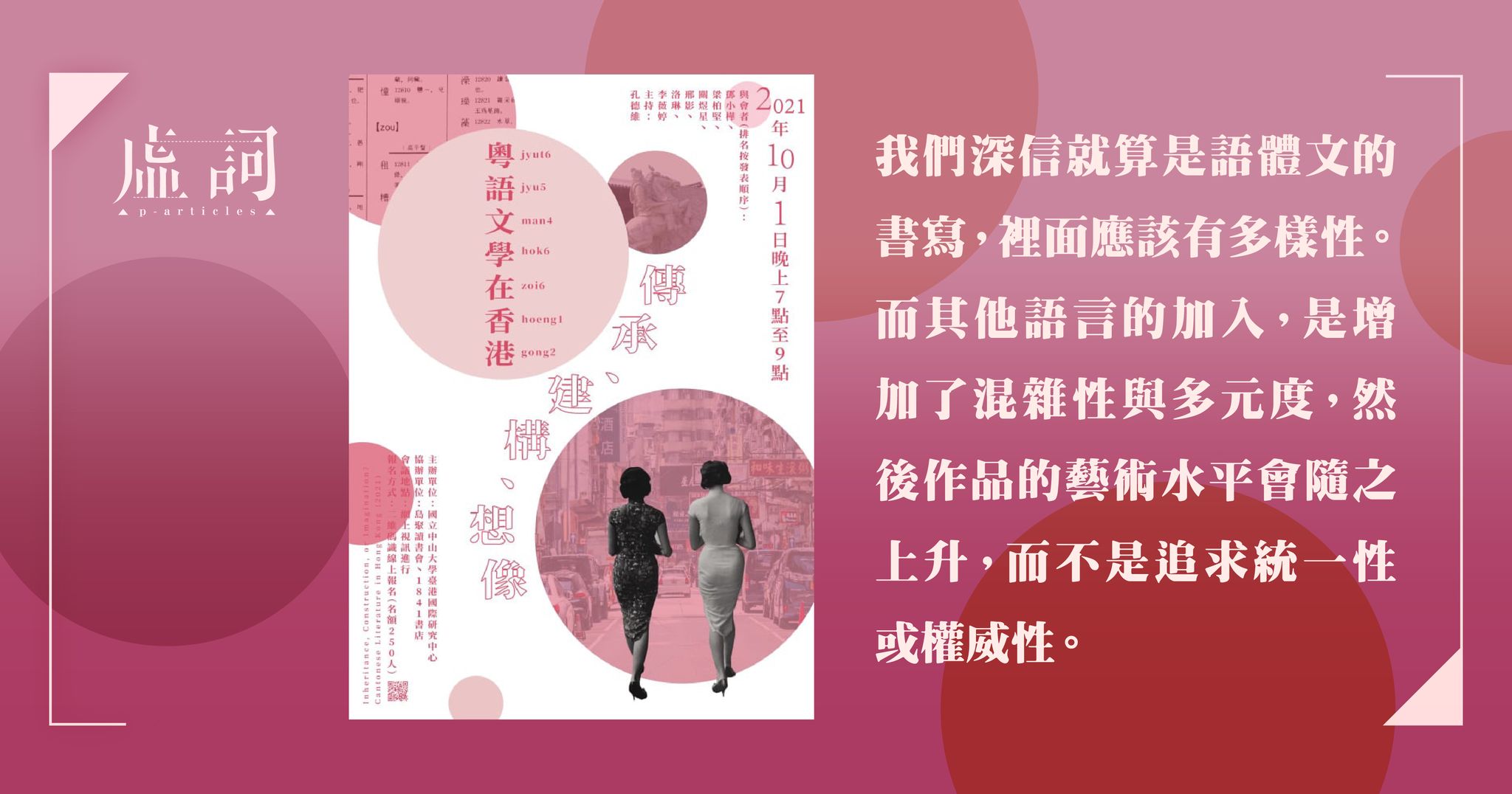粵語的多元與歷史——「傳承?建構?想像?粵語文學在香港」對談整理(二)
報導 | by 國立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 | 2021-12-03
會議日期及時間:2021年10月1日(五)19:00-21:00
會議地點:網上視訊進行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
發表人:
李薇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
邢影,《伊索傳·驢仔》譯者
洛琳,文學評論人
梁栢堅,填詞人
鄧小樺,香港文學生活館
關煜星,《迴響》
(按筆劃排名)
主持人:
孔德維,臺港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
會議紀錄義工:
Pony(逐字稿)
梁悟心(逐字稿)
梁嘉軒(逐字稿)
Edmund Chau(華語翻譯)
(編按:「傳承?建構?想像?粵語文學在香港」之整理稿,虛詞分三篇發表,本篇為第二篇。以下為李薇婷及鄧小樺發言,及發表人之間圓桌討論環節。)
李薇婷:(華語)我現在先講一下,我發表的語言會用比較台灣腔的普通話,到了一些粵語的文本的話我就會唸粵語。很有趣的是我準備了幾頁Powerpoint 給大家,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較早期的時候,到底廣東話是怎樣進入創作的。我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回答大家很專業的問題,比如說白話文運動中的「我手寫我口」,事情能不能適用於(applicable to)香港。可是在我自己的觀察裡面,我覺得他們對於粵語有一種還蠻複雜……我說的是清末的香港,他們對於粵語還是有一些比較有趣的想法,但是他們也是很盡力地去推廣我們現在覺得是「粵語」的這個部分。最近不是有一齣《1921》的大電影要上映嗎?然後我就跟我朋友分享了,因為他知道我今天要分享黃世仲、黃伯耀兩個人。他們兄弟倆以香港作為一個小小的基地,然後幫同盟會發了很多報紙,他們很早就期望要建立一個以粵語來溝通的文學。然後我覺得可以回答兩個問題:因為我們的母語是粵語,所以很直接就一定會用粵語溝通,可是當他們有了一個文學的意識,然後有一個文學的想法——「我們創作也要用粵語了」,那就是另外一個情況了。
另外就是說(簡報中的圖片)這個是《十月圍城》,這個畫面就是黃世仲要去保護那些印刷機,以免被那些……因為他們一直在反帝反清,也反殖,所以就怕印刷機被查封。從這裡說起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粵語」其實是一個蠻……黃世仲這個人是一個非常政治的人,所以粵語一開始就是很政治。他們在1906年開始創辦《粵東小說林》的時候,其實是在廣東。廣東一帶有自己的口音,因為嶺南很大,因此粵語也很大,其實廣東話跟我們現在講「香港話」,譬如說有一些本地的群體說我們有「香港的粵語」,跟「廣州的粵語」不一樣。然後可能跟馬來西亞、新加坡用的粵語也不一樣。所以這個情況其實在清朝的時候也發生,他們就像是每一種語言都會有他們的口語跟書面語的表達。在這方面他們倆兄弟就做了很多事情,他們真的嘗試同時用白話與文言作為創作語言。因為他們都是想要去考科舉,可是失敗了。可他們也是文高八斗,於是就往南方發展。他們也是可以用兩種語言去書寫的人,也是有點像我這種傳統中文系出身的,那我要學普通話,或是真的要去懂書面的書寫,或是說廣泛而言書面的表達是怎樣的。可是那跟我的口語很不同,他們也面對這種情況。對他們而言「白話」這個詞,不是五四裡面我們說的「白話文」。因為五四的白話文, 1919年以後就是把一些語體文,也就是說每一種語言的口語,提煉成一種更純粹的語言書寫方法。他們裡面說的「白話」,就真的是廣東、閩南地區他們有一種「廣東的白話」,他們可以共通的一種白話。然後就開始去翻譯,還有創作一些很有趣的,像「談風」、「班本」、「粵謳」等民間通俗文藝。而且他們自己會去寫一些詼諧的文章(「諧文」),取笑英國殖民地政府,也取笑清政府。他們也會創作一些「南音」,或是「龍舟歌」,那些其實都是一些民間的歌謠。到了清末的狀況,他們到香港之後其實還蠻努力去辦雜誌,發表了很多年。
到香港之後他們也有一個想法:我們為什麼要創辦這份雜誌——就是要日益求精。他們要去精進的是「白話小說者,則又於各體小說之外。而利用白話以為方言之引掖者也,姑無論其為章回也,為短篇也,為箴時與諷世也,要均以白話而見長矣。(註1)」他們在說的時候,其實根本沒有針對北方的政權。他們要處理的是去思考「閩南的人怎麼想」,這其實並非什麼新發現,可是黃世仲跟黃伯耀兩個人其實年輕的時候科舉失敗了,然後第一個到的地方並非香港,而是吉隆坡。黃世仲去當賭場書記,那時候他們已經知道很多當時去南洋找工作的、以粵語為主的離散群體,會共用這個「白話」,也會做一些文學創作。回到香港以後,他就覺得「既然現在大家都用『官語』,沒有人會為在南洋的人考慮,那不如我們就用白話來創作!」於是他接下來就去說很多關於「小說改良」的事情,這個「小說改良」其實一點也不新,因為它就是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說法。他自己加了一些東西,因為他創作戲曲與南音,所以就覺得說「不如我們也去改變戲曲吧!我們就能更有渲染力,能夠讓他們感受到很多粵語民間文藝同時,也能以他們的手寫他們的心,我們就能團結。」
《中外小說林》來到香港以後,借助香港的發表網絡,像以前香港的第三波黑死病,鼠疫的傳染路線就是新加坡、馬來亞、舊金山等地方,後來黃世仲也當然是在這些地方發表《中外小說林》,所以《中外小說林》的讀者群跟今天《迴響》蠻不一樣。《中外小說林》就是靠馬來亞或是南洋的群體來消費然後延續下來,因為當時他們也沒有錢。接下來譬如他們的戲曲中是如何去說廣東話呢?就像是會一些白話的表現,譬如說:「你個奸賊呀奸賊。你早知今日。何苦當初。你今日死期已至。待姑娘把你數臭一番。等你死也心息。(註2)」這種文學表現在1906、07年的香港是蠻驚訝的。黃世仲的例子有回應到一些離散(diaspora)的問題,可是他們在廣東的認同也蠻強的。當時在香港常說要以白話來講話,來取笑殖民政府、來反帝。他們運用在「排演班本」之中,「班本」其實就是粵劇演出的稿子,因為戲子們的語言能力有限, 所以就用口語的方式呈現,他們看了就能排練,(班本)也刊登在《中外小說林》上。另外譬如說黃世仲的弟弟——黃伯耀,他也是一位創作者,後來(沒記錯的話)就一直留在香港的一間書院教書。有趣的是他們也會創作「南音」,簡單介紹「南音」就是廣東人會唱的音樂(註3)。最後他們到底如何看待廣東話的身分呢?他就說「我與諸君都係廣東嚟,自然係親密的,即相酌道理,亦較之易的既⋯⋯我地的華僑,寄身在外埠,受人政治,供人使喚,重邊得能令人睇得起呢?(註4)」所以他們對粵語的運用非常有意思,因為他們把文學當成政治一部分。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這些非常有趣、我看到的廣東話的表現,它是在1910年以前的吧,大概就是這樣。
孔德維:好,非常感謝。那我們預留一點時間給我們的文壇前輩,鄧小樺女士,你如何看待這幾年忽然不斷提倡有「粵語文學」這一種說法?會覺得是一種斷裂,還是一種延續(continuity)?
鄧小樺:我在七〇年代末出生,在香港創作以及寫評論,還有辦幾份文學雜誌,所以可以補充一些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是從差不多大學畢業以後開始教寫作班,就是在中學的寫作班中,那時候我已會有一堂課專門教粵語寫作。譬如那時候我教的是像謝立文(「麥兜」的創作者)、或一些寫得不錯的部落客,還有會教「粵謳」。我一直有寫一些文章去爭取粵語的地位。剛才孔德維問我們這波粵語文學的興起與之前有何不同,粵語這個問題是涉及法定官方語文的相互角力,它一直都有種政治與美學的交混(mixture),這幾波我相信其實都蘊含著政治與美學的追求。而因為我們研究的已經是歷史,可能那時候他們會覺得還蠻政治性的,但現代流傳下來、讓我們看到的,通常都是美學上的追求比較多。因為從一開始,寫粵語其實已經有一定的政治性,但是經過文學歷史的「淘沙瀝金」,剩下來的都是美學追求上比較突出的,不是最暢銷的,而是有其美學上獨特性、代表性的高度。我們目前身處的這波粵語運動,其政治性當然也非常強。我對政治性的部分並非不同意,只是在學習上我對美學性的著重比較強,而且對政治與美學的交界點比較敏感。因為從這些交界點就可以看到我們如何去面對一個世界、或是產生中的新事物、或是一些邊緣的事物,感受得到我們的質地與底氣。
譬如說,像要爭取粵語成為官方語言;它要有規範性、權威性,這些部分其實是從語文的角度去衍生出來的規範性,然後指向權威性,其實也就是一個權力鬥爭(power struggle)。關於這一部分,我只能說如果爭取到的話,我當然是樂見其成,但我本人作為作家,就未必會加入去塑造權威、或打造規範的過程。因為從美學性的角度而言是另外一些標準:行文、語言、文字編排、表達,全都有一個關於藝術的意識,以及希望表達予受眾的意識存在(即希望受眾獲得甚麼),而意識會有高下之分。我想大部分香港作者所抱持的觀念是甚麼呢? 譬如我們不會講求純正性,而是追求混雜性(hybridity)。為甚麼那時我在中學不是教學生要「拔尖補底」、要寫好描寫文,而是教他們粵語怎樣寫?是因為我們深信就算是語體文的書寫,裡面應該有多樣性。而其他語言的加入,是增加了混雜性與多元度,然後作品的藝術水平會隨之上升,而不是追求統一性或權威性。就像某些「語文權威」教學生不要寫粵語,因為那樣不是「純正的白話文」。其實我是採取一個邊緣的角度來反對那種權威的論述以及思維。創作的時候應該讓更多的多樣性或語言進入自己的世界,而不是要把它們趕出去。所以我不覺得一個美好的藝術作品中只有一種語言和一種思維,我覺得在作品中加入不同時代、種族、地方的語言,其實會增加其藝術水平,這樣也比較符合我的藝術信念。
另外包括我自己還有一些前輩作家,或是我知道近幾年其實很多嚴肅作品評論或創作者都在重新思考如何用粵語寫作。我們始終還是在同一個政治潮流(political current)底下,他們不是為了利益,而是出自於一種身分認同,所以想用粵語創作。所以也我很明白大家為何會想以粵語翻譯、辦粵語雜誌,為何想令更多人使用粵語。很多前輩就算已經退休也繼續在努力,譬如蔡炎培先生也用很多粵語去創作,但在比較完整的結集中,他的粵語詩就相對少被收錄 。始終要顯示一位作家的藝術成就,成為典範的時候,他的粵語詩就會被拿走。其實這些前輩有很出色的粵語創作,「粵語創作」其實是一個很豐盛的寶藏,仍然需要大家努力整理、評論。
另外就是粵語應用在作品中時,操作上如何會比較容易?自然就會用對白;或是主張粵語文學應該用以表達「生鬼(生動有趣)」、親切、市井。這是很常見的說法,也是主流說法,但嚴肅文藝界不只著眼在這一點。譬如董啟章在2007年左右,他的《時間繁史 · 啞瓷之光》運用了大量粵語創作。董啟章也特別提到雖然裡面有大量的粵語對白,但裡面最具挑戰性的是要用廣東話去討論一些嚴肅的問題。像人生、意義和哲學的問題 。為何他要這樣做?其實當我們說廣東話的特色的幽默、生動、詼諧的時候,其實是侷限了廣東話的可能性。那些「生鬼」、開心的情緒只是佔我們很少一部分,如果說粵語的強項就是適合表現這些情緒,難道就代表粵語不適合表達其他東西嗎?如果粵語沒辦法表達憂鬱、頹喪、或是綿綿情意,那麼它作為一個語言的活力可謂相當低。因此嚴肅藝術的文學家正嘗試以粵語去表達嚴肅的話題、概念,讓粵語適用的範圍與彈性擴大。
我深信粵語當中有類似古文的結構,它比普通話更簡潔。所以我曾想利用這「簡潔」的結構去寫詩,那首詩是評論一支現代舞的作品,希望從現代舞的作品引伸去寫比較抽象的哲學思維。我用粵語寫,寫了還蠻長的,但最終失敗了,一來是粵語有其困難度,就像它彷彿沒有一個既定的位置,倘若要問某個東西是不是粵語,然後再把它分出來,這是有困難的。如果要標籤「這是為粵語而創作的」,這需要花費很多精神去把它的niche寫出來,而且稍一不慎就會失敗。我想跟大家說的是,在這個是為廣東話而做的事情是值得的,亦需要很大的意志與胸襟,我希望大家能互相知道彼此在做的事情,也能互相支持。
孔德維:那我想我們可以直接進入討論時間。首先因為在留言區中已經累積了很多問題,不如就先讓有興趣反映的觀眾提問⋯⋯如果沒有的話,我會先從留言區中總結一些題目,然後最後的排序就是嘉賓之間的交流。
那有與會朋友想問問題嗎?如果有的話可以自行打開麥克風。我第一個看到得到的留言是很多朋友都對粵語的書寫——如何作為一種書寫的可能性,或者漢語語體文方面有很大的爭議。剛才鄧小樺分享了許多,我想關老師應該會有興趣回應,因為這跟平常我跟你私下的討論有不同的印象,你會不會有興趣先分享?
關煜星:我自己找作者的時候,第一時間的反應很常是「這個字該怎麼寫?」、「怎樣才是正確的廣東話寫法?」其實很常是他們自己創作的字。這第一時間會是編輯的問題。我辦《迴響》之前有一個叫「粵典」的計畫,就是一個網上的粵語字典詞典,我會用我辦「粵典」時的基準去回答那些問題。如果要問甚麼是正確、甚麼是符合權威的話,這樣而言的確是還沒有,沒有一個很強的制度(institution)、權威去做出來。其實不需要這種權威才能書寫你的想法或故事,只要其他人看得懂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嘗試寫了,然後其他人看不懂,或是你用5P字(類似於火星文)去寫的話,那麼它當然會有自己獨特的效果,但這個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呢?又不一定。那麼我會跟他們說:「你先寫,寫完後再讓編輯看,或是你寫完我們再去改。」當然,通常說完之後,他們寫出來的東西是否需要特別修改、或特別編製所謂的「正字」呢?也不盡然。為甚麼大家需要這個(權威性的)保證(assurance)才能安心寫作?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也是任何語言的創作也會經歷過的階段。但對我而言,一個符號正確與否,是否真的對於表達想法、書寫故事、創作神話而言那麼重要呢?其實也不太是。另外想回應一下,剛才李博士提到南洋、東南亞的粵語,我們雜誌不久前找了一位新加坡朋友,他幫我們辦了一個南洋書寫的徵文比賽,引來了很多馬來西亞、新加坡或是印尼等的朋友用粵語創作,我發現他們對粵語的想像跟我們其實不是說很不同,但他們在寫作方面似乎不存在那種「關係」——他們會少了種「啊!這是書面語」「啊!這是口語」⋯⋯他們寫出來的東西會少了一層過濾或枷鎖。當然,他們創作的的樣本量(sample size)還不足以讓我看到有甚麼本質上的不同,但這是一個有趣的觀察(observation)。
李薇婷:我覺得這點觀察很有趣,因為寫書面語中文的時候,所有以粵語為母語的人應該都是用粵語來思考如何寫書面中文。這是(鄧)小樺也提到了很多,譬如在正典化過程當中會抽走很多粵語作品,或是如何用粵語去表達哀怨與憂鬱這些情感呢?其實到了這個位置,有一些創作者,以我觀察的兩位而言(黃世仲、黃伯耀),就會變成有點夾雜古文的狀況。因為他們書寫的字是挪用自那邊的,然後再加上一些廣東話的後綴,以此完成他們的中文創作。像我們現在不會問董啟章的《時間繁史 · 啞瓷之光》是「用普通話來說的書面語」、「用粵語來說的書面語」還是「廣東話」。因為他們常常會被說「中文不好」,那到底是那種「中文不好」呢?究竟是一種規範性的——像北京、台灣也會有⋯⋯(華語)像台灣國務院也會發佈(指導他們怎樣去用的)一些詞典,那如果是這種官方發放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問題就是沒有一個粵語建立的政權吧。如果這樣子去解答的話,粵語最後又會變成一個問題——當一種語言變成官語,它就會產生新的問題。我的想法是比較接近於小樺,雖然大家都用政治性的方法去解讀語言,可是我覺得在創作上⋯⋯我自己的觀察是,要怎麼去處理粵語和古語之間的關係呢?用古語的話——用古語報告的時候,我的同學會問我⋯⋯反正他們就是在「誇」這個中文(chinese),然後加兩個粵語的音進去,你不能把它完全當成粵語,這樣的事情就一直輪迴(such a loop),所以我就拋個問題給大家想吧。
孔德維:是不是有朋友想回應?剛才看到有兩位舉了手。
洛琳:(華語)是我。我也用一下華語去說。因為我之前有一些朋友是用粵語去創作,也有一些不是,他們曾經分享過一個很有趣的貼文:就是說有一些法律文件和地契也是用廣東話去書寫的,而且在法律上具有作用。我們剛剛說了好多東西——有些是在留言區討論的東西——也說到「要爭取粵文為半官方語文是有難度的」,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下法律文件它是說⋯⋯中文是一個官方的語言,但是不是只有我們平常認知的那種「中文」是官方語言?要是我們整個民間都用廣東話去創作、書寫,很多條例我們嘗試用廣東話去演繹,能不能有一些以廣東話去寫的法律文件 ,而還是能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我覺得是有一些朋友——尤其是法律界的朋友他們研究過,似乎是沒有問題的。而我們說要爭取它是為了做甚麼的時候,我們是要有一個政權去承認我們的地位,可是在法律上、不要管政治的東西的話,其實有沒有爭取別人認可的需要?
好,那接下來就換回廣東話。有趣的是我之前回看五、六〇年代,或七〇年代的文學,忘記是誰說過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回看二、三、四〇年代的報紙,是文言文鄙視語體文的;到了六、七〇年代、或七、八〇年代,語體文就開始鄙視廣東話了; 但到了現在廣東話又好像沒有一個足夠的地位去鄙視其他。是不是非得要得到某些人的承認、或某些政權、團體、組織的認可,我們才有權利去創作;抑或是我們有某種程度的生產力、勢力的時候,它不得不承認我們呢?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而且是值得大家去思考與討論的。「政權是否認受我們」和「我們是否去做」是兩件事來的嘛——我是這樣子想的。
孔德維:不好意思我想再問清楚一點:剛才提到的「生產力」,是指「經濟上的生產力」,還是「文學作品上的生產力」?
洛琳:我想是整個生態的蓬勃程度,或許我的用詞沒有很恰當。
孔德維:明白。如果接下來沒有朋友想回應,在留言區中有位觀眾想問⋯⋯
鄧小樺:我想回應。因為我說話太快,有時又太亂,我在這裡在延伸一點點。的確以我的認知粵語目前作為一個邊緣的語言,但邊緣裡其實有很大的自由度和可能性,我們並不需要先得到別人認可,然後才去做。但有一個情況是說——我的問題就是:事實上我們是否需要爭取所謂法定的框架?我也說過我其實不太介意有沒有爭取成功;剛才關於法律的討論,做得到的話當然好,我樂見其成,但其實我對於統一性和正統性的要求感到很困惑(puzzled)。因為坦白說,譬如我有看過關於《迴響》的訪問提到:編輯會因為覺得作者在語法上「不是那麼廣東話」而去作更改。坦白說我自己當文學雜誌編輯這麼多年,就算是使用語體文的投稿者,在語法上有問題,我也不會作更改。我是蠻驚訝於(shocked)這份大眾化的粵語期刊會做這件事。不知道是否在理念上的不同,我要說明一下為甚麼我不會改:我覺得「規範」並不是保障創意的最好方法; 我覺得「混雜」才是保證創意的最好方法,這是我的信念。所以坦白說我是蠻驚訝的。
那我能否展示一下這個我努力做出來的圖片?我解釋一下這個「粵語方陣(圖)」(如下):
首先我們要打破二元思維,但不是以解構,而是以建構的方式,就是像所謂「格雷馬斯方陣」(Greimas square),這是結構語言學的一種方法。在這方陣中有兩組相對性的觀念:
1. 「書面語」vs「口語」(而非「粵語」),譬如湖南話也有分書面語與口語;
2. 「白話文(官話)」vs「粵語」
「口語」與「粵語」是「相近」,但不完全一樣; 「書面語」與「白話文」亦然。如此拆開了兩組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每個交叉(cross)之間,其實都可以產生一個「相容」的觀念。如此便可以打破一些二元對立的思維:譬如認為「粵語」沒有「書面語」,這個觀念完全錯誤——粵語中也存在書面語。 像「歡迎光臨」既是粵語,也能是寫成書面語。這樣去看待的話,粵語的世界以及可能性就會大很多。
然後是「口語」變成「白話文」的。我舉個例子: 《紅樓夢》中經常出現「小蹄子」,其實差不多是「仆街」或「死o靚妹」的意思。我們做學術有客觀性,「仆街」就是「仆街」,是有一點粗魯,是丫鬟之間的辱罵像「小蹄子,你真係太曳啦。(小蹄子,你真是太壞啦。)」它是一個口語,但以書面方式呈現之後就變成白話文的一部分;然後「歡迎光臨」就是能夠粵語「說出來」的口語,譬如你去便利商店也有人會跟你說「歡迎光臨」。如果說所有可以變成書面語的東西都不寫進文學作品,然後意欲讓粵語的身分變得「很鮮明」,這樣的話其實連「歡迎光臨」也不可以寫。譬如我有一位老師——張洪年教授,今年出版了《香港粵語:二百年滄桑探索》,他其實也反對將「粵語」與「中原」分得太清楚 ,他說:「如果真的要分那麼清楚,那麼連『你好』都不要說了,『你好』也是從中原傳進來的。」所以我們始終會發現並沒有一個所謂絕對「純粹、純潔」的根源⋯⋯
孔德維:到這邊那麼我們先讓他(關煜星)回應一下,因為後面也有其他朋友舉了手。關老師可以快速回應一下。
鄧小樺:他是不是編輯?可能他不是?
關煜星:其實我是(《迴響》的)編輯,但事先聲明,那個受訪的編輯不是我。大家愈多「語碼混合」(code-mixing)、愈多混雜、愈多的挑戰界線,愈多的⋯⋯我們會稱為「折磨」。我很喜歡「折磨」這個概念,我覺得去探究一個意識、一個想法,其實是在「折磨」這個想法。像倒一杯水那樣,水本身沒有形狀,但裝進杯子裡之後就會有杯子的形狀。那我們去看界線、去看守挑戰的面向、去看那種局限性,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水裡面「盛載」的意識、想法到底是甚麼形狀。我自己在談論粵語規範的時候,我是極度反對那種「粵語法西斯」或是「粵語塔利班」。這種追求「純粹的粵語」、或是有個「粵語的道統」、或是要追溯到很多年前那一本古書中「剛好與粵語的另外一個字同音或意思相近,那一定就是從那裡演變過來」之類的想法。這件事情是⋯⋯喜歡做可以做,但就和我現在在做的東西沒甚麼關係。
孔德維:所以的意思是《迴響》裡的編輯、編採準則也具有多元性,還有是互相在「折磨」大家?
關煜星:我們還蠻常吵架的,經常折磨對方。譬如我們曾就「咁」字該如何寫而吵過架。
孔德維: Ok,我們有機會再分享,因為目前累積了很多問題。
(標題為編輯所擬,待續)
註:
1. 出自老伯(黃伯耀),〈曲本小說與白話小說之宜於普通社會〉。
2. 出自量拙排演,《妓俠》。
3. 譬如耀公(黃伯耀),〈宦海悲秋〉
4. 出自光翟,〈敬告外埠華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