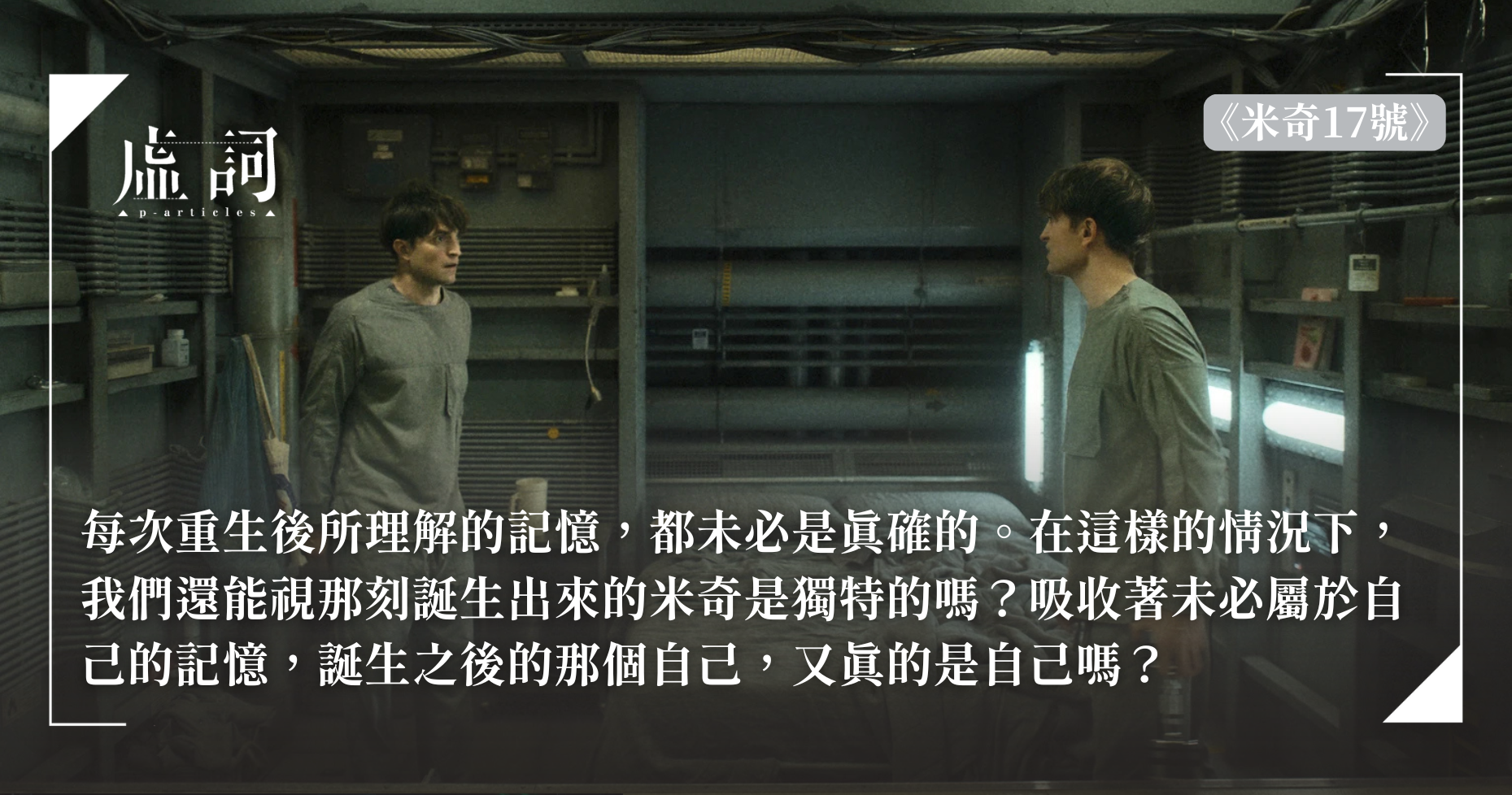《粗獷派建築師》:由斷裂的敘事結構到現代性與大屠殺
影評 | by 姚金佑 | 2025-04-01
姚金佑傳來影評。他表示《粗獷派建築師》分為三個章節,觀畢後對於第二章與第三章之間的滑坡,以至電影的結束略為突兀而感到茫然。姚金佑相信這樣的結構安排,旨在突顯「歷史傷痛的輪回」,並以突兀之感給觀眾一巴耳光,提醒觀眾那段悲痛的歷史。姚金佑續指,這樣獨特的結構所相應的,其實是電影所帶出對現代性的批判。 (閱讀更多)
《門逃》信仰困獸鬥
石啟峰傳來電影《門逃》影評文章。他表示,近年推出《完美物質》等驚悚傑作的出現,觀眾對恐怖片的期待和標準被不斷拉高。《門逃》這套電影可算是出乎意料——它將關於宗教信仰的哲學思辯與令人毛骨悚然的緊張氛圍巧妙結合,為這個語境帶來深刻的意涵。不論在劇本及角色設定、鏡頭語言,及至故事深入叩問宗教信仰的本質,均使石啟峰認為《門逃》實為優秀的恐怖片之作,更直言觀畢後將會對此種類的電影期望一再提高。 (閱讀更多)
反抗。躺平。出軌——我們這一代的都市青春哀歌
影評 | by 鄧皓天 | 2025-03-19
鄧皓天觀畢《青春末世物語》,聯想到《函館夜空更深藍》以及《愛上透明系女孩》兩套日本電影,當中都描繪出角色在青春的迷茫中展現的各種面貌及感悟。鄧皓天認為《青春末世物語》將青春的茫然透過焦慮憤怒等情緒展現出來;《函館夜空更深藍》將春青應有的愜意與無憂無慮呈現在鏡頭;《愛上透明系女孩》將一個青春純真的人被社會後變成當初「討厭的大人」的模樣。 (閱讀更多)
《看我今天怎麼說》的兩個議題
洛楓傳來影評,指自己被電影《看我今天怎麼說》打動,表示:「電影採取平視的角度、含蓄的敘述風格⋯⋯讓人物透過影像與聲音自動講故事⋯⋯讓觀眾體驗聾人的聲音地景!」觀畢即激發洛楓思考兩個議題:一,科技能否帶來自由與平等,「人工耳蝸」的出現令堅持使用手語者容易被視為異端;二,何為聾人圈子的「異質者」,使用口語或手語者雙方有否彼此尊重和容納。電影探討何謂平等、尊重與共融,是日常生活的相處、人情的建立和自我的長進,鼓勵觀眾懷著面對生命限制迎難而上、找尋出路的勇氣。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