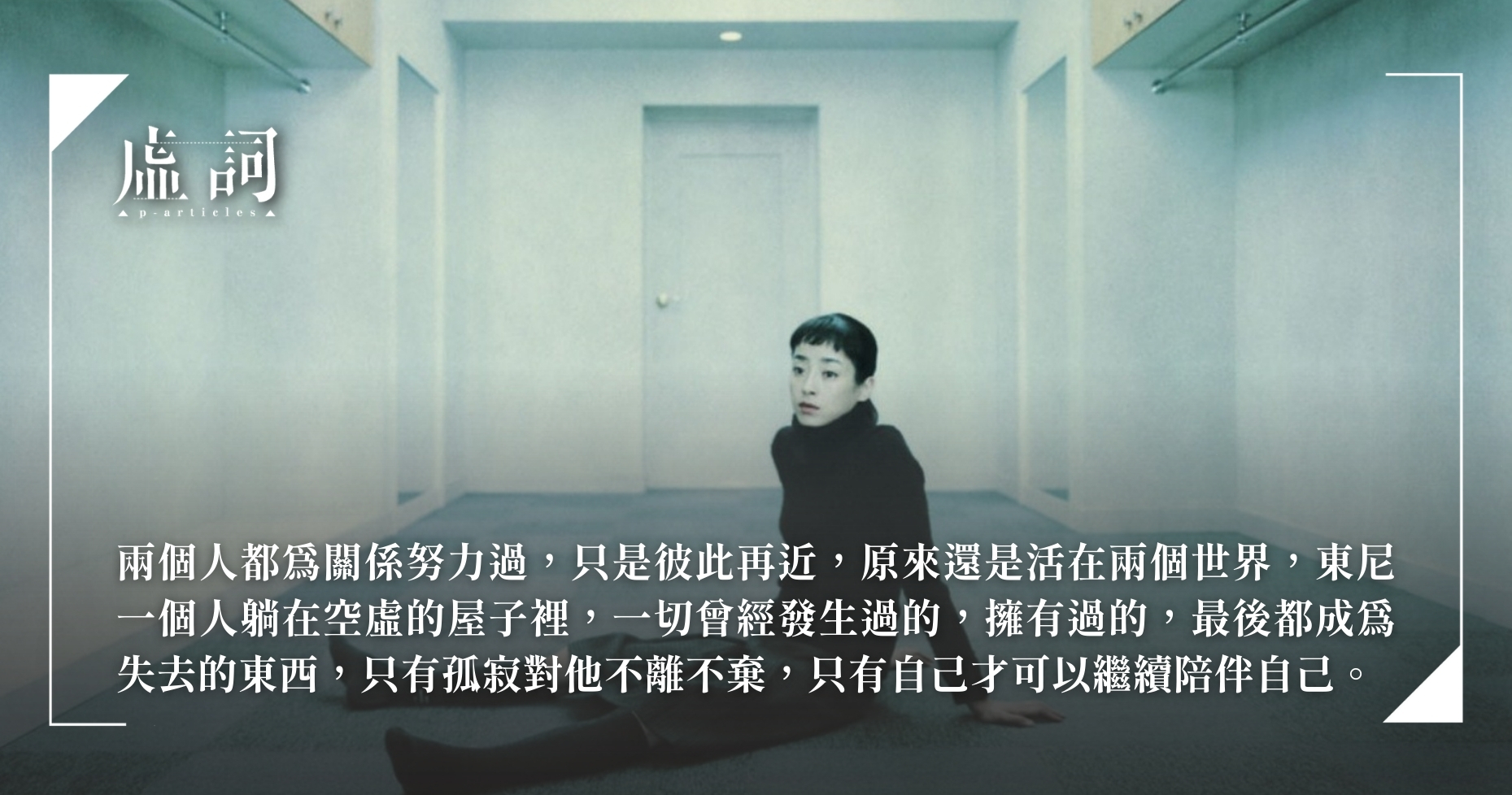東尼瀧谷——貪戀村上春樹
影評 | by Ivymoksha | 2025-01-15
當案頭還有整整三分之二本黑夜之後(After dark)未完成之際,我又肆意捲入另一個村上春樹的旋渦:沒有期待之下看了改編自村上同名小說的電影《東尼瀧谷》(Tony Takitani)。由一完場時有一點點嫌棄(故事帶出關於孤寂和其不可改變的宿命意味似乎未能深入呈現於大銀幕上),到反復思量後越發歡喜,這當中簡單不過的解釋, 莫不與自身性格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環顧身邊喜歡本片的朋友,或許不多不少與本身性格多慮、悲觀感強、富憐憫情感的居多。有朋友直指不明白電影有何可取之處,只感到沉悶、沒有真實需要交代的東西。喜歡的朋友則基於再一次得到角色代入,在孤絕的情緒下得見真正理解的人,如沙漠的綠洲,癮君子的海洛英,別人眼中的娛樂調劑實乃生活中缺乏的必需品。
湯禎兆已拿《東尼瀧谷》作例子來引述日本青年一代的「蟄居族」(hikikomori,注一)現象(《CUP》#41),矛頭直指村上春樹筆下的主人翁本來就是不折不扣的「蟄居族」人。香港人好喜樂、熱鬧,凡事功利主義、目標為本(這樣很好,不用浪費時間和氣力),香港很少機會孕育出「蟄居族」人:香港人直接,不屑一系列“無病呻吟”的行為/產物,所以電影得不到大迴響自是意料中事,不過,喜好這回事從來主觀又個人,不欣賞的人自然有多種背景因素影響,反之亦然,而且以拍廣告出身的導演市川準實在在視覺上提升了村上春樹故事的想像性,撇開電影題材,電影本身著實有很多其他可觀的地方。
看過電影,本想買《萊辛頓的幽靈》(內載有短編小說《東尼瀧谷》),只可惜實在忍受不了博益的粗糙出版。現在正好在未看原著前先記下純粹對電影本身的感想。
東尼瀧谷,一開始就詳細交代這個奇怪名字的由來,道出自己的爸爸、以至和家庭間疏離的關係及孤獨的成長背景;因為一直感到自己不能好好融入社會之中,於是努力斷絕和離開群體社會;雖然長大後事業有所成就,卻也不表現得怎樣高興,一直在沒有得到別人真正的瞭解而生活,活在擠滿人的都市,卻比在荒島更荒涼。直至東尼遇上心中那個註定的妻子。搶回來的妻子(可見東尼本身有其過人的魅力)看來和他倒真的很相敬如賓,幸福是當中那些努力建立的瞭解關係,唯一的不配合是妻子跡近瘋狂的購衣欲;妻子最後也因買衣服,在交通意外中賠上了性命。妻子死後,東尼聘用了一位和妻子身型一模一樣的女子,目的是要她每天如穿制服一般穿上他妻子留下的衣服。東尼希望這樣能減退妻子離去對他的影響。片末,東尼的爸爸因病逝世,在妻子、親人相繼離去的打擊下,東尼的人生,走了一個圈,好像又回到了最原先的地步。
我久久不能忘懷東尼小時候一個人吃飯,後面一切頓變得漆黑一片和不對焦的一幕。導演在片中不時穿插東尼吃飯的場面:長大後一個人吃飯,以至在婚後妻子和他兩個人恭敬地共進晚膳,那種由孤絕到一點歡樂的改變,那些不是兩三句對白所能交代的心態轉變,及至妻子離去後他又要面對一個人吃飯的日子,畫面正好更有力的彌補文字所不能傳遞的張力。
印象深刻的還有關於妻子的描述。妻子說自己沉醉於購買衣服,因為覺得穿上漂亮的衣服就能彌補自身的不足和缺點。這對白正好為後來這對夫妻間感情的起伏埋下註解:妻子有一段時間確實能夠制止自己的購衣慾-因為丈夫的要求;後來妻子再次不自覺地沉迷於衣裳堆中,暗示夫妻間的疏離,妻子努力的維繫最後連結果也看不到就離開了。兩個人都為關係努力過,只是彼此再近,原來還是活在兩個世界,東尼一個人躺在空虛的屋子裡,一切曾經發生過的,擁有過的,最後都成為失去的東西,只有孤寂對他不離不棄,只有自己才可以繼續陪伴自己。
電影的攝影手法、色調運用,很能配合村上小說的風格。所謂村上的風格,就是那種淡淡然的無奈帶來的震撼。習慣煽情橋段、多元化鏡頭運用的觀眾可能就會對影片感到單調甚至懨悶,因為不停的從左至右的過鏡和偏向靜態的情節,觀眾一心期待“究竟想說甚麼呢?”的問號可能在滿溢戲院後只得到一個令人失望的答覆-沒有特別的意義,不過是在蘊釀一種必要的氣氛。其實不論是村上的小說,抑或是這電影本身,所需要的就是蘊釀。村上故事的味道都需要讀者付出一定程度的耐性去協助故事的推進,讓故事的味道精髓走出來。若漏去了那些看似沒甚意思卻暗暗交代關係的場口,當中的意思似乎便難以鞏固。不論是文字、或是影像的表現,村上春樹的故事都是邀請讀者/觀眾投入其中,而不是一個旁觀者眼中的娛樂商品。
其實,我不算是沉迷村上的那類讀者群,要算迷村上的,至少數以萬計的讀者在我之上;在我身上其實很少出現 “迷”的情況,不過,對於村上春樹,除了迷戀,確實也想不出另一個合適的辭彙去形容;村上的吸引力在於他不是要給予讀者一個糖衣處境,讓他們陶醉的反而是一個可能比現實世界更殘酷和不近人情的境況-試想想有多少個村上的故事是大團圓結局?他不特止殘酷,或要迫讀者思考,故事結尾大都是留白的,要讀者看過後反思,為故事(或自己?!)想下一步的做法。所以看村上就好像到一個景色秀麗的瀑布前一樣-但你在一條斷尾的橋上走,到最後你很可能需要自己處置自己。村上小說的吸引力不在於故事或角色本身,而是它能夠被現實世界孤絕的一群代入的力量。
注一:「蟄居族」被界定為感到被日本社會淹沒壓迫、感到不能夠滿足社會角色的要求,然後選擇以逃避來斷絕與社會聯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