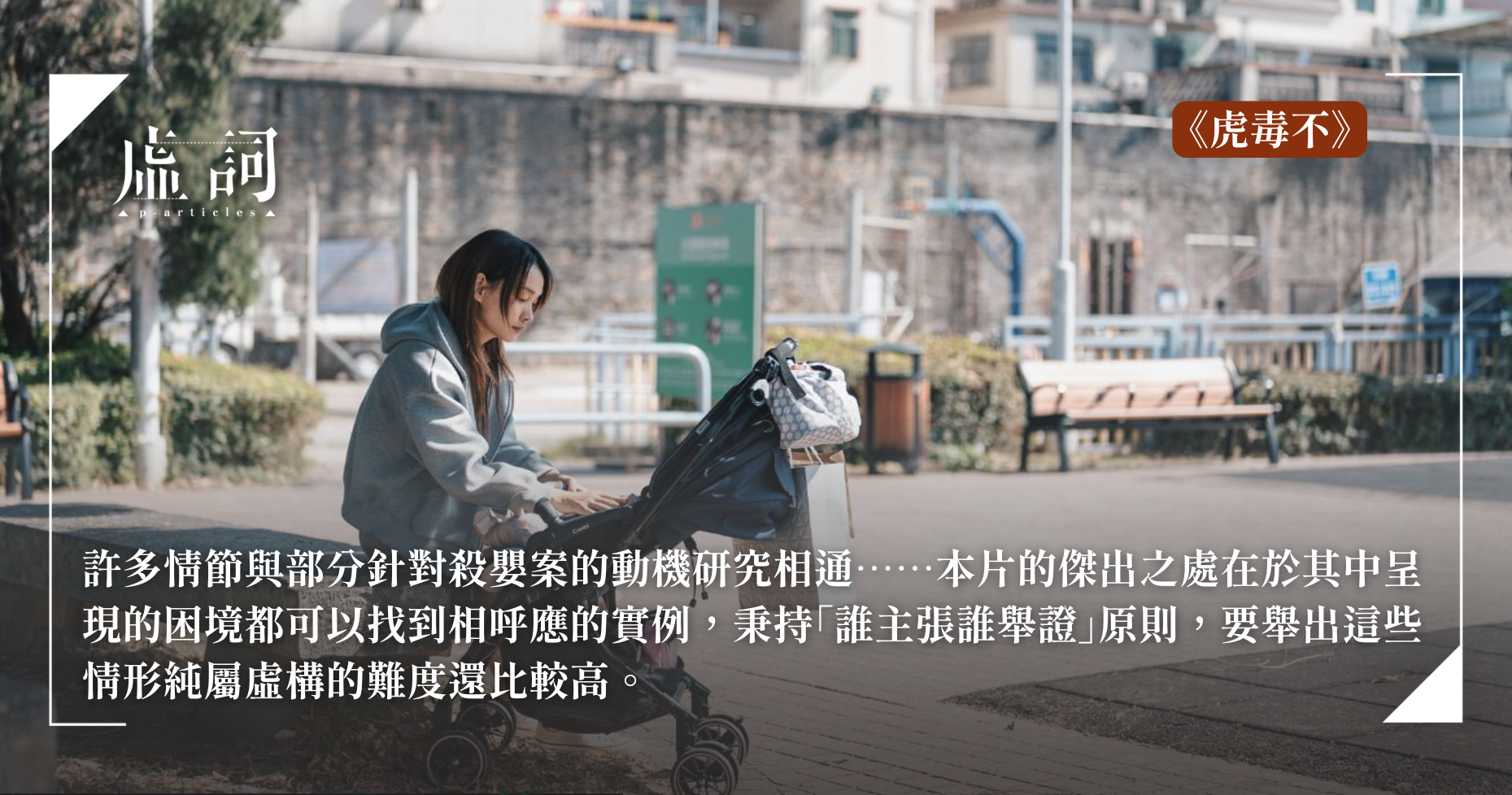閃閃發光——從《貓貓的奇幻漂流》中的魚談起
雙雙傳來《貓貓的奇幻漂流》影評,指出電影要角貓貓、拉布拉多君、蛇鷲君等在電影賦予人格化,而同為動物、使流水閃閃發光,在構圖上不可或缺的角色的魚群為何被高度物化呢?雙雙認為魚群被視為「人」的碎片,象徵故事中的角色與人際關係的流動性;鯨則代表家長般的守護者,結尾殞地隱喻生命無常。電影中的水流與動物的隱喻,均映照著人類情感的複雜與生命旅程的漂泊。 (閱讀更多)
《虎毒不》:邊一個發明了母職
影評 | by SC | 2025-04-30
SC傳來《虎毒不》影評。他認為《虎毒不》從戲名故意故意缺失了後半截,便直擊母子關係的陰暗面。SC認為《虎毒不》透過新手母親淑貞的經歷,揭示現代女性在照顧孩子與工作間的掙扎。又,刺耳的嬰兒哭聲貫穿全片,象徵無法逃避的責任,而丈夫阿偉的「喪偶式育兒」與婆婆的傳統觀念,更突顯社會對女性的不公。 (閱讀更多)
《貓貓的奇幻漂流》:蛇鷲為何消失不見?
影評 | by 姚金佑 | 2025-04-23
姚金佑傳來《貓貓的奇幻漂流》影評,他指出電影原名為Flow,概指劇中貓貓及其他動物在水災之下所坐帆船的流動,又或洪水的流動,但整個華文地區的譯名均以貓為重心。姚金佑認為儘管戲中其他動物有經歷前後的變化與成長,但都不及貓貓來得要多,而只有以貓貓為本來解讀這趟奇幻漂流,才能夠理解大家在電影後面感到迷惑的一幕——蛇鷲於山巔之上的消失。 (閱讀更多)
《穿越時空の初吻》穿越橋段之必要
葉嘉詠傳來《穿越時空の初吻》影評,她認為「穿越」雖是平淡尋常甚至俗套得不值一提的橋段,但導演坂元裕二正巧妙利用此「老土」橋段,將「穿越」作為工具,反寫出天長地久的愛情觀,同時沒否認曾經擁有的浪漫激情。又,將電影三種愛的方式融合了「穿越」當中,不僅推動劇情,更深化哲學思考,提醒一切的抉擇,更為個人意志的選擇。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