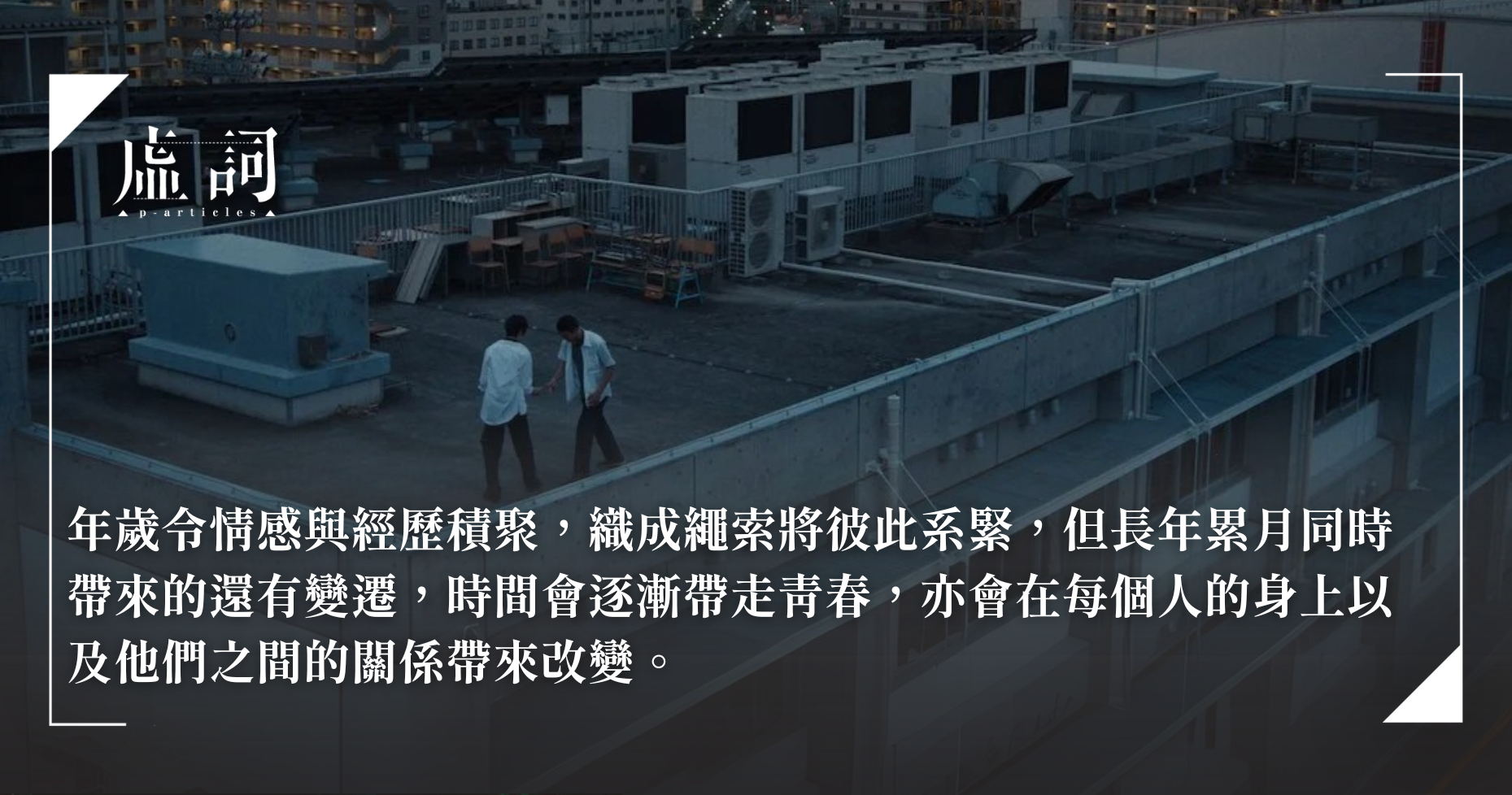《青春末世物語》——所謂的「盛世」,便是「末世」的開始
影評 | by 亞C | 2025-02-26
「坂本龍一的兒子」,說起空音央,這大概是個繞不過的標籤,而他作為導演,上一部執導的作品亦正是自己父親的紀錄片。但這部他第一部執導的電影長片《青春末世物語》裡,並無坂本龍一的參與,即使由音樂人Lia Ouyang Rusli創作的極之出色的電影配樂裡彷彿帶著某些教授的影子,而創作人亦曾表示希望音樂會帶出某種懷舊的感覺。這不但是指那隨著劇情推進,於某些場景下響起的一般意義的Background Music,還有戲中主角阿高和裕太演奏起的幾首電子音樂,實在不禁令人想起當年YMO的作品。
而電影與過去的年代似乎有所聯結的不止是音樂。
空音央曾在不同的採訪中表示電影創作的靈感追溯到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而日本社會在這場地震中受到的創傷不止是自然災害帶來的,還有伴隨著肆虐的種族主義引發當年對朝鮮人的屠殺。
而在戲中的主要人物便是五位常常聚在一起的摯友。這彷彿是影視劇中常出現的設定,像韓國導演申沅昊創作的請回答系列以及機智的醫生生活裡同樣如是。不過《青春末世物語》裡的少年少女更像有台灣導演楊德昌,侯孝賢們的感覺,而空音央亦曾坦言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影響頗大。
但除了身上瀰漫的青春氣息之外,電影中的少年們在身份上亦已帶有某種政治意味。五人之中小明和Tomu分別都是台日與美日混血兒,但小明熟悉的國語匱乏得有如自身的混血兒色彩,Tomu即使無法遮蓋自身膚色,但言談舉止亦與一般的日本人無異。但是似乎最無法擺脫自身身份的反倒是尚未歸化的韓裔居民阿高。電影中兩次遇見警察運用人臉識別獲知身份後,都與眾不同地被要求交出證件,甚至在夜晚行走在街上因缺少那一紙證明,被兩位警察「貼心」地立即「護送」他回家。除此之外,電影中有一幕,自衛隊前來學校招募宣講,那些被劃分為「非日本人」的同學都需立即離開課室。
距離1923超過100年的今天,不止是日本,世界各地的社會上對於移民,獨有的針對身份上的區隔與歧視的陰霾仍久縈繞著。並且與此同時這亦成了政客們最隨手拈來的話題,但無論是公式化地重複著偽善而非妥善呼號與宣示的;或是興奮並肆意地將其與五花八門的問題牽上關係,當作緣由的,兩者看似針鋒相對,勢不兩立,但殊途同歸,都是一起為那陰霾的籠罩推波助瀾,使其並未遠離。
而戲中的政治信息亦不止如此。
在電影裡,同樣出現了地震,因為地震,戲中的日本首相藉此擴大政府權力,從而引發了社運。
但這些社運,在電影裡只是零散地於電視新聞裡交代,並無太多的場面,只因敘事的主角和視角都是那幾位少年,主要的筆墨便亦落在那幾位高中生,以及他們所在的校園上。
但校園與社會,兩者並非完全隔絕的。
地震的餘波也不止震及外在的社會,同時亦給那高中校園帶來變化。
首先被突如其來地震打碎的是校長的那部豪華跑車,而這事故的「真兇」除了地震外,還包括阿高和裕太。只因是他倆半夜偷入學校時將這名貴跑車豎立起來(究竟怎麼做到戲中並無交代),但地震將這「惡作劇」的破壞力擴大,甚至還令校長以此為理由為校園引進了一個「全視點」系統。校園因此充滿攝像頭,並且還伴隨人臉識別,每個同學在校園每個角落的任何所作所為都變得無所遁形,以一個個框框呈現於螢幕上,而據此監察所得的任何微小舉動若逾越了那校規所訂立的框框,便以扣減不同的數字作為分數懲戒那些相同紅色框框內不同的人。
和戲中新聞報導所提的首相所為,兩者間彷彿有著「異曲同工」的感覺,甚至與現實裡某些揚言已擁有的AI水平可以亦即將會取代政府功能的「偉人」們也像是有著某種照應。
不過電影裡的同學們對於這新事物的反應,拋卻最早的新奇感覺,親歷過螢幕冷冰數字會伴隨後果之後,仍是彷彿帶著某種迷惘,與首相提出的擴大政府權力方案不同,這個改變發生後並未即時面對反對或不滿的聲音。
但同時地震亦帶來另一道悄然增長的裂痕,橫亙在阿高和裕太之間。
二人逐漸不再像以前一樣形影不離,只因阿高開始受到班上另一同學富美的影響,開始留心社會,同時亦身體力行地參與起社運。但裕太仍像從前一樣,醉心並專心於以往和阿高一樣一直深愛的音樂上。對於社會上的問題,抗爭的訴求並非並不理解,但是抱持著一種疏離的態度與無力的感覺,和唱片舖老闆娘說的「最好的音樂已在過去」確是他內心真實的想法,並且這想法亦不止局限於音樂。
過去一直在身邊的人,就這樣忽而遠離了。
不止是阿高和裕太,Tomu決定在畢業後前往美國,阿太和小明正式相戀並將對方介紹給自己家人認識,青春仿正漫步於末路,五人似乎已不能如從前一樣。
但在青春終結之前,在校園裡,同學們終於不堪那「全視點」之擾,在上文提到那幕,因非日籍而被迫離開課室的一眾同學在走廊上全部都被系統識別扣分,引發了激憤。而雖屬日籍卻依然選擇離場的富美則提議前往校長室靜坐反抗,要求取消這個「全視點」系統。不過對於這行動的附和,隨響起的下課鈴聲以及需付諸行動的代價而沖散不少人心。即使如此,富美仍然聚集了好幾個同學一起圍堵在校長的辦公室,要求取消這個監控全體同學的系統。
然後的情境實在彷彿是在重複著大多數的社運場面般,不過這次行動最終成功迫使校長服軟,經歷一個晚上後最終承諾會將這個系統廢除。但在真正宣布實行他的承諾時,校長再次本色出演現實中的政客,加上了一個條件,就是要求毀壞他汽車的「元兇」主動自首。
鼓噪的台下和呆坐著的阿高,目睹著裕太主動走上台前,自己一人承認了那「罪過」並承擔了退學的罪罰。
裕太的個人見解不見得開始改變,轉而認同並投入這場抗議之中,但是自己卻成了整個行動中付出最大代價的人。而他下定的決心大概不止是為了自首從而順利促使監控全校的系統能夠取消。
「如果我們不是從小就認識,現在還會在一起玩嗎?」
那天阿高說的話,站在一旁的裕太清晰地聽到。
年歲令情感與經歷積聚,織成繩索將彼此系緊,但長年累月同時帶來的還有變遷,時間會逐漸帶走青春,亦會在每個人的身上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帶來改變。那繩索可變作是彼此依舊親密的牽繫,也可是束縛,會令人感不解和不適,以及不甘。
裕太會如此一人承擔這二人合力而成的「罪行」,大概都只因為阿高。
雖彷似是成了束縛,但材質終究是由那些珍貴的情感與經歷編織而成的。
結尾處裕太和阿高又走到那個天橋的分岔口,這個地方在電影的中段便出現過,兩人各自回家時便於此處分開,分開前兩人都會玩鬧一番,甚至盡訴「愛意」。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著愛,戲中並無清晰交代兩人的性取向,但愛大概也不止於一般意義上的愛情。畢業禮完結,電影的最後兩人似乎仍能帶著愛。鏡頭曾停留在裕太分別時捏著阿高乳頭的瞬間,但配樂仍在繼續,似是響起一切如舊的餘韻,不過畫面停留數秒後,兩人終究還是朝著自己的家,兩個相反的方向走去,奏起的終究是末尾的輓歌,同時亦是步向迷惘未來的樂章,他們從此離開校園,正式步入這個充滿缺陷,千瘡百孔的世界。
但是在校園內,不也有所經歷過了嗎?
其實那位開著豪華跑車的校長亦不見得是多麼十惡不赦的人,而他為自己辯解的說辭也並非毫無道理(校園建築物確是經歷地震後依然堅挺),尤其訴說自己的苦衷時,莫名令人想起陳冠中當年寫的小說《盛世》裡的那位國家領導人何東生。不知到書裡的老陳和方草地們怎麼想,自己卻一直覺得何東生臨走前說的那句「為國為民」的宣言確是真心的。電影裡的校長的所作所為似乎也如他自己所認為的那樣,全為的是學生的福祉。
而小說《盛世》和電影《青春末世物語》裡的世界當然也是截然不同的,如盛世與末世,在詞義上,當然也是相反的。電影裡的世界有著不滿,憂慮,迷惘乃至絕望。但小說裡描繪的那個社會上的人民內心充斥著的是千篇一律,漫溢著的幸福。
人當然會追求嚮往幸福,希望身處盛世而非活於末世之中。
真的嗎?
小說中的那個「盛世」,人人都感到自豪滿足,幸福感爆棚,對於整個國家民族的未來,光明得睜不開雙眼,熾熱的光灑在神州大地和人民群眾的心頭。而這個世界的締造依靠的是某位偉人的雄才偉略,建構設想的正確藍圖獨治寬廣天下,當然還配之以混在自來水中的適量能令人感到幸福快樂的化學物質,另外還有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也講出口的「天佑我黨」這一利器。
而與之相對的那個世界,歧視與區隔的陰霾密佈,隱藏在全新技術背後的極權主義蠢蠢欲動,極端右派不斷抬頭並蔓延,自詡的「菁英」所堅持的價值追求只掛在口邊重複著以示身份,除了「含淚含*投票」外找不到令人支持的理由。如此的「末世」。
這兩種世界,究竟那種更壞?
從前的那個港台曾拍過一期《鏗鏘說》的節目,名為《不要麻木》,採訪的對象是香港的詞人周耀輝。節目中耀輝回憶起自己曾生活過的兩個地方,荷蘭和香港,談到烏托邦,也談到自覺一種相當恐怖的麻木,便是認為一切很安全,天下太平的感覺。
也許所謂的「盛世」,便是「末世」的開始,那身處「黃金時代」的陶醉麻木,比起社會的缺陷,方才是令世界變得更壞的根源。
「軟弱無力全是堅忍的證據」,並且會對世界感無力失落,甚至絕望,也是因內心仍對世界存有關懷以及思考,方才會覺察認知到那些令世界走向「末路」的隱患。會有人心覺「末世」,大概反倒才能輕柔地唱出耀輝寫的〈銀髮白〉裡的那句「世界再壞,仍舊不怕」。
聊以自慰地想,這樣的「末世」也不算那麼「窮途末路」,令人感覺渺茫無望。
這尤其是相比起另一種「盛世」,以及,追回那已逝的青春與那些彼此曾距離得那麼那麼近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