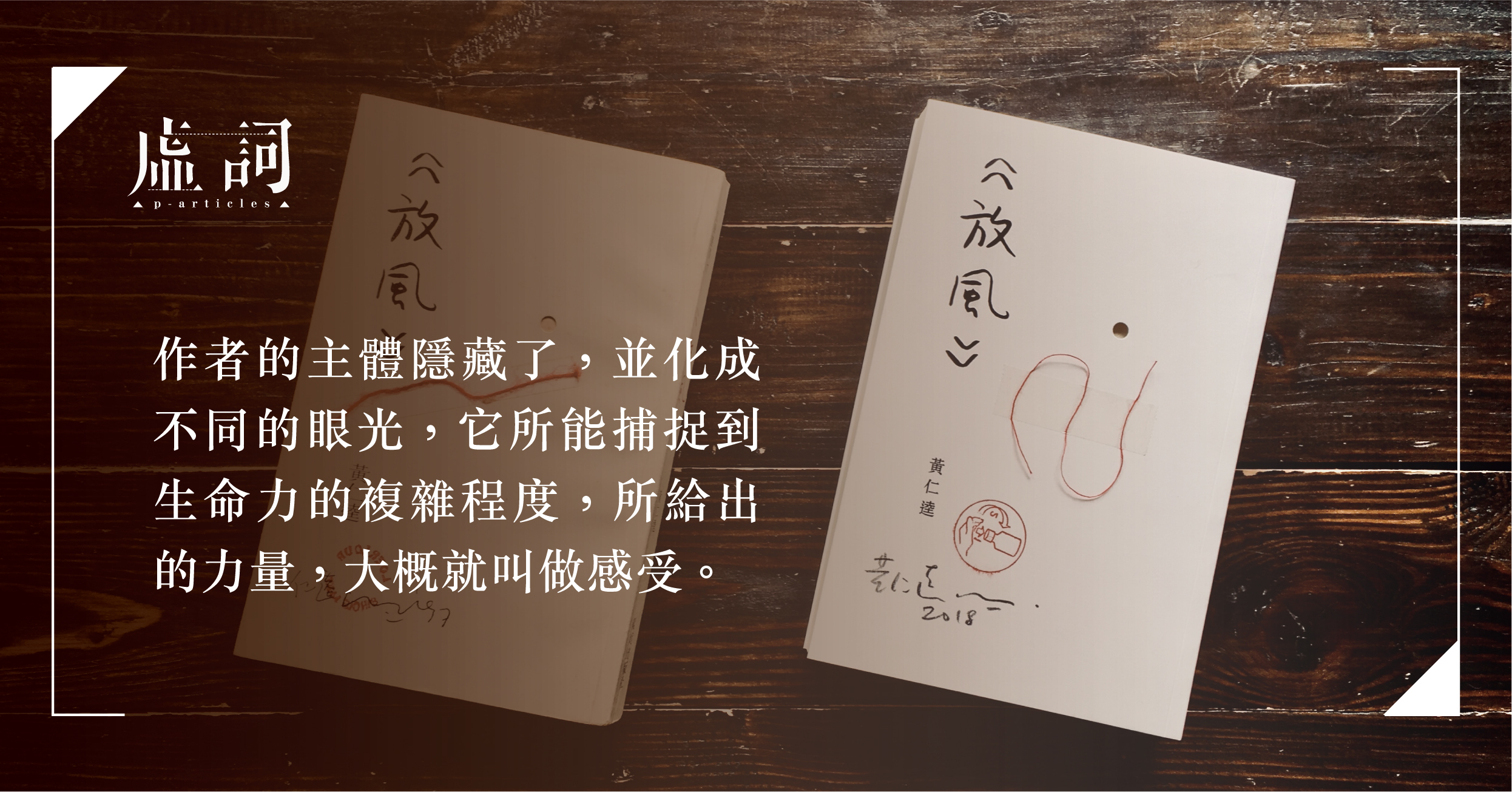讀不懂的,大概關於感受——《放風》
每次寫的時候,才意識到那本書的價值與重量,例如《放風》。
如果親近一本書是需要一種機緣,那我跟《放風》也算是有一點點的。
《放風》是A-level文學科的選讀書,在我的書架上不覺已十多年,那時要做個類似讀書報告的東西,便從二手書店買回來,初版一刷。書當然是囫圇吞棗地吞了下去,並以為閱讀可以用「不懂」兩個字輕輕帶過。直至大學寫作課,老師用〈羅宋裂痕〉教呈現,再重遇,才眼前一亮地在書頁上圈點畫線。到再後來當上老師,第一年便在kubrick買了幾本送給學生。
今年《放風》20年再版,個多月前一個晚上,我翻著自己那本校對再版。那時文學館連我有三人,P買了兩碗麵上來,我記起小室內那一陣藥膳的熱湯味道(R那碗好像有豬紅,儘管我沒有吃,而我叫那間店做「難吃麵」,還有碗浸菜)。
一下子想起許多,其實也不知道為甚麼忽然說起這些無關痛癢的事來,但很自然就這樣寫下了。或者,是因為最近腦海常冒出的一個詞:感受。而這樣錯雜的時光,對我來說,很美。
讀不懂的
校對時周旋在字與字之間,卻忘了去感受。然後一時想到,《放風》的價值與重量,就是在「感受」。
四百擊,四百字,漫長又短促。
一篇順著一篇讀下去,粥王、沒落的湯瑪士馮、髹電燈桿工人阿東、美食家油豆腐……六十五個人物好像由一條隱形的生命線貫串,我看到同一張臉的幾個側面,又看到很多張臉組成了同一張臉,是一人多面,也是千人一面。更重要的,是我看見每一個可以看見的人——那日常生活的力量,真璞的生活哲學。
洞察、尖銳、好奇,難怪黃仁逵是懂得讀人的。他的文字有種「塑像」特質,只敷以淡淡幾筆,文字就在剎那間有了顏色、形狀、氣味、與表情。他寫的不是生活片斷,不是以小見大,而是結實地自成一體;篇幅很小,卻有厚實的內在。敘事從細微、人性、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出發,先挑起讀者好奇,人在其中,都能找到生命的落腳點,再在結尾留一扇窗,放向我視野所未及的風景。如〈遊俠〉寫電車司機肥庚與他的四寶飯:「『閒靜』有多長?別人可能不懂,肥庚默默算過︰大約三百五十呎。」〈半山物語〉寫家傭:「瑪利亞本來並不討厭狗,她在菲律賓南部老家濱沙就養了好幾條」。肥庚的閒靜是「在大路口停住,綠燈亮之前,細細欣賞面前半盒四寶飯」;討厭狗,是因為「泰臣如常牽了瑪利亞上街」。故事情節其實一句話便可說完,但情節以外的,才是生活的真正形態,需要以我們的思路游離開去。讀著,會覺得自己跟那些小人物是彼此貼近的,作者的主體隱藏了,並化成不同的眼光,它所能捕捉到生命力的複雜程度,所給出的力量,大概就叫做感受。
感,動人心也(《說文》),有深化的意味。
《放風》以最平凡的字眼,組成最平凡的句子,說最乏善足陳的恆常。祝君早安毛巾、豆豉鯪魚送飯、舊樓清拆、寫毛筆的曾氏……柴米油鹽醬醋茶,一切日常,一切也並不日常:飯桌上一頭烏蠅、湯碗上一道裂痕、清拆後無家可歸的人與鴿、扮懂日文的日本餐廳侍應……事與人,物與人,物與事,趣怪人事,點滴瑣碎,交互連結,就是天天上演的生活。以是生活,就是他的創作泉源,即在自述中所說的,一井多源,一源多井[1]。
《放風》取名雖然很輕,但毋寧包含了黃仁逵的一套世界觀與美學觀。《畫外音》這些段落像淡淡說著心裡話,卻擲地有聲:
「『我想說︰抽一根香煙/『感覺』一個下午/結識新朋友/聽音樂等等,都是一些資料,你能從中得到一些甚麼的話,就能變成下一個劇或下一幅畫的養分,要是沒有這個轉化能力,即使一天畫二十四小時,也只是自我重複。」——〈相睇〉
「『創作人從生活中選取素材,並非砂中淘金(藝術並不如金子般奪目),而是『米中淘砂』。」——〈溝渠映明月〉
日子一拉長,每天就像重複昨天。但生活的真正形態藏在冰山之下,一篇一篇走進去、走出來,每讀完一篇,便嘗試把遮蔽了的翻開,像喚出一雙雙不同人物之眼看待人生辯證。也許,這就是中學時我以為的「不懂」——一些生命裡真性情的東西[2]。
這才發現,生命原就與懂或不懂無關,而是關於感受。問題在於,我們不接受——不接受「不懂」就是答案,而忘了由它所帶來的反思,乃至我們面對生命之大時所產生的暈眩、迷茫、恐懼[3]……這,就是人,跟書,跟畫,跟世界的原有關係,從來都不止於「讀懂」,就好像散落紙上的點,隨你怎麼連成線成網都可以。「不懂」是因為我們不夠,感受力不夠。而在連串的「不懂」之中,我所能感受到的,其實比「懂」還要廣闊得多。
那些字那些畫就是他這個人
翻看《放風》,第一頁便引我深思:「第一部份《四百擊》是序,第二部份《畫外音》是跋,中間甚麼都沒有。」
序、正文、跋,一本書的結構。
序 ,象徵開始,通常交代成書經過;跋,暗示結束,是對前序的修改或補充。如果閱讀是與書對話,《放風》中間甚麼都沒有,是否代表不求與人對話?或,沒有經過,沒有補充?(又或,一切都是經過,都是補充?)我循著這樣一條思路閱讀,直至看到黃仁逵在訪問中說:
「藝術不是一個愛好,不是一個職業,不是用來過日晨的東西,它是一種生存的取向。」
「我畫畫,是因為我想看到;當我不畫,那幅畫就不存在,而且沒有人能替我畫出來。」
從這番話,可知他對藝術的見解,繪畫在他生命中的位置(他只會說自己是繪畫的人,而非藝術家/畫家),更看到他所關切的,是一些更為本質的東西。
我會不時自問,為什麼還要寫:
「惶惑可以變為能量……蒙克的建樹,不在於他也對世情惶惑,而是把它畫成了畫,於是他走過去了,路上有了落腳地方。[4]」過去不留神的段落,如今一下子捕捉了我。
畫畫,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是因為惶惑,因為模糊。
「當我不畫,那幅畫就不存在,而且沒有人能替我畫出來」,要看到就必須以某種形式記下:寫下來,畫下來,甚麼都好,重點是一個「自言自語而不會被打岔的空間[5]」。只有這樣,我才能看到生活的輪廓,才能揣摩現實是如何造像。這就是中間甚麼都沒有,一種生存的取向。
對一幅畫一篇文章能夠接收多少,決定了我們與它的連結程度。又想起《水底行走的人》黃仁逵畫中的顏色、構圖、筆觸、線條,難怪這樣斑駁,這樣有力(我只懂這樣形容)。
——那些文字那些畫,就是他這個人。
大概是關於感受
寫,對我來說,並不容易。可是不寫,更不容易。而每次沿著感覺探尋,都像向冰山之下懸吊一條繩子,一直拉一直拉,總是會打撈到一點甚麼。
《放風》已經是20年前的書了。一步一腳印。現在我那本封面紅線上的膠紙已經發黃,紙頁也變啡變脆,但那些在書頁以外的,關於《放風》的小事,我的種種尋常片刻,各種眼前逝去,卻因寫著這篇文章而柔柔浮現,像把身處的扁平世界充氣,怦然地豐盈起來。
恍恍走到這一年之末,在甚麼也不想的寒夜,巨大又渺小的生命面前,我總是感受到一些非常真實、細微的甚麼,並微微地起了雞皮疙瘩。
[1]作者自述: 1955年 ,繪畫人,旁及寫作/電影/音樂,所有創作莫不來自繪畫;歸於繪畫。 一井多源;一源多井。
[2] 尤其寫好友麥顯揚的文章,讀到作者躲在文字背後的不忍,疼痛,深情。
[3] 他在《水底行走的人》說過:當然有恐懼,冇恐懼點創作。
[4] 〈更大的事業〉
[5] 〈遊大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