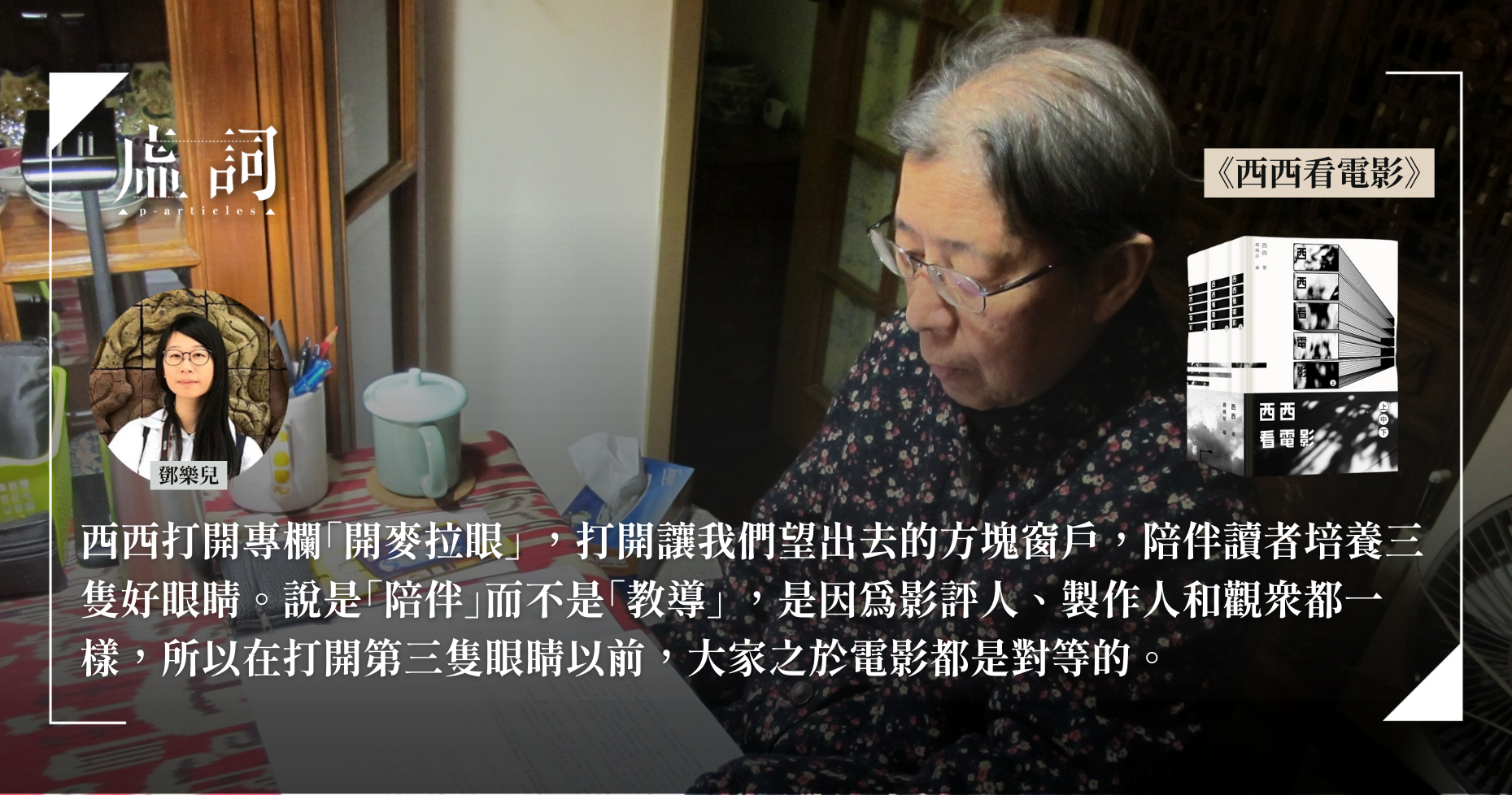打開你的開麥拉眼:打開《西西看電影》
書評 | by 鄧樂兒 | 2024-09-03
看西西看電影
當打開厚厚的三冊《西西看電影》,我們想看的是甚麼?
如果想看「西西」,我們可以追蹤她從六十年代「電影時期」走向小說創作的足跡,從《夢斷城西》走向《東城故事》,從《廣島之戀》走到〈港島.我愛〉,看看電影內容和技法如何在文字中蛻變。[1]
如果想看「電影」,我們不難從影評專欄回到六十年代讀報的現場,拼湊出香港對世界電影的接受、本地電影製作的演變,以至電影院的經營面貌。又或者把地域的距離化為時間,於今日重新從西西的引介中認識經典電影和導演,悄悄收集有趣又傳神的小比喻:如果英瑪褒曼是顯微鏡,費里尼就是萬花筒;如果愛森斯坦的線條是直的,費里尼的作品就像水,「放在臉盆裏就圓,放在浴缸中就方」;[2] 至於希治閣?「他能當參謀,不適合做軍長」。[3]
那如果今天天氣太熱雨太大,不想在文本和時空之間來回旅行,那不如我們就收起腳步,張開眼睛,先專注看看如何「看」?看看如何在眉間打開一隻「開麥拉眼」?
甚麼是「開麥拉眼」?這是橫跨六十年代前後期西西於《新生晚報》和《香港影畫》的專欄名稱,亦是其影話中不時提及的名詞。她說:「如果塞尚在,一個蘋果可以拍成一部電影作品,塞尚可以展示一個蘋果的形態,塞尚有那麼的開麥拉眼」,這麼的開麥拉眼,是一個攝影機鏡頭,一種展現的形式,「實實在在就在展示事物當刻的形態」。[4] 但她也說「這樣的朋友,我敬仰他們。因為他們是真正愛電影的,他們才是打開了開麥拉眼的人」,[5] 那樣的開麥拉眼,又變成了認真研究如何看電影的觀眾眼睛。
那麼,從攝影機到觀眾,到底甚麼是「開麥拉眼」?
三隻眼睛和一個腦袋
開麥拉眼先是Camera Eye,是放大縮小、加速放慢、看肉眼所不能看的技術化視覺:「攝影機有這樣的本領:可以給我們看見我們肉眼看不清楚,看不仔細,看不準確,甚至看不到的東西。」因此西西從電影的開端談起:「馬在奔跑的時候,四蹄是同時離地的?」為了回答這問題,二十四台攝影機連環拍攝馬匹奔跑的動作,而連起來的照片就成為了活動的圖畫。但那還不是西西的開麥拉眼,只是跑馬場的「電眼」:「快活谷的電眼的設備,就是為了看馬,仔細地看馬。重要的是:仔細地看。準確地看,清楚地看。看到的看。」[6]
惟有當這種視覺帶來填補肉眼不足的「快感」,帶來其他藝術形式(而非日常肉眼觀看)不能實現的視覺經驗,那才是電影:
我們要以電影替代我們肉眼的不足,像《梁山伯與祝英台》裏面,我們實在應該特寫祝英台的耳環。作為舞台劇,那是不可能的,作為電影,那是要爭取的。要讓我們能夠得到一種「馬奔跑的時候,四蹄是同時離地的」滿足的快感。滿足我們眼睛無法辦得到的以別的事物辦到而有所收獲的快感。[7]
有趣的是,雖說「快感」,雖說「替代肉眼的不足」,西西卻少有強調超越人類肉眼的視覺衝擊,亦不欣賞「以特殊來取悅眼睛」的電影作品,[8] 反而經常着意連結鏡頭效果與日常觀看方式的共通處。「當然人是應該眨眼的,電影也應該眨眼的」,[9] 所以變成了電影的「割接」;漂亮的女生,我們總是老遠就發現了,然後看着她站在櫥窗前抱着禮物,再着急要細看她的臉,所以變成了「遠景」、「中景」和「特寫」,「電影中鏡頭遠近是因為眼睛看東西時習慣集中或選擇,並同時捨棄或歸還」。[10]
觀看的經驗成為了我們和電影的共通語言,讓我們輕易理解鏡頭的「意義」,譬如「搖鏡」意味着「尋找」:
大家且起來走走路,就知道自己的眼睛不會用Pan的方法看東西。……除非我們在找尋,我們會「搖」自己的眼。電影也一樣,既然不找,就不必「搖」。[11]
這種「輕易理解」,也就是西西認為視覺不同於其他媒介之處。她想要把過路處地上的Look Left畫成一隻眼睛和一個箭咀,讓人不必思考就能領會,一如「拍電影是應該簡潔的,整個的電影可以讓你想三天三夜,但一個畫面絕不能讓人想三分鐘,我們要能夠迅速接受每一個畫面」。[12]
但既是如此,電影又如何「滿足我們眼睛無法辦得到的以別的事物辦到而有所收獲的快感」?「我們眼睛無法辦得到的」不只是定格馬匹四足離地的瞬間,卻亦是獲得他人的眼睛,看見他人的世界。尤為重要的是,如此「看」就直接成為「感」,令觀眾因視覺的直觀易感而感受他人的感受:「只叫我們看。但我不想看,我想感。[13]」所以西西期望電影能與文學不同,能讓我們體驗《生葬驚魂》中困於棺材之人的恐懼和焦急,也讓我們看見《變形記》曱甴眼中的世界:「讀《變形記》時,卡夫卡要對我們描繪曱甴,但上了銀幕的話,曱甴就和我們二位一體了。[14]」我們可以換上哭呀哭的人的淚眼:「導演就應該硬把觀眾都當作是那個哭呀哭的人,把戲院裏所有的眼睛混合為那個哭呀哭的人的眼睛」,[15] 自然也可以盜取「神」的眼睛,穿門入戶窺探人物的祕密,知道角色所不知道的:「我們這些人為甚麼一天到晚都喜歡看電影呢,原來是因為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們都是神。[16]」
因此,「開麥拉眼」打開我們的第三隻眼睛,卻不是外加的電子配件,而是內存於我們之中的另一種觀看經驗:
我想過的了,如果電影就是鏡子,畢加索怎麼辦?你的兩隻眼睛在鏡子裏面是兩隻眼睛,但畢加索看見你有三隻,他反映你的第三隻眼睛。你的第三隻眼睛打從哪兒來的呢?鏡子不是畢加索。攝影機也不是畢加索。現在,我們就希望電影能夠反映出我們的第三隻眼睛,攝影機不要老那麼固執地一天到晚老老實實地把自己當作是獨眼龍。[17]
攝影機的鏡頭,不過是反映事物客觀形貌的「獨眼龍」,電影卻要二加一等於三,促成「獨眼」和我們「雙眼」的配合和對話,構成「看」/「感」、客觀/主觀混和的表現和接受方式:「主要還是眼的問題。外眼和內眼的問題,肉眼和心眼的問題。所以,要給我們的內眼心眼看電影,要讓我們感到」。[18]
然而,西西並未忘記,這隻獨眼龍畢竟不是我們的雙眼,擁有的也是全然不同的本領:
攝影機有時動有時靜,它們看東西可以很正常,可以和我們眼睛看出去的世界一樣,時間和空間都沒有改變,那是自然化。但電影畢竟不是我們的眼睛。電影除了反映「自然」的自然化之外,還可以來一下「自然的加工」(一般人就叫它做藝術),成為電影化。[19]
「自然化」和「電影化」的分界,並不是判定「藝術」的標準,亦不純粹是視覺效果的經營。「電影化」對觀看習慣的刻意打破,中斷了「看」和「感」的同步,卻是故意迫使我們後退一步,把代入的「感」切換為抽離的「思考」,把「開麥拉眼」變成「開麥拉腦」。譬如突然加插的「交替剪接」既是緊張之「感」,也可以提醒觀眾注意電影的手法:「而交替剪接的出現也往往是逐漸導向電影的高潮,觀眾緊張之餘,就不會覺得悶,不去想電影中的手法了」;[20] 彩色電影普及後仍以黑白拍攝,則可以把銀幕隔絕於我們生活的彩色世界,需要時亦能隔絕於美:「所以黑白是『拒』人於外,叫觀眾們袖手旁觀一點」、「所以,一些『暴動』,『戰爭』,『謀殺』的畫面,是不適合用彩色的,要不然,我們會想,原來戰爭這麼漂亮,原來謀殺如此多姿多彩」。[21]
因此,甚麼是「開麥拉眼」?那遠不只是「開麥拉的眼」,而是對電影的本質、對如何拍/看電影的思考,是「開麥拉VS眼」、「開麥拉+眼」,亦是「懂得開麥拉的眼」,並且這隻眼睛,理應時刻與我們的雙眼、心靈和腦袋同步:「電影不光能用眼睛拍,開麥拉眼只是攝影師之蟲技,電影所需的乃是開麥拉腦,加上一顆開麥拉心。[22]」於是,電影造就我們的開麥拉眼,而又只有懂得開麥拉眼,我們才學會看電影。
打開觀眾的眼睛
為此,西西打開專欄「開麥拉眼」,打開讓我們望出去的方塊窗戶,陪伴讀者培養三隻好眼睛。說是「陪伴」而不是「教導」,是因為影評人、製作人和觀眾都一樣:「是呀,我和你一樣,有二個眼睛一個鼻子,也有一個嘴巴」,所以在打開第三隻眼睛以前,大家之於電影都是對等的:「製片人和導演還不知道甚麼是『好』的,觀眾還不習慣甚麼是『好』的。」[23]
當我們反覆談到電影媒介中大眾的參與模式,以及感受藝術方式的變化:「漆黑放映室裏的觀眾是檢驗者,不過這位檢驗者是在消遣」,[24] 西西卻於《新生晚報》「開麥拉眼」第一篇即開宗明義,執意提醒觀眾拒絕消遣:「逛百貨公司是一種消遣,逛百貨公司就不等於看電影。[25]」我們不需要過多的散心遊玩,而需要專注的感受和思考,與接受其他藝術無異。
惟有訓練好眼睛,觀眾方可以實現「共同創造」的責任。責任既體現於對一部現代電影的接受:「有些導演在創造電影時純粹給出許多的提示,觀眾如果不肯聯想,不共同創造的話,就沒法和編導的心境溝通」,[26] 也體現於對電影製作水平的監督:「觀眾的興味就是電影的指南,我們常常罵國語片的陳腔爛調嗎,不如罵我們自己不長進吧。[27]」
所以觀眾、影評人都必須與電影一起奮力向前奔跑:「每一個看電影的人都應該對電影方面的知識盡量求知,這等於是在沙漠上行軍,電影向前奔,影評人向前衝,難道你獨個兒留在沙漠上等死。[28]」向前奔跑,眼睛也要瞻前顧後,反覆調整,才能覓得觀看更多風光的角度。1964年西西曾言「依我看,從電影來說,形式比內容稍重些」,[29] 1967年她卻又回心轉意:「我現在想清楚了,形式和內容,還是內容重要些」。[30] 這可不是西西三心兩意,卻是當時電影已從技法的不成熟,跑向了另一個階段:「不錯,電影是進步了。因為大家都懂得電影最容易騙人,技巧是最可以搬演的,銀幕上的畫面和節奏都已經進入了新的境界」,卻跑呀跑又跌進了另一個深淵:「我們不再嚷悶,可是,我們又落進了另一個深淵裏,因為,我們忽然醒悟:我們空洞」。[31]
當打開厚厚的三冊《西西看電影》,西西卻讓我們不必看她的影評:
如果我們能夠開啟眼睛,能夠思想,我們還用得着別人來對自己說:「看這電影,不看這電影」──嗎?[32]
但1967年以後,我們已奔跑了多少年?跑出深淵了嗎?跑回頭了嗎?還是全新的電動車開得太快,兩側的風景已叫人眼花繚亂,而開麥拉早獲得了自己的意志,張開一隻巨大的眼睛反過來凝視着我們,讓我們在目眩神迷之中忘記了「開麥拉眼」,甚至忘記了我們的眼睛、心和腦袋?如果你是慶,你還能不能發現奧林匹斯生病了,能不能切除它腦裏的瘤?或是你的眼已經悄悄被移植成奧林匹斯的眼,阻斷了屬於你的思考和感受?
但西西半世紀以前的聲音,至今仍然在遙遙提醒你:如果我們能夠開啟眼睛,能夠思想。
[1] 參見趙曉彤:〈作為意向的地方:論西西〈港島.我愛〉對《廣島之戀》記憶策略的改寫〉,《中外文學》第45卷第1期(2016年3月),頁195-219;趙曉彤:《西西一九六零年代影畫寫作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13年。
[2] 西西:〈《中國學生周報》「電影與我」.二十九〉,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香港:中華書局,2022年),頁65-66。
[3] 西西:〈《亞洲娛樂》非專欄文章.電影筆記(二)〉,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中冊(香港:中華書局,2023年),頁281。
[4] 西西:〈《中國學生周報》非專欄文章.開麥拉眼〉,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90。
[5] 西西:〈《香港影畫》「開麥拉眼」專欄.四〉,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中冊,頁304。
[6] 西西:〈《新生晚報》「開麥拉眼」專欄.八〉,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147。
[7] 同前註。
[8] 西西:〈《中國學生周報》非專欄文章.開麥拉眼〉,頁92。
[9] 西西:〈《星島晚報》「特稿」.談電影的「眨眼」〉,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下冊(香港:中華書局,2024年),頁34。
[10] 西西:〈《香港影畫》「開麥拉眼」專欄.二十一〉,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中冊,頁375-377。
[11] 西西:〈《香港影畫》「開麥拉眼」專欄.二十〉,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中冊,頁374。
[12] 西西:〈《香港影畫》「開麥拉眼」專欄.一〉,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中冊,頁293。
[13] 西西:〈《中國學生周報》「電影與我」專欄.二十三〉,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54-55。
[14] 同前註。
[15] 西西:〈《中國學生周報》「電影與我」專欄.二十二〉,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52。
[16] 西西:〈《中國學生周報》「電影與我」專欄.二十五〉,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58。
[17] 西西:〈《中國學生周報》「電影與我」專欄.二十二〉,頁52。
[18] 西西:〈《新生晚報》「開麥拉眼」專欄.四〉,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141。
[19] 西西:〈《中國學生周報》非專欄文章.電影文法:C〉,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115。
[20] 西西:〈《香港影畫》「開麥拉眼」專欄.九〉,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中冊,頁328。
[21] 西西:〈《香港影畫》「開麥拉眼」專欄.十八〉,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中冊,頁364-365。
[22] 西西:〈《香港影畫》「開麥拉眼」專欄.二十一〉,頁378。
[23] 西西:〈《中國學生周報》「電影與我」專欄.二十〉,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48-50。
[24] 華特.班雅明著,許綺玲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9年),頁100。
[25] 西西:〈《新生晚報》「開麥拉眼」專欄.一〉,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138。
[26] 西西:〈《新生晚報》「開麥拉眼」專欄.二十六〉,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172。
[27] 西西:〈《香港影畫》「開麥拉眼」專欄.十六〉,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中冊,頁356。
[28] 同前註,頁357。
[29] 西西:〈《新生晚報》「開麥拉眼」專欄.三十六〉,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185。
[30] 西西:〈《亞洲娛樂》非專欄文章.電影筆記(二)〉,頁279。
[31] 西西:〈《香港影畫》「開麥拉眼」專欄.三〉,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中冊,頁303。
[32] 西西:〈《中國學生周報》「電影與我」.十八〉,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冊,頁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