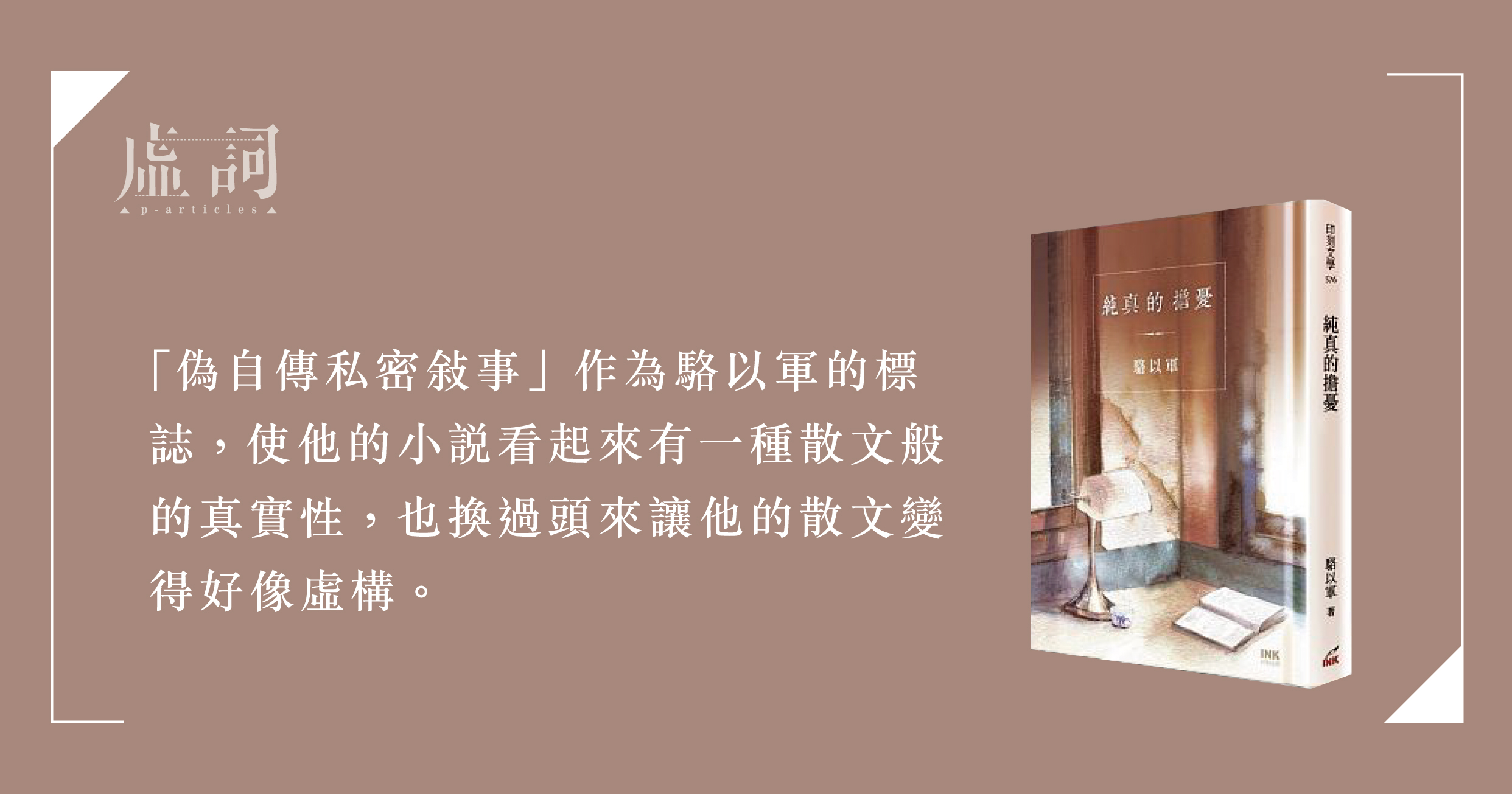作為小說家的基礎零件——讀駱以軍《純真的擔憂》
也許我們不只一次聽過關於駱以軍的某些故事零件:大學時期在陽明山上,孤獨地在某些夜裡,對空蕩籃框反覆苦練跳躍,也是在孤獨的夜裡,臨案抄寫馬奎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川端康成的小說、苦苦追求尚未成為妻子的女友直到她與時任男友分手,與她開著一輛破車到處旅行直到結婚、極其嚴重的憂鬱症與失眠,使他將身體當成某種煉丹壺甚麼藥也吞得進去並在質素極差的睡眠裡一個夢接著另一個夢……關於小說家駱以軍,他的敍事彷彿來來回回,都會回到這些書寫零件上。最近在新的散文集《純真的擔憂》面世時,我又重臨一種好像以前讀過的感覺——déjà vu,既視感。
十月,印刻文學同時出版了兩部駱以軍的新作,《計程車司機》收錄他的Facebook發文、《純真的擔憂》則收錄他的專欄散文,在Facebook上他寫道,它是一本安靜的小書,最開始是在香港《明報》的一個小專欄,叫做〈失落之物〉。失落與空虛,其實一直都作為駱以軍的書寫母題,但最後他仍選擇了另一篇散文〈純真的擔憂〉作為書名,好像在提醒讀者好像要換個角度切入,這些重重複複的拼裝零件,在反覆說了將近20年後,磨耗破損以後還有甚麼可以剩下的?抑或說,在無盡的重複拼裝以後,產生甚麼新意?
小說是輛拼裝的二手車
《純真的擔憂》全書分五個章節:〈靜靜的生活〉、〈失落之物〉、〈天空之城〉、〈如夢的繁華〉及〈無人知曉的〉。散文集從他的家庭軼事展開;到第二章是拿手主題「失落」,寫生命各個時刻遺棄了的人事物;隨後三四章寫昔日在陽明山上的大學時光,以及圍繞著文學所發生的事。最後〈無人知曉的〉並不是指從未發表過的故事,這章裡頭有不少故事也能對應上其他文章或演講,無人知曉的其實是不同人的細微心理,那些不寫出來就會被錯過,被忽略,被否認或錯認的一些心事。一些傷害。一些傷感。或一些擔憂。
既視感是讀《純真的擔憂》時令我又愛又恨的感覺。當然,假如你沒讀過他過往的作品,他的演講與散文肯定能打動你,一部「廢柴胖子」的奮鬥史,而命運不仁總向他開殘忍的玩笑。但如果你早已讀過他的不同作品,就會察覺那些勵志或被遺棄的傷害敘事,幾乎成了駱以軍的起手標誌。如〈山中時光〉一篇,「想起我二十多歲,租屋住在陽明山那些破爛的、山中溪邊的學生宿舍,就覺得非常懷念。」接下來你可以預期幾個發展方向,其一是練習投籃,其二是狂熱地抄寫小說,其三是開著破車與豬朋狗友或妻到處晃,其四是養小動物等等,還有其他相類近的故事,這本書自然是一個不漏地,全用上了。
又如夢境、又如婚後生活、又如帶孩子,零件一直都重重複複。如此一來,我要問的是:《純真的擔憂》與其他作品有何差異,尤其是當你忽然覺得,這書彷彿就是長年掛在他嘴邊的拼裝二手老車——小說在不同外殼下,零件與機械有好多重複的組成元素,再添上一些晚近發生而與舊故事具有親緣性的新零件。
小說是接力賽跑的環狀運動場
王德威所分析的駱以軍,是場「接力式碎片故事長跑」,是「偽自傳私密敍事」,只要小說家還想說話,他就可以跑得無限遠,讀者就跟著他跑直到其中一方耐力不支倒下。而黃錦樹就認為這種要命的跑法有點不太健康,「《西夏旅館》應該刪掉一半,沒必要學步董啟章搞冗長臃腫那一套。」這些駱以軍式的小說標誌,如果分拆開來,可以在《純真的擔憂》裡找到不少零件碎片。我曾誤以為自己破譯了某種密碼,錯覺自己破了關——結構主義式想像——如果無限繁殖的故事,就出自那些原初零件,只要全部收集起來,也許可能,某日就能建築/還原出一個新的駱以軍?或以董啟章的話來說,駱以軍2.0?
在駱以軍長篇小說《匡超人》裡,王德威用「洞」作為中心意象去理解小說家的最新狀態,「如果『棄』觸及時間和慾望失落的感傷,『洞』以其曖昧幽深的空間意象指向最不可測的心理、倫理和物理座標。」隨著中心意象的亮起,駱以軍開始用無數故事繞著這個主題跑。所以我會打個比喻:駱以軍的小說是個運動場,書寫作為一種運動(稍微借用楊凱麟的用詞),他兜著圈跑不太一樣的軌跡。
在散文集的〈化作春泥更護花〉一章裡,他悲傷地與自殺死去的台灣作家們對話(這種對話方式可以與《遣悲懷》對話):「比起邱(妙津),我多活二十二年了;(黃)國峻,十六年;(袁)哲生,十年。我很努力,應該若遇到那被時間凍結的你們,不會羞愧自己比起年輕時的自己,下墜了,腐朽了,靈魂的感受纖維固化了。我交出的作品,可能也就是最初寫《降生十二星座》的我,在這後來的時間流刑裡,天賦耗盡,所能交出的極限了。重來一次,我或也無法做得更好。」這場書寫運動,可能就只是兜著圈跑運動場,有天提不起力氣就要離場了。
小說是以純真心靈去面對傷害
但正如一個人不斷繞著運動場跑步,看的東西都會產生變異,駱以軍從「棄」跑到「洞」,如今跑到了「純真」。這是程度的差異。在「棄」時期的駱以軍是暴戾的,他寫被遺棄,被命運無緣無故地玩弄,於是在《西夏旅館》等作品裡,血肉橫飛,人與人之間的傷害從心理到生理都是摧毀性的。而後來的「洞」則是困惑無助的,它看不清楚,摸不透徹,但始終都在那裡,引發駱以軍的焦慮,《匡超人》裡的情感雖然沒棄那麼強烈,但仍是有一定強度的。直到《純真的擔憂》,情感弱化極多,彷彿一種似有若無的托腮,稚童凝視窗外稍稍皺眉的情境。
王德威分析《匡超人》時寫道,「這些年駱以童言戲語的『小兒子』系列書寫成為網紅,在某一程度上,可以視為雞雞敘事的熱身。」這裡指的是破洞的意象,也是從棄到洞的轉移。但「小兒子」系列同時也是《純真的擔憂》的熱身,被遺棄的人從家庭重新接觸童真與溫柔,在破洞的空虛失落以外,對世界稍微擔憂,一個更親和的駱以軍正慢慢蛻變著。
這本書也寫傷害,其中〈很小很美的一件東西〉裡寫妻子的一次經歷,她一直堅持著「任何事情都該用柔慈的方式對待」,但在一次摩托車意外中,她受到摩托車騎士的誣衊,這種都市裡發生的暴力與不仁使妻悲傷:「我以為會有人和人直面相交時,有真實的柔和的東西發生。現在好像這些比較美好的東西,這樣流失掉了……」
書中寫傷害的手法是比較輕的,場境、人物或故事距離駱以軍都相對抽離,那是一種擔憂,擔憂這些無理傷害會落到身旁的人身上。但他能做的僅僅是擔憂,這是無力的,也是疏離而無法伸出援手的狀態。因為事情就是按你無法理解的軌道,就此發生了。又如〈夏日煙雲〉一篇,這篇的名字與《西夏旅館》第二章是相同的,但相比旅館裡發生的性暴力、引誘與無能,這篇散文寫的是一種關於時代的擔憂: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世界,應該跟從前的那個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了吧?駱以軍想及一個失散多年的女孩(也許是《遣悲懷》裡的一個少女),「沒移民到網絡世界,她竟就像煙一樣在這世界蒸發了,消失了。」相比起「棄」與「洞」,他擔憂的是她到哪裡去了?在繞著小說運動場跑圈之時,《純真的擔憂》開啟了這道比較柔和的書寫通道,讓我們在重溫熟悉的故事時,讀到新的觀感。也讓尚未讀過駱以軍作品的讀者,看到一個讓傷害故事溫柔綻放的人。
小說是對舊友重新招魂
「偽自傳私密敘事」作為駱以軍的標誌,使他的小說看起來有一種散文般的真實性,也換過頭來讓他的散文變得好像虛構。虛實界限的模糊化甚至拆除,讓我讀這書時彷彿讀一部長篇,其中與前作對話的部份又讓我宛如在讀連載。這種閱讀經驗會讓我願意將其讀完,其中尤其驚喜的是看見他的童年玩伴謝至道的登場,在〈逃家〉一篇裡他寫他們「在某一堂下課,躲在校園一處樓梯死角的一個大箱子後面」,我仍印象深刻地記得駱以軍在《遣悲懷》裡寫這個情境:「謝至道的臉開始扭曲變形。他的鼻子也掉下來了、他的嘴巴像釘鉤釘歪的壁飾版畫那樣歪斜著,他的眼睛像用貼紙貼的少女漫畫眼睛這時膠水不黏而剝落掉下……」如今謝至道在散文集裡作為一個完整人類出現,總覺得真是彷如隔世。
上次在台北的咖啡廳碰到駱以軍,正是他在散文集裡寫「因為他抽菸,而這間咖啡屋有一塊略高出平地木搭平台的憑街外區桌位」那家,由於吸煙區最後一個位置被我佔了,他得換一間咖啡廳。我向他打招呼時,他無法在腦裡龐大的社交網絡裡定位我的座標,很客氣以一種帶距離的親切向我用力揮手,我那時想,親和力還真是高。也許這就是書裡所寫的純真,在暴虐的棄與傷痛的洞後仍保有日常的親切。又如《純真的擔憂》剛出版時,他人正身在香港,在Facebook上寫「現在人在香港,在大學旁的一家小pub」,我往日正是在大學旁的小pub,那種夏日煙雲,把駱以軍的作品一篇接一篇地讀,然後動身報考台灣的研究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