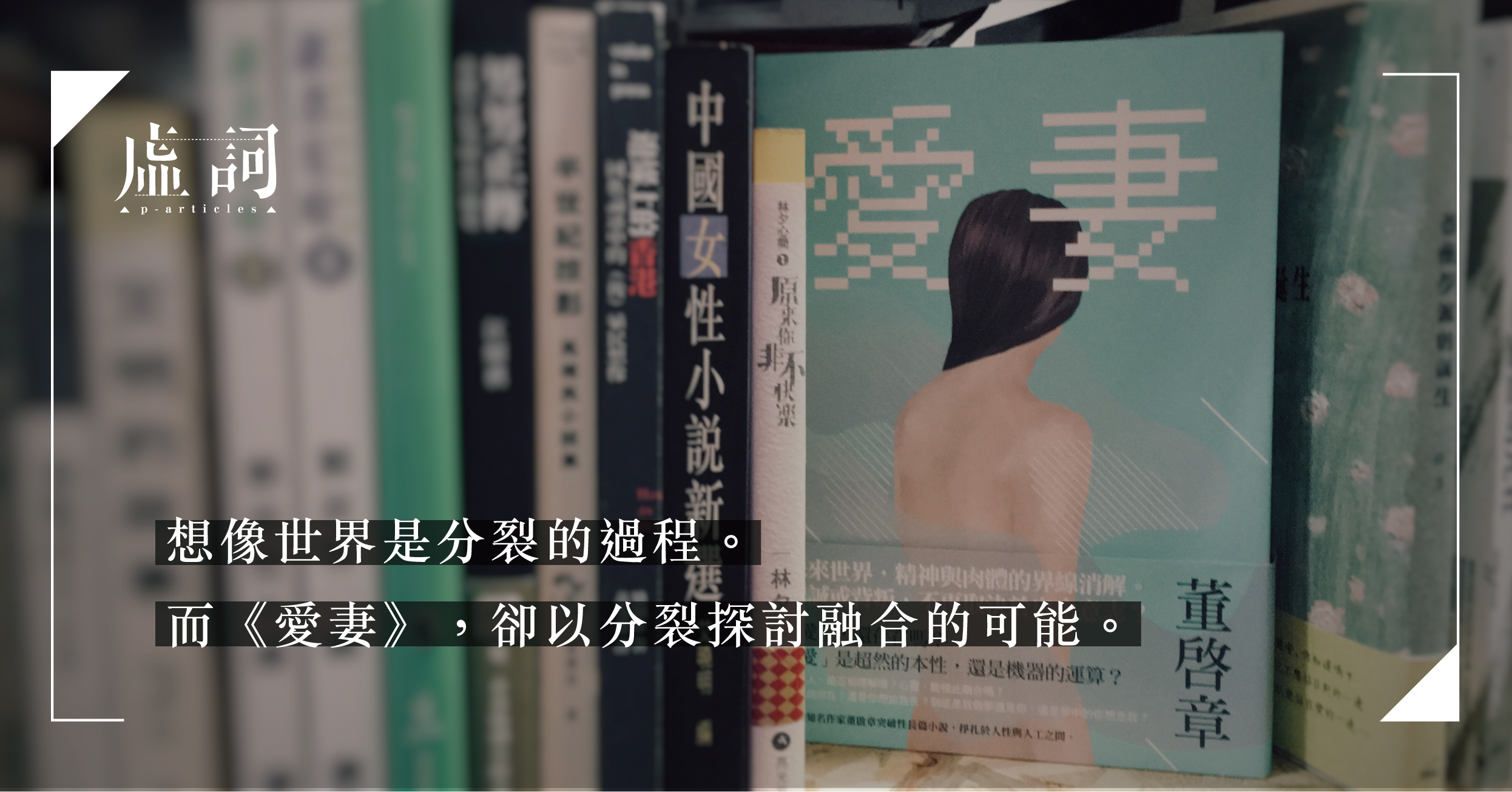心身如何融合︰談《愛妻》的愛
書評 | by 林雪平 | 2019-01-03
評論《愛妻》,甚至「精神三部曲」,我覺得頗為沉重。循著「精神史三部曲」閱讀的人,可能想看董啟章如何評論文化研究式的文學評論。該方面的研究相當有意義,尤其在於處理由「必要的沉默」引伸的事件與變化。然而,在理清「精神史三部曲」之前,我沒有辦法仔細地處理這議題。不過,讀完《愛妻》後,我卻疑惑「愛妻」到底是否只能是一個稱呼?我想起《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其中一幕:眾人在糖水會上討論何為人的源始,有人說是語言,有人說是意識,或者歷史、精神性、為性而性,最後主角阿芝卻說「人類的起源是愛!」。
當時,我立即合上書,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愛是運動,由內往外延展
愛?我難以想像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說「人類的起源是愛!」,我會如何反應。我非常理解為何「大家也有點不知雙手和身體如何安放的尷尬」。當然,也許作者自己都知道,這個答案非同凡響。然而儘管尷尬,董啟章依然安排這個情節,就是因為「愛」是他世界觀的核心。
對董啟章而言,到底甚麼是愛?阿芝解釋:
但是有一天,一個雌性人類和一個雄性人類在生存和生育需要以外,彼此產生了依戀和不捨的感受,而這種感受甚至比所有其他因素變得更加強烈,到了不惜為了對方的安危而犧牲自己的程度,這一刻就是「愛」的誕生,也就是「人」的誕生。[1]
換句話說,這裡所指的愛是一種狀態。當個體為他者犧牲,即個體視角超出自身物質基礎,進入他者的視角時,這種狀態就是「愛」。類近的描述,我們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中都可以讀到:維珍尼亞從父親的筆中讀到,愛最為純粹的形式,就是由內部往外輻射,擁抱整個外部 [2]。董啟章所謂的「愛」,至少在「自然史三部曲」中,都可以理解為個體由內往外輻射的運動。
處於意識與肉身之間的愛
《愛妻》中,作者借岸聲引入德日進對於愛的解釋:「愛是一種能量」[3] ,是事物內在的精神性,推動著外在的物質與另一事物互相融合。但是精神與物質的關係,本身就是個難題。小虎指出龍鈺文的「身心不協調」[4],也是對應著這點。讀《愛妻》時,首先引起我興趣的問題是,沒有身體的意識存在嗎?換句話說,沒有物質的精神存在嗎?假如精神必須建基於物質基礎,那麼物質如何才能避免淪為精神的囚牢?
其實以上這些問題,在董啟章創作一直有跡可尋,例如在《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中(或稱為卡門)有性別認同障礙,也是身心衝突的代表角色。如果此書是一本成長小說,正如書名所致敬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一樣,當中的成長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於調和身體與意識的衝突。但是《愛妻》與前作不同之處在於,《愛妻》是一本科幻小說。小說,對於董啟章而言,「通過想像去營建意義的方式。」[5] 再加上Quentin Meillassoux所說,科幻小說的重點,「是透過挪動科學知識,來為人與世界的關係打開種種可能。」[6]《愛妻》是一本科幻小說的意思是,董啟章計劃挪動科學知識,來思考愛的問題。書中的「葉靈鳳機器」,可以視為測試精神與物質的關係的實驗裝置。有了新的方法,小說中所呈現的愛也顯得帶點不同。
實驗裝置首先告訴我們,心身不能分開。裝置設計者余哈解釋:「我說的是一個『觸媒』的必要,也即是一個跟葉靈鳳的精神相交接的另一個精神,去把那已經失去實體(也即是肉體)的葉靈鳳精神重新實在化。」[7] 純粹精神性的葉靈鳳並不能實在化。同時間在〈浮生〉中,我們亦見到「觸媒」之必要非虛。換言之,沒有物質的精神並不存在。
反過來說,沒有精神的物質亦不能認知。作者對於這點的實驗一直潛伏在故事設定:在小說的後半部分〈浮生〉中,主角佘梓言的妻子說,主角原來早已突發性中風,腦部缺氧,「在進行意識複製後一個月,你的腦部狀況急速惡化,已經不可能維持生命功能,意識也漸漸消失,基本上就是一具敗壞中的空殻。」[8] 另外,余哈亦提及「敍述功能,就是把由記憶所構成的所謂自我的所有資訊,整合成一個簡單易明的故事。」 [9] 身體感知而產生的記憶碎片,需要精神來整合,才出現所謂的主體。所以無論對於人,對於愛而言,精神與物質彼此互相依賴。
分裂與融合
想像世界是分裂的過程。而《愛妻》,卻以分裂探討融合的可能。
想像是分裂的,因為它由當下的真實世界出發,另闢蹊徑。但如果想像是純粹的思維活動,將會是一片混沌,如書中所言,「矛盾與混沌、斷裂和縫隙,肯定是『精神世界』的重要特徵。」[10] 於是,一致的肉體便相當重要。基於精神的不一致性,「葉靈鳳機器」需要一具肉身,將「種種不一致的特徵,又同時「『一致地』納入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體系中」[11]。
這設定不同於傳統的身心二元理解,亦即德日進所反對的傳統。一如岸聲提到,「[德日進] 自小就被教導,只有精神或靈性才是永恆的事物。世間的物質要麼就是暫時性的、會變質的、低層次的東西,要不過就簡直是拖垮精神追求的罪魁禍首。」[12] 然而,假若精神如此獨立無瑕,便會引起衝突。某個精神(夫)的外部,實際上亦存在另一個精神(妻)。兩個過於倔強的精神在體內相撞,便無法調和。所以,董啟章需要一副維持一致性的肉身,來組織相異的精神。
於是讀到結局時,我有點驚訝,董啟章想像的分裂竟然逆向操作。他不再以肉身盛載著單一精神的不連續性,而是將兩個精神融合於一副肉身。就小說情節而言,兩個意識記憶交錯,兩年壓縮為一年,教授成了小說家,小說家成了教授,所有存在都拖著個連接號,「佘梓言—龍鈺文」。再問:「如何才能確保佘梓言是佘梓言?」,已經沒有意義。小說中兩個意識可以對話,顯示「愛」不再是行動,而是「佘梓言—龍鈺文」的存在條件。因為愛,兩個意識向彼此暴露。而如果沒有愛,失去共同存在的平面,該暫時性的主體便會煙消雲散。
不過,這樣推展似乎走得太快。實際上,討論《愛妻》的其中一個關鍵位置,正正出於「愛」的設定當中:這種「愛」強調一個精神的超脫肉身,擁抱外部,然而對於外部的另一個精神而言,他要如何回應前者的愛?他如何接受或者拒絕?以甚麼機制判斷接受還是拒絕?小說只是蜻蜓點水帶過。所以面對意識已經脫離肉體的佘梓言,龍鈺文在小說中相對被動。
在〈浮生〉之前,妻子只是散落地穿插在故事中,彷彿是被動地再現。然而,我們不可忽視,動手寫〈愛妻〉的其實是妻子的肉身。在〈浮生〉中,妻子解釋:
我在你的意識裡,看到——或者應該說是感覺到——一股強烈的敍述欲望,也即是你長久以來寫小說的欲望吧。於是我便運用了你的記憶資訊,去演算出一個『愛妻故事』。然後,我根據演算結果,轉化為文字,記錄下來。[13]
〈愛妻〉其實是兩人意識融合後,所衍生的故事,而當中的敍事者原來是無知的敍事者,或者更精準地說是他不知道自己知道。這樣一來,作為介入者的龍鈺文反而處於主動地位。只不過,如此寥寥半頁解釋設定,難免有點單薄。如果真的要探討愛如何作為融合的推力,《愛妻》暫時只寫了一半。另一半其實是,在外部的龍鈺文精神如何面對,並且接納(或拒絕)佘梓言的愛。融合應該是雙向運動。
結局必要的性描寫
最吊詭的是,上述的設定,竟與德日進的「內部精神推動外部物質」一致。作為內部精神的佘梓言,推動作為外部物質的妻子。妻子的肉身,以及兩人的意識記憶,基於丈夫的書寫欲望重組。當初問「物質如何才能避免淪為精神的囚牢?」,也許是捉錯用神。我們真正應當擔心的正正相反。如果只談及愛作為意識的單向運動,身體便變成被動的容器,小說便會自相矛盾。所謂的身心協調,淪為精神壓倒身體。建基於這個危機,我們便能理解為何在故事結尾,會突然出現情慾環節。
或者,性其實是愛的逆向運動。小虎形容,在龍鈺文的小說中常常出現身心不協調的狀兄,「身可以理解為人的感官系統反應,以至於本能的性反應;相反,心則可以理解為意識,或者作為意志的愛。」[14] 若果愛是精神超出肉身,與另一個精神融合的話,性也許可以理解為兩個肉身在精神之下互即互入的狀態。小虎強調,「性愛不協調」當中,愛不是建設力量,性也不是破壞力量。愛與性,或者是兩個方向相反的行動。只有兩者同時運行,才能畫出一個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董啟章,《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臺北:麥田出版,二零一零)。頁504。
[2] 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下冊)》(臺北:麥田出版,二零零七),頁386。
[3] 董啟章,《愛妻》(臺北:聯經出版,二零一八),頁175。
[4] 同三,頁268。
[5] 同三,頁212。
[6] Meillassoux, Q. (2015). Science fiction and extro-science fiction. Univocal Publication. P.5.
[7] 同三,頁220。
[8] 同三,頁379。
[9] 同三,頁319。
[10] 同三,頁221。
[11] 同上。
[12] 同三,頁175。
[13] 同三,頁374。
[14] 同三,頁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