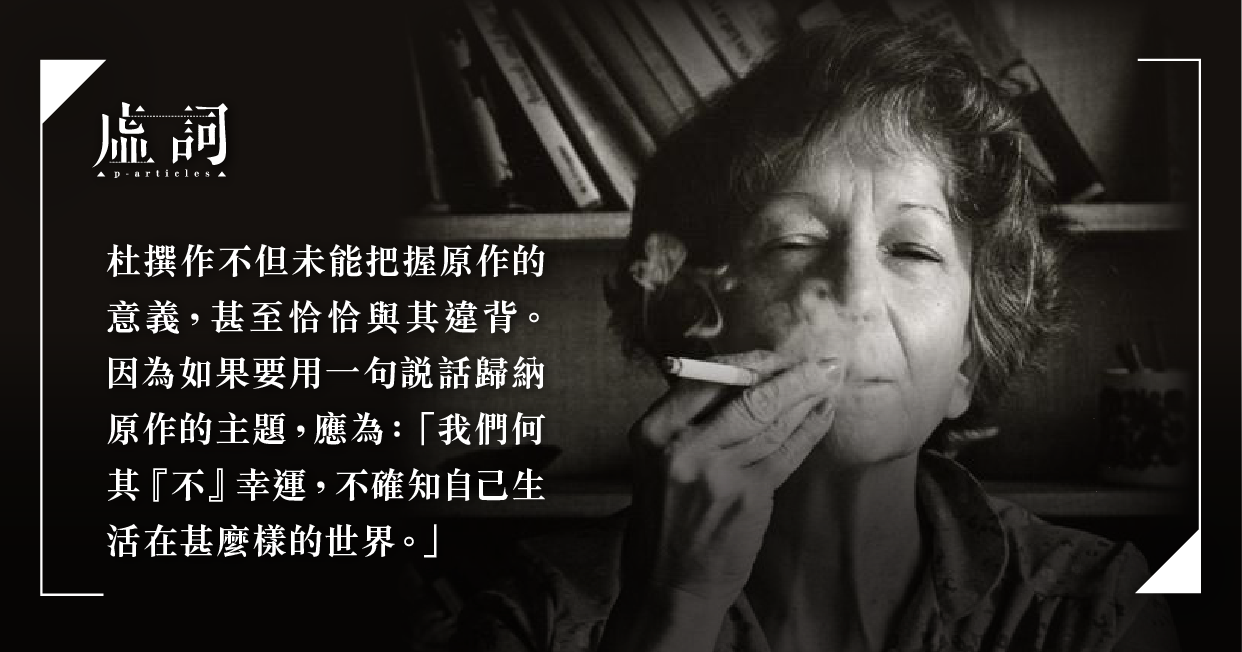【虛詞・辛波絲卡,種種可能】一樁關於辛波絲卡〈我們何其幸運〉的荒謬事件
曾經聽過一則關於DSE中文科的笑話:要應付著重例子數量的議論文,只消背下幾個歐洲地區的詩人名字作為出處,然後你便可按照題目方向杜撰任何說話。閱卷的老師不會懷疑。一來,他們沒有時間翻開詩集,檢查每個語例的真確性;二來,因為你寫下的詩人確有其人,而且是歐洲詩人,他們不敢懷疑。
我接下來要說一樁與辛波絲卡一首名為〈我們何其幸運〉的詩有關的真實事件。它與上述的笑話同樣荒謬。它發生在我身上。
喜歡辛波絲卡的中文讀者會清楚,目前要讀到她的中譯作品,不一定要到圖書館借閱由陳黎、張芬齡或林蔚昀翻譯的實體詩選。只要在Google搜尋欄輸入「辛波絲卡」四字,〈種種可能〉、〈一見鐘情〉、〈時代的孩子〉等甚具代表性的詩作就會逐一出現在眼前。至於上述提到的〈我們何其幸運〉呢?同樣在不同的內容農場與社交媒體廣傳,這首詩共有六節,首節是這樣的:
我何其幸運,
因為我不是氣象學家,
不用知道雲彩如何形成
或氣流裡有甚麼成分,
但我卻可以用我的眼採集天邊的流雲,
放在心裡細品那份最抽象的唯美。
詩歌首四節基本上遵照同樣格式。詩人雖然不通曉氣象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卻依然覺得自己「何其幸運」,因為她沒有知識,依然能用眼睛欣賞這個世界的美景,想像上帝的匠心。最後兩節延續「對世界一無所知」的「感恩」,詩人寫:
我何其幸運,
因為我不是需要說謊的政治家或律師,
也不是要在人身上開刀的醫生,
我甚至也不是開畫展前需要盤算成本的藝術家,
那我是什麼?我什麼都不是,
我對這個世界也一無所知,這,也許便是我的幸運所在。
我們何其幸運,
無法確知自己生活在甚麼樣的世界。
正因自己「甚麼都不是」,對世界一無所知,所以自然迴避了世界尖銳的部分——謊言、生死、生活的壓力——只管浸淫於自己的「小確幸」便可⋯⋯讀到這裏,熟悉辛波絲卡的讀者應該要開始覺得可疑(或不必讀到這裏,早就發現不對勁的地方)。事實上,辛波絲卡並沒有寫過上述文字——雖然她的確有一首同題的詩作,收錄於《結束與開始》(1993)一書。這首詩歌唯有開首部分與杜撰作的結尾相同。詩人(這次真的是辛波絲卡)寫道:[註1]
我們幸運極了,
不確知自己生活在甚麼樣的世界。
一個人將得活
好長好長的時間,
鐵定比世界本身
還要久。
得認識其他的世界
就算只是做個比較
得超脫凡俗人世——
它真正會的
只是礙事
和惹麻煩。
詩人同樣指出「不確知自己生活在甚麼樣的世界」是一種幸福。她的理據是甚麼呢?因為要真正認識自己的世界是非常麻煩、甚至花上超過一生的時間也不足夠,難以讓人快速地得到結論。既然如此,詩人建議:「一個人不妨告別/小事件和細節」,「不去計算週末以外的日子」。然而,思路清晰的讀者固然能馬上理解以上全是反話,更一貫了辛波絲卡諷刺、慧黠的風格。正如詩作結尾兩節:
把信投進郵筒,
愚蠢少年的衝動;
「不准踐踏草地」的告示,
精神錯亂的症狀。
書寫的意義在紀錄日常裏容易被忽略的事物,而「把信投進郵筒」則能將這些珍貴的細碎意念、觀察予以他人。但當我們決定節省時間,「告別細節」後,不論書寫還是寄信,均成了「愚蠢的衝動」。至於草地——與人無關的生態系統——它的存亡當然是無足輕重的事,但凡「正常」一點的人,也不會思考「要不要踐踏它」這一個問題。
看過原作甚具諷刺意味的詩句以後,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杜撰作不但未能把握原作的意義,甚至恰恰與其違背。因為如果要用一句說話歸納原作的主題,應為:「我們何其『不』幸運,不確知自己生活在甚麼樣的世界。」的確,辛波絲卡常以自然生態入文,也表現了對觀察萬物的熱情,但這種熱情,是基於她對知識的好奇心,近日出版的辛波絲卡傳記中文版《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裡面有提到辛波絲卡在她的讀書專欄「非必要閱讀」中,介紹最多的不是文學書籍,卻是各種各樣的科普書、指南,範疇包括但不限於:自然(譬如,關於蜻蜓或蝴蝶的書)、歷史、人類學等等,她甚至認為費曼的《費曼物理學講義》是她讀過最有趣的書籍之一。[註2] 像她這樣的一位讀者,怎麼可能會寫出「我何其幸運/因為我不是氣象學家/不用知道雲彩如何形成或氣流裡有甚麼成分」?在〈植物的沉默〉中,她便曾嘗試與植物對話,交流:[註3]
我知道葉子,花瓣,核仁,毬果和莖幹為何物,
也知道你們在四月和十二月會發生甚麼事。
雖然我的好奇心未獲回報,
我仍樂於為你們其中一些彎腰屈身,
為另外一些伸長脖子。
她又指出人類與植物的相通處:
因為關係密切,我們不乏話題。
同一顆星球讓我們近在咫尺。
我們依同樣的定律投落影子。
我們都試著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一些東西,
即便我們不了解處,也有幾分相似。
但事實上,無論詩人多麼渴望貼近、了解植物,與植物對話是不可能的事。人類對於植物的認識,也只能透過自身的觀察與學習達成,非常困難,但非達成不可:
和你們交談雖必要卻不可能,
如此急切,在我倉猝的人生,
卻永遠被擱置。
常言道辛波絲卡的詩作充滿了「形而上」的思考,意指她透過詩作滴水穿石一般往深處挖掘、思考事物的原理。她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尾聲,曾如此說:[註4]
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它是令人驚異的。
但「令人驚異」是一個暗藏邏輯陷阱的性質形容詞。畢竟,令我們驚異的事物背離了某些眾所皆知且舉世公認的常模,背離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明顯事理。而問題是:此類顯而易見的世界並不存在。我們的訝異不假外求,並非建立在與其他事物的比較上。
如果真如她說:「在字字斟酌的詩的語言裡,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或正常的」。那麼對她而言,「雲彩如何形成」、「鳥到底靠甚麼飛翔」、「光合作用的原理」,這些龐雜、需要花費精神、時間理解的事物,其實比唯美的風光重要,或是說,同樣重要。
言歸正傳(你也可以說是題外話),文首提到那發生於我身上的「荒謬事件」,到底是甚麼呢?如果你現在於Google搜尋欄裡輸入「辛波絲卡 我們何其幸運」,你會發現,這些假冒的詩句仍繼續被反覆引用,有讀者就此大發議論,更有能力兼論辛波絲卡的其他作品;還有一個部落格,貼上了中英雙語版本的〈我們何其幸運〉,然而唯有英語版本是原作。
但還有比這些事更荒謬的事:一年前,有一位讀者在IG的個人簡介貼上了杜撰作品,為此沾沾自喜,直到一個星期以後才發現不對勁。當然,那個讀者就是我。
註:
1. 辛波絲卡:〈我們幸運極了〉,收入陳黎、張芬齡譯選:《辛波絲卡.最後》,(臺灣:寶瓶文化,2019年),頁186-188。
2. 辛波絲卡:〈植物的沉默〉,收入陳黎、張芬齡譯選:《辛波絲卡.最後》,(臺灣:寶瓶文化,2019年),頁209-212。
3. 安娜.碧孔特、尤安娜.什切斯納著,林蔚昀譯:《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臺灣:臉譜出版,2023年),頁210。
4. 辛波絲卡著,陳黎、張芬齡譯:〈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辭——詩人與世界〉,收入陳黎、張芬齡譯選:《辛波絲卡.最後》,(臺灣:寶瓶文化,2019年),頁219-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