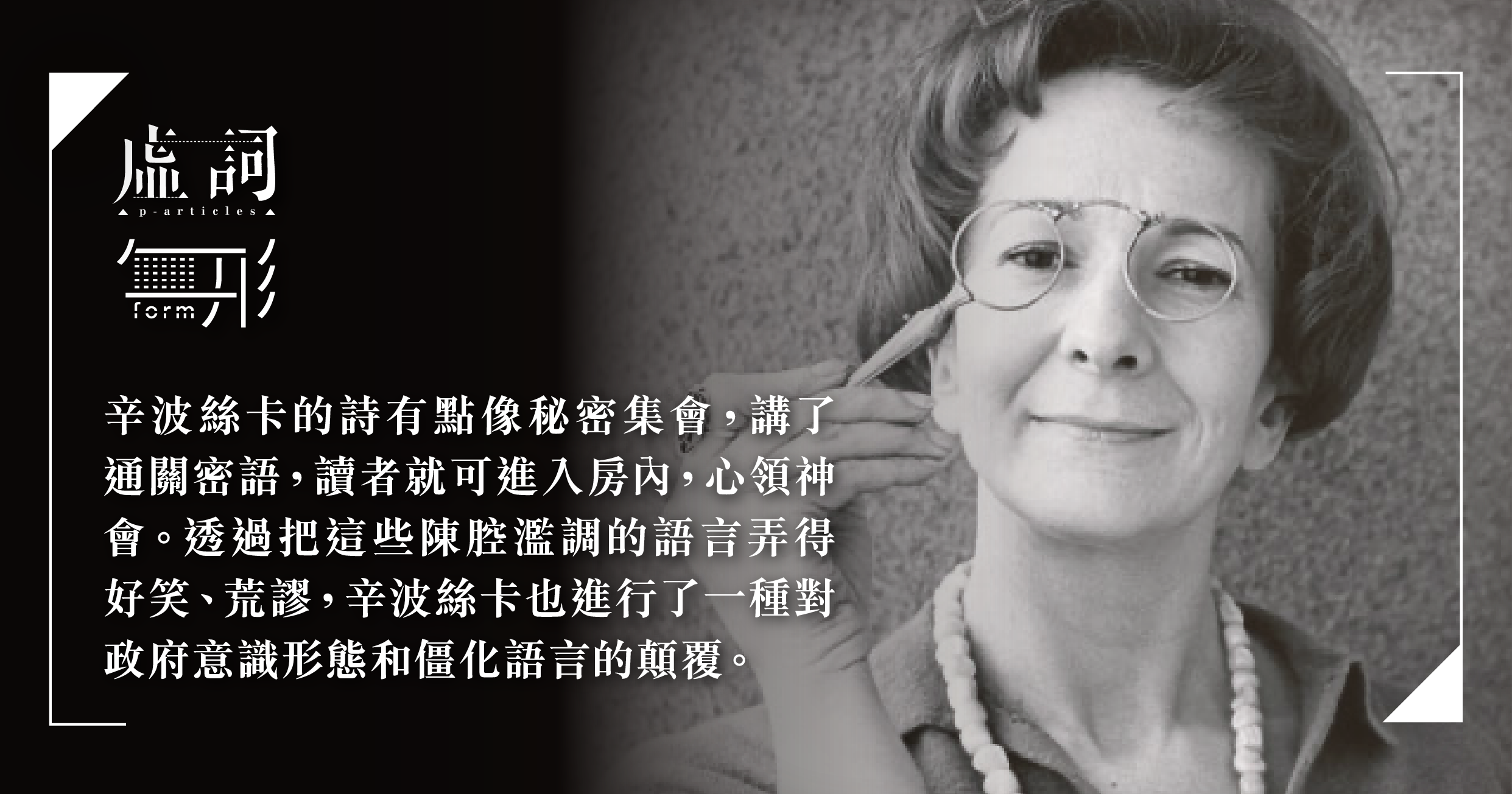【無形・辛波絲卡,種種可能】用詩奪回個人的完整性:談辛波絲卡的政治詩
其他 | by 林蔚昀 | 2023-07-11
辛波絲卡誕辰一百年,香港詩人鄧小樺邀請我談談辛波絲卡。我說,我想談辛波絲卡的政治詩。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奇怪。畢竟辛波絲卡在我們的印象中,是個情詩寫得很好的詩人,是個關心普世價值的詩人,常以睿智悲憫的眼光,點出人生的珍貴和無常。辛波絲卡好像不太喜歡談政治或參與政治,在她的許多朋友加入團結工聯時,她雖然對這運動抱持好感,卻沒有加入。(1)她也不喜歡像許多朋友一樣,「把所有的智慧都花在思考哥穆爾卡昨天說了甚麼,明天吉瑞克會說甚麼上頭(譯註:這兩位都當過波蘭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2)在她的書評專欄中,她也避開政治議題。(3)
可是,很矛盾的,她曾經加入共產黨。她曾經真心信仰共產主義,也寫了一些讚揚共產主義的詩如〈列寧〉,或是悼念史達林的〈這一天〉。後來對共產主義失望,因此選擇退黨。她說,當她不再信仰共產主義,就不再寫這樣的詩了(4)。
在那之後,辛波絲卡就真的沒有在詩中提到、影射政治?活在波蘭人民共和國,政治真的沒有影響到她的生活和創作?其實她還是有寫到政治的。寫於1960年代的〈字彙〉,就是在用一段法國人和波蘭人的對話作為隱喻,談言論審查:
「喔,女士,」我想這麼告訴她:「在我的國家詩人們戴著手套寫作。我不是說他們從來不把它脫下,如果月亮夠暖的話,那是當然。在充滿響亮隆隆聲的段落裡 ── 因為只有那才能穿過狂風的怒吼 ── 他們歌頌海豹牧人簡單的生活。」
——辛波絲卡,〈字彙〉(5)
或者,她也會用色情做隱喻,談論政府對思想自由的箝制:
再也沒有比思想更淫蕩的事了。
在被指定種植雛菊的花圃中,
這嬉戲的行為像是風媒傳粉的野草一樣狂長。
(⋯⋯)
有時某個人會站起來,
站到窗前,
透過窗簾縫隙
偷窺街上的動靜。
——辛波絲卡,〈關於色情〉(6)
甚至在〈寫履歷表〉或是〈考古學〉中,我們都可以隱隱約約看到一個名為國家的機器,在審核、監控、觀看、侵入人民的生活,告訴他們要如何描述自己,告訴他們「有人在幫你書寫你的歷史」:
必須長話短說,遴選事實。
把風景換成地址,
用固定的日期取代搖擺的回億。
(⋯⋯)
誰認識你比你認識誰重要。
旅行只寫出國。
寫你屬於什麼組織,不寫入會動機。
寫你得了什麼獎,略過原因。
——辛波絲卡,〈寫履歷表〉(7)
只要我想這麼做,
(我是否真的想,
你不該知道),
我會看進你沉默的咽喉,
從你的眼窩讀出
你的視野,
並且根據許多小細節提醒你
除了死亡你在人生中還等待過什麼。
(⋯⋯)
給我看你寫的小詩,
而我會告訴你,為什麼
你沒有早一點或晚一點寫下它。
——辛波絲卡,〈考古學〉(8)
但這些詩是在講政治嗎(搞不好它們只是在講寫履歷表和考古啊)?只講政治嗎?說它們是政治詩,會不會侷限了它們?違背了詩人的意志?(當然,在這個作者已死的年代,讀者要怎麼解讀,好像都和作者無關。)
我個人認為,說她很有意識地寫社會詩、政治詩(尤其是那種要熱血改變社會的議題詩),有點過頭。但是她的詩中確實有政治。那是不直接的政治詩,是「可是可不是」的政治詩,是讀者可以創造、互動、參與的政治詩。和〈與石頭交談〉裡面那顆冷冷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石頭相較,辛波絲卡的詩邀請人走進來,你可以在她詩中找到你想要的東西,你可以感覺,可以思考,甚至可以發笑。
幽默,是辛波絲卡詩作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她也常在詩中運用嘲諷手法。比如,在〈恐龍遺骨〉中,她寫道:
親愛的弟兄,
在我們面前聳立的是一個比例不佳的例子:
一具恐龍遺骨——
(⋯⋯)
仁慈的公民,
大自然不會犯錯,但它可能會開點小玩笑:
請注意這顆可笑的頭——
女士先生,
這顆頭無法預見未來,
這就是為何它的主人滅亡了——
可敬的在場與會者,
牠的腦容量太小,食量太大,
愚蠢的睡眠多過明智的恐懼——
——辛波絲卡,〈恐龍遺骨〉(9)
表面上看似在講恐龍,但其實辛波絲卡在諷刺共產官僚政權(這件事台灣作家宋澤萊也有講過(10))。「親愛的弟兄」、「仁慈的公民」、「可敬的在場與會者」這些都是波蘭共產政權常用的官僚語言,明眼人一看就懂。辛波絲卡的詩有點像秘密集會,講了通關密語,讀者就可進入房內,心領神會。透過把這些陳腔濫調的語言弄得好笑、荒謬,辛波絲卡也進行了一種對政府意識形態和僵化語言的顛覆。
「在詩人那兒,字想起了它們本質的意義,像花一樣綻放,自由又隨興地根據自己的法則發展,奪回了它們的完整性。」(11)波蘭小說家布魯諾.舒茲(《鱷魚街》的作者)是這樣談詩的。雖然他是另一個時代的人,他談到的語言的僵化平庸,也不是辛波絲卡那個時代的語言的僵化平庸(辛波絲卡時代語言的僵化平庸是共產主義造成的),但在辛波絲卡的時代,這準則依然適用。
這當然不是直接的反抗,無法造成什麼立竿見影的政治上的改變,但卻是個人可以做的,保有心靈自由的一種瑜珈(而且是空中瑜伽)。個人主義,在一個倡導集體思考、集體行動的社會,是多麼難得又珍貴。
(1)安娜.碧孔特、尤安娜.什切斯納著,林蔚昀譯,《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台北:臉譜出版,2023)。頁363。
(2)《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頁197。
(3)《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頁211。
(4)《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頁156。
(5)辛波絲卡著,林蔚昀譯,《黑色的歌》(台北:聯合文學,2016),頁104。
(6)《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頁374-375。
(7)《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頁23-24。
(8)出自辛波絲卡詩集《橋上的人們》(Ludzie na moście),頁9-10,此段為林蔚昀翻譯。
(9)出自辛波絲卡詩集《萬一》(Wszelki wypadek),頁23,此段為林蔚昀翻譯。
(10)宋澤萊,〈辛波絲卡不寫政治詩?〉,《台文戰線聯盟》,2010.03.05。https://twnelclub.ning.com/m/blogpost?id=3917868%3ABlogPost%3A3232(2023.06.08)
(11)布魯諾.舒茲著,林蔚昀譯,〈現實的神話/化〉,《鱷魚街》(台北:聯合文學,2012),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