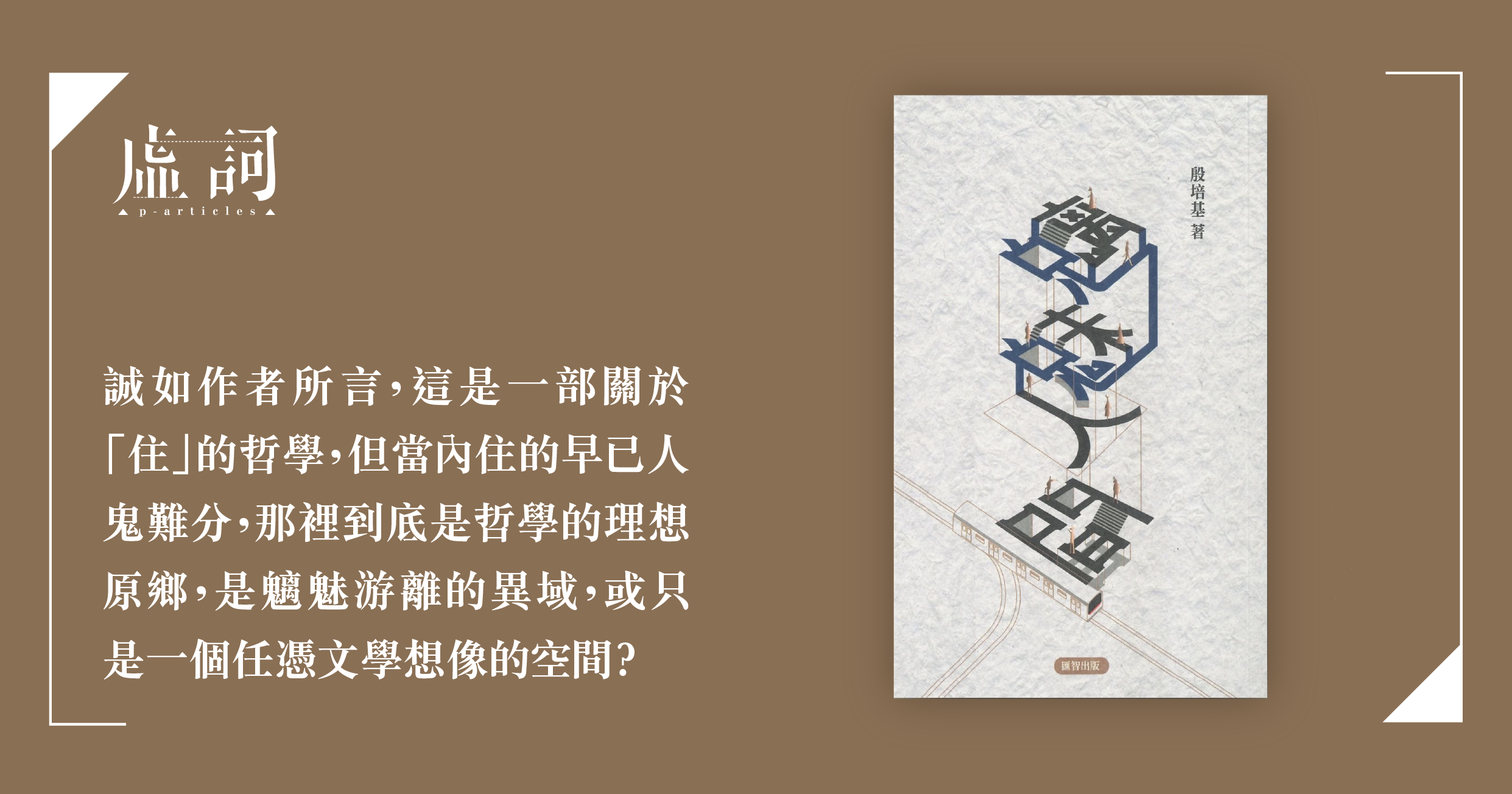住即不住,不住即住——論《魑魅人間》的異化觀
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
——庾信,《哀江南賦》
庾信(513-581)寫《哀江南賦》,以「奔魑走魅」寫北朝侯景叛梁武帝蕭衍,釀成「侯景之亂」,終致蕭衍餓死宮城。「魑魅」原為草澤妖怪之名,杜甫《天末懷李白》云:「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文人每以山川精怪喻小人,魯迅嘗言六朝文人之作,雖非有意為小說,卻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實有,故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1)每借鬼怪之說而言作者之志。至唐傳奇,雖不離搜奇玄幻,但已從作意好奇的幻設,而「假小說以寄筆端」,更是以鬼魅之說談人間事。明代神魔小說盛行,同是世情小說興旺之時。魯迅論其原因,離不開當時的社會狀態各人心中的向背。(2)清初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更是「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這種借鬼神之名道人間冷暖的情況在五四時出現逆轉,其中以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的胡適為「打鬼」的佼佼者。他一方面提出整理國故,疏理過去傳統以迎接西方文化;同時又自膺「捉妖打鬼」悍將,以民主和科學為工具,志在古紙堆裡抓那些毒害國民精神的吃人老鬼。周作人比他兄長更激進,他高喊〈無鬼論〉,認為古老的中國早成鬼域。五四後中國在世界舞台屢遭屈辱,對外欲爭國權,對內望除國賊,但每次總鎩羽而歸。人民對由西方列強帶來的民主與科學既愛又恨,慢慢轉投馬克思的共產理想。從國共內戰到新中國成立,馬克思的幽靈代替了歷朝的魑魅,至今仍縈繞不散。
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擷取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異化理論,他所論及的異化(Alienation),從人對社會失去歸屬感的「隔閡」(Separation)以致形成對立。馬克思把黑格爾的絕對唯心論顛倒,他專從資本社會中的工人勞動與生產品的異化說起,抽離當中的精神和心理論述,把人的價值與產品的生產掛鉤,強調勞動愈多,愈加大內在勞動力的異化。加上資本家推波助瀾,造成人與出產、甚至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跟自身發生異化。這種異化是強制性的,把人變成非人,物化人成為人獸鬼難分的存在物,要改變這情況,低層階級必需對上層階級進行革命鬥爭,並摒棄過去一切壓制人民的封建思想。四十年代延安有名的《白毛女》就曾稱「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在紅色革命的年代,白毛女的呼聲無疑是對過去國民黨腐敗的證言,也是對新中國政權的正當合法性作正名。廿多年後,文化大革命來臨,先前處身於新社會的進步人士被陸續打成牛鬼蛇神,歷史見證人鬼間的異化並非如馬克思所言絕對地二分。
王德威在〈魂兮歸來〉一文中提出「書寫即招魂」,以余華〈古典愛情〉(1988)的一場人鬼戀書寫為引子,形容余華以殘暴改寫傳統,再以海峽對岸的韓少功和朱天文談鬼之言歸(〈歸去來〉)與無處可歸(〈古都〉)表達人的無處安身。王德威認為在一眾華人作家中真正談到「寫作即招魂」意涵的,當數書寫九七回歸的香港作家。其中有搬演鬼事的李碧華(《胭脂扣》、《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以一個死人在回歸週年留給我們一席鬼話的陳冠中(《什麼都沒有發生》),當然少不了常把張愛玲筆下人物借屍還魂的黃碧雲,他們都耽溺暴力,玩弄施虐與受虐想像。(3)這批書寫回歸,為死者招魂的文人,跟馬克思在過去留下對人異化的論述,竟在這資本氣息濃烈的城市無縫接軌。千禧至今已過廿多年,科技的爆炸理應結束魑魅魍魎的迷信,但城市裡的異化,卻仍年年月月地在如影隨形依附人心。殷培基的《魑魅人間》,接上馬克思的黃水晶菱鏡,反映母城的前世今生,折射出人的異化,見證著人鬼之難分。
開篇〈一宗生意的抉擇〉以身體器官象徵資本主義城市內的醉生夢死。被形容如便秘的高速公路,一到繁忙時間頓成栓塞的血管、中風的經絡,煩囂的城市彷如定格,「發達的光景和美好的前途,互相堆疊成一幅美麗的城市圖畫」,但外表的風光掩蓋不了內部的積疾:「我城的樓宇只得框架般的輪廓」。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我」毫無顧忌指出「賣人賣己是我純粹的想法」,布希亞所批評的商品拜物,把人矮化成商品,正是馬克思理論的幽浮在現代都市具體呈現。殷培基書寫都市人不止甘於異化成物,更要異化成魑魅的怪獸。 「我」的同事劉仔,在燈紅酒綠的鏡像映照下,「張開血盆巨口,噬咬鏡中的我」。那時劉仔終於完全現出真身,「顯露鱷魚和蟒蛇的原形」(4),是人、非人?馬克思以物質與階級間的動物性衝突代替人的心性與精神,但人畢竟是追求自由的,〈變鳥〉正是被迫異化的人尋求解脫的故事。只是我城早成樊籠,「我」唯一可以做的,只有離開現實,逃入夢境;但現實早已脫離想像,我唯有再次進行自我異化,成為鳥,飛向遠方,當然,現實最終只會是斷骨殘羽而歸。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獨立自由精神,卻跟牛鬼蛇神的幽靈再次弔詭地重疊。
殷培基對未來的想像同時闡釋了城市內人與人之間異化。在〈末日謊城的浮靈自白〉裡他以先知式口吻說出:「末日異境,破落死城,黑海重生,浮靈巨變。」科幻式的想像兩座城市互換,出現碎裂、重組和重疊的不規則空域異變,那些在末日戰後留下來的人被迫轉生,成為人們口中的陰魂,不住噬咬當前的現實。永無休止的革命令人只能單顧眼前身,不理身後事。〈一級榮譽畢業〉把故事人物置身在極權統治下的「自民區」,時間在無情的過去和幽暗的未來間擺動,「已經過第幾次世界大戰了?地球給我們毀滅多少次?」倖存者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只能為巨人圍牆內的一級榮譽而努力。從末日回到當下,〈放逐〉彷彿回到普羅大眾所熟悉的殷培基——那位寫熱血少年在籃球場上馳騁爆籃,渾灑青春汗水的青少年文學作家。〈放逐〉表面是個堅持理想的勵志故事,但魑魅人間那容得下半點陽光?故事發生在被戲稱為「蒸籠」的古老體育館,因年代久遠而常有鬧鬼傳聞。現實是體育館因日久失修,昔日的光芒早被嶄新的場館所替代,但人總愛聽都市傳說,任憑校園被籠罩在一片陰森的霧中,「霧裡會傳來拍球的聲響,和男人們遭受極刑的嚎叫」。唯有這樣,人才會念舊。〈電話錄音殺人事件〉中可怕的鬼爪正是來自人心中的夢魘,那隻黑色的鬼爪,伸長了如鈎的指甲,不住以殺人為樂。殷培基以推理小說的格局,書寫自身的異化:「神秘的黑色爪影再次出現,撕毀她的靈魂。她彷彿看見一個男人坐在一旁,欣賞她的痛苦表情,沒有伸出援手」,「定格了的他猶如看見蛇髮女妖曼杜莎的妖瞳,步向石化。」曼杜莎的醜陋和邪惡源自偷情的咒詛,而凶手七次伸出如鬼魅黑暗般的魔爪傷害無辜,同樣來自於妻子的背叛,她讓「家不成家,只是一個空間,一份徹底無力感」。馬克思從人的異化到在家庭中的異化,擴充至人在資本社會下的異化,唯有打破既有的家庭、社會觀念,動員全世界的工人革命,烏托邦才會來臨。歷史見證著曼杜莎的異化悲劇,卻讓被她眼光觸及的世人,動彈不得。
書寫一直正向的殷培基,回到他熟悉的黑暗現實,也漸走上迷途。〈那天,我在港鐵站迷路了〉的DSE考生,以三分的公開試成績論證以分數量化人的價值何其荒謬,偏偏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就是以人的出產為量化值。以考試的高低判斷、標籤人能否成為一顆有用或無用的螺絲釘,然後投入量產。在整座城市的生產流程下,成年人看到的只是成績和利潤,再化約成一連串的數字,一些較清醒的人或許「看見了不是真實存在的哲語背後的夢魘」,但魑魅早已依附在整個體系。從工人的異化,到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異化,擴充至人與其種性(Specis)的整體異化,每雙狂人的眼睛都成非人,最終又回到自我的異化(Self-alienation)上。〈貪生〉是整部《魑魅人間》的總歸,結構最複雜。主角定焦在母城的幾個日子,不住的重新出發,在那個看似選擇卻又無從選擇的第二、第三多重人生不斷過渡。這裡有貼近現實的世紀瘟疫和政治跌盪,也有種子飄零奔走異鄉的移民想像,是作者再次以母城的根、為方向、為中心的人生輪迴。整部《魑魅人間》都在書寫人在異化中苟延殘喘,而馬克思的幽靈也在不住的敵我矛盾階級鬥爭中夢想那世界大同,那張在歷史長河裡出現了裂紋的菱鏡,為一眾牛鬼蛇神伴以佛謁般超渡:「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誠如作者所言,這是一部關於「住」的哲學,但當內住的早已人鬼難分,那裡到底是哲學的理想原鄉,是魑魅游離的異域,或只是一個任憑文學想像的空間?
這是一首永難唱好的安魂曲。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頁44。
(2)同在,頁343。
(3)王德威,《歷史與怪獸》(台北,麥田出版,2004年),頁227-242。
(4)殷培基,《魑魅人間》(香港,匯智出版社,2022年),頁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