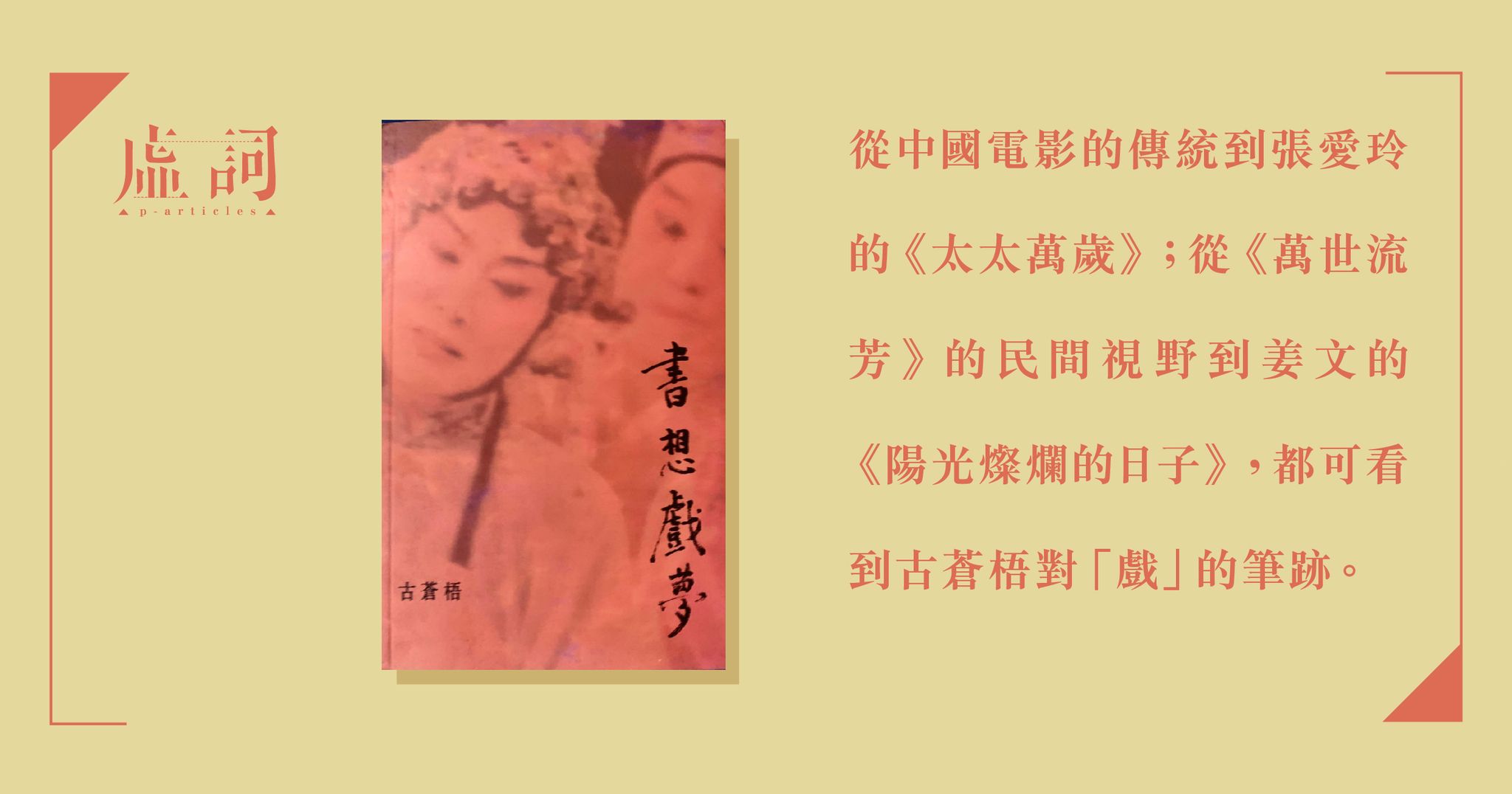讀古蒼梧的《書想戲夢》
「其西風吹無蹤! 人去難逢,需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裡別是一般疼痛。」
——《牡丹亭.鬧殤》
踏入2022年初,驚聞噩耗,作家古兆申先生(古蒼梧)被好友發現在家中離世,享年76歲。從《中國學生周報》發表的第一首詩,筆耕於《素葉》、《文學與美術》、《羅盤》等文學雜誌多年。看到媒體對他冷漠的零星報導,在重讀他的文集《書想戲夢》,頓時百般滋味在心頭。
古蒼梧一生醉心崑曲,尤愛《牡丹亭》。崑曲為最古老的傳統戲曲劇種之一,明代稱南戲為《傳奇》,兼收雜劇音樂,改名「崑曲」。《書想戲夢》中「戲」的部分主要談崑曲。王思任在《批點玉茗堂牡丹亭敘》中,以仙、佛、俠、情作為「臨川四夢」的鑰字。能以隻言點出戲曲神髓固然精彩,但曲目在後世是否能被接受還需倚賴受眾的鑑賞力和評論家的解讀分析。其中〈期待這樣的一齣《牡丹亭》〉一文點出傳字輩藝人從清末崑劇老伶承傳的十三部折子戲等細節,由此表達作者盼望在現當代舞台演出一個完整的《牡丹亭》本子(註1)。《書想戲夢》成書於1998年,2000年古蒼梧助江京崑藝術劇院改編《牡丹亭》,2004年更為青春版《牡丹亭》擔任顧問,算是還了多年夙願。
談戲曲,不能不提程硯秋與梅蘭芳。〈談程派唱腔〉和多篇以梅蘭芳莫斯科座談會評論,是「戲」中較學術的部分。文中對程派的藝術上的達情與韻味,或是技巧上的演唱、就字、以至程派特有的臚腔共鳴,都有傳神的表達; 而關於多篇梅蘭芳莫斯科座談會的評論,更援多位國外劇評人的理論,如英國戲劇家戈登克雷的「傀儡象徵性表演」和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間離化」理論,他們反對演員對角色的感情控制,要求演員站在角色以外去表現角色的多面性(註2)。
除了戲曲,古蒼梧還愛電影,「戲」的部分夾雜多篇影評。從中國電影的傳統到張愛玲的《太太萬歲》;從《萬世流芳》的民間視野到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都可看到古蒼梧對「戲」的筆跡。改篇自王朔的當代文學《動物兇猛》,古蒼梧沒有依從當時流行的痞子文學或開放後的文化商業點切入,卻以姜文早期主演的《大太監李蓮英》比對《陽光燦爛的日子》。電影主角馬小軍面對米蘭的挺胸裸露時的無能、無力,只懂喊「有勁」,猶如閹奴李蓮英(《大太監李蓮英》的原名) 裡的洞房情節。封建權力下的男性固然被無情地閹割,文革後的青年們在一堆傷痕文學中所流露出對政治的自我去勢和頹廢冷感,兩者形成既無形的對立,卻又荒謬的依附。《動物兇猛》發表於1991年《收穫》第6期,古蒼梧的評論既表現對改革開放後的文化走向表示擔憂,同時對89後群眾只知其喜不知其悲的金錢至上現象感到無奈。以《陽光燦爛的日子》比對《大太監李蓮英》,正是對現實的一種自嘲與反諷。
無論是崑曲的傳統藝術,或是後文革中心從政治轉向市場經濟,固有價值正不斷被資本主義的浪潮衝擊。知識型的經濟漸漸代替6、70年代的香港以勞動力為主的輕工業市場,用李歐塔的話,「在這種普遍的變化中,知識的性質不會依然如故。知識只有被轉譯為資訊量才能進入新的渠道,成為可操作的。一切被構成的知識,如果不能被這樣轉譯,就會遭到遺棄,新的研究方向將服從潛在成果轉變成機器語言所需要的可轉譯性條件。……隨著資訊科技的霸權,某種邏輯佔了上風,由此生出一整套的規範……從此我們可以見到明顯的知識外在化。(註3)」知識不斷地變化,不合用的舊知識轉眼就被遺棄,被遺忘。古蒼梧的仙逝,在媒體裡外的寂靜,或許正說明了工具性的知識跟真善美等永恆價值難以協調。唸著他的無題詩,以為祭文。
無題
燈燼後
桌、椅、鏡、床、人
都消失了
我們卻以手捏黑暗
重塑
彼此的形象
再以唇
慢慢的燒、鍛鍊
那一刻
我們都相信:
到天明時
我們便會變成
一座連體的銅像
裸體在大地上
千年萬年
接受八方的風、霜、雨、雪......(註4)
他曾說:「我對人生雖無希冀,卻多依戀: 夢耶? 影耶? 夢中之事何其幽深,影中之象何其繽紛! 素喜詩文、書畫、電影、戲曲,目迷五色,耳亂五音,沈醉不能自拔……歲月飄忽,不覺年過半百。世途崎嶇,然亦無大憾。若他生得如此生,則不辭輪迴也。故前塵舊跡,以待來世。遂有一『夢』輯,與『書』、『想』、『戲』並存。(註5)」
別矣,詩人、作家、伶人、哲人。
註:
1. 古蒼梧:《書想戲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33-134。
2. 古蒼梧:《書想戲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33-134。
3. 李歐塔(Jean Francois Lyotard)著,車槿山譯:《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34-36。
4. 鄭樹森、楊牧篇:《現代中國詩選II》(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3年),頁710-711。
5. 古蒼梧:《書想戲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