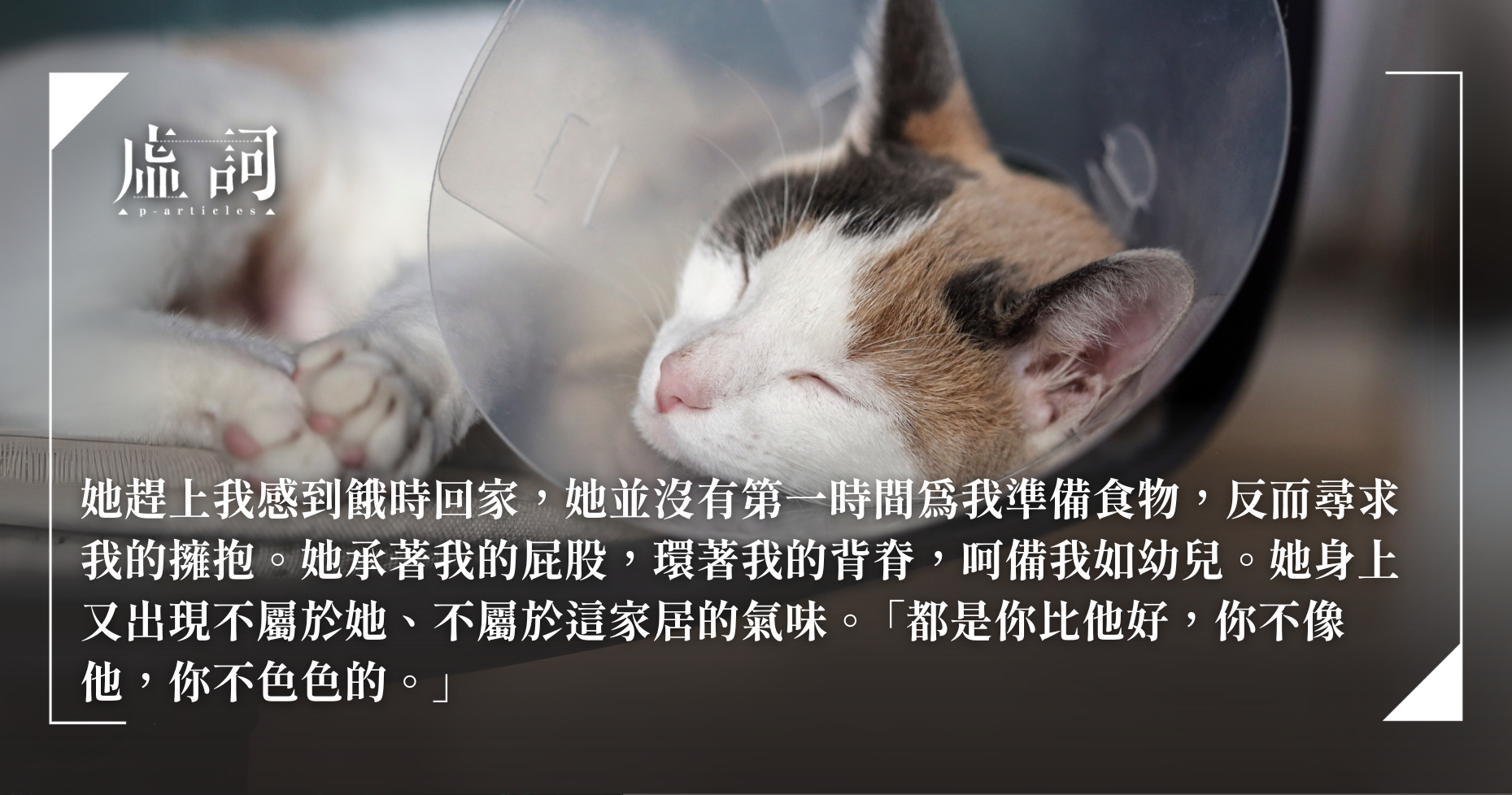後超人時代
黃戈傳來以「超人」為題的散文。他指出《超人迪加》作為他的童年回憶,有著無可磨滅的地位,每集都有特定主題,但其描寫的神性與人性,是整部劇的關鍵思辨,甚至挖掘出克蘇魯神話的暗影。黃戈藉由回憶該劇的經歷,探討懷舊情感、人性與神性的交織、文化版本的差異、成長過程中對童年記憶的重新解讀,以及他對自我身份的反思。 (閱讀更多)
雞蛋
周丹楓傳來以純粵語書寫的小說,書寫Tracy陷入了對幸福的迷思。她與男友Peter的關係看似穩定,卻因平淡而令人窒息。若希望對抗孤獨,便需模仿明星、網紅及身邊富有的朋友好讓自己融入社會中,且需令自己變得脆弱,才能成為某群體的一份子,獲得認同感。我們活在一個「它的自我世界入面,呢度得一個世界,所有事都以這個世界為標準,其他全部都可以係錯或者假 。」 (閱讀更多)
詩三首:〈慣性〉、〈鵝之悲歌〉、〈這一邊和那一邊〉
詩歌 | by 丘亦斐, 王培智, 侯蔽 | 2025-04-04
讀詩三首。丘亦斐傳來詩作〈慣性〉,以「一棵走失的樹」為主體,探討生命的迷失與無常,並將其置於時間與宗教的框架之中,質疑神聖與人性之間的關係;王培智的〈鵝之悲歌〉以口語撰寫深井燒鵝的前世今生,以幽默諷刺的形式憾嘆香港文化身份失落的現象;侯蔽詩作〈這一邊和那一邊〉通過細膩的情感描寫和豐富的意象,提醒人們應理解人際關係的複雜性、接受愛情的雙面性,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在反思中追求成長。 (閱讀更多)
廢話文學
潘逸賢以「廢話」為題傳來散文一篇,透過重沓、喋喋不休的文筆講述一個「廢話」連篇的故事。透過故事、事件、時間與目的的剖析,反映了人類在生活與創作中尋找意義的過程。然而,潘逸賢認為很多人終其一生只是漫無目的的故事,映射出生命本就如同廢話那樣荒誕。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