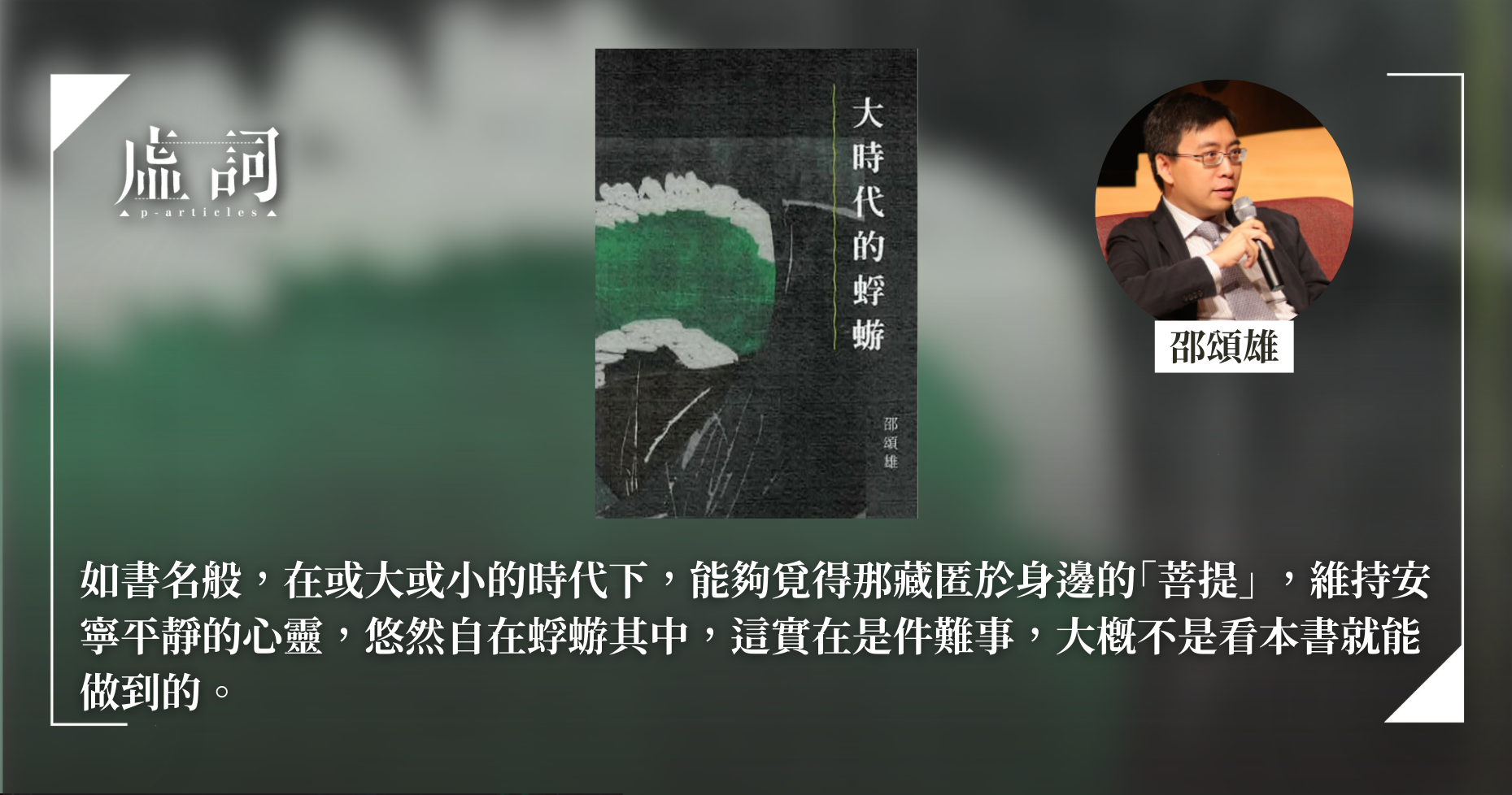菩提在世間
書評 | by 亞C | 2025-08-26
總有某些書,即使一直心心念念,但依然難遇不可求,比如黃碧雲的著作,縱使為其文字著迷不已,但對於她的大部分著作而言,能擁有一本紙質實體書實在是件十分困難的事。而當初見山為邵頌雄先生出版的《大時代的蜉蝣》,雖不至如《無愛紀》,《後殖民志》般稀有,但後知後覺地在這本書出版了一段時間之後,無論是執笠前夕的見山書店,或是其他獨立書店都未能覓到。
幸而在颶風與不可抗力到來前,在文學館散書祭的「豬肉枱」上,竟然發現到這本「愛而不得」的書,實在難掩興奮果斷買下。這是大型書展所不能擁有的樂趣。
認識並喜歡閱讀邵教授的文章源於他在《明報》的專欄,尤其是那些深入淺出地介紹剖析各種佛學理念的文字,用郭梓祺序言中所寫「每次讀邵頌雄寫佛學也如清泉」,而這也是想閱讀這本《大時代的蜉蝣》(下簡稱《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重要原因,便如書中的序言部分所提及的,收錄的文章不少都是出於已經消失的媒體,曾存在於網絡上的,現今都淪為雪泥鴻爪,已再不能尋。
當下被視為老舊落後的實體書籍,有時比起先進科技,反倒是更好留存紀錄的載具。
而在《大》裏不少文章都書寫著過去,無論是老師,親友,或是關於這座城市的文化與記憶,甚至包括那條常在童年回憶中閃現,不同於Peaches and Cream那黃白互間的品種,而是帶有「不知人間何世的滿足感」的黃粟米(〈憶黃粟米〉),即使現今超市大多已無法覓得此品種,唯有透過文字隔靴搔癢都算不上地領略並惋惜一番。
而最期待的講述佛學部分的文章,每篇讀來都只覺當初對這本書的朝思暮想以及找到時難掩的興奮實在並不虛妄。尤其是那篇〈佛家的斷證二事〉,當中拋出何所應斷,何者該證,列舉「執著」與「空性」為例,實在是十分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深信「萬物無自性」,「一切皆空」的同時,如何看待對社會上並非應然之事;對於是非善惡對錯之辨別堅持,是否是阻撓心寧,是修行上的絆腳石,兩者之間又是否並非必然矛盾,而是可共存相生的?
「唯若對固有成見堅持,連客觀的思考空間也不予開放,如此的封閉心靈,才真的是對『空性』毫無感悟的牢固執著。」
這是邵教授文末處的總結。
除此之外對於時興的「放生」,「齋戒」或是「佛誕浴佛」等行為,《大》之中也一語中的地將這些與佛教相關行為的原初本義闡述一番,而與普羅大眾們當下如何前仆後繼踐行上述行為作一對比,實在是解釋「大相徑庭」詞義的最佳實例。
不過書中真正論及佛學的文章似乎並不多,但真正細讀領會過後會發現,其實是很多的。
佛學蘊含的智慧大概並非只可一本正經探討解釋著別具深意,看來晦澀的名詞,背下「一花開五葉」各自的名字與差異,緊記經文或各單流傳的公案,正如六祖慧能所言:「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真正的智慧並非束之高閣,遙不可及的,就如在這本《大》之中的不少看似生活瑣事的記錄書寫裏,其實也隱含著不少值得思考領會的「禪意」。
比如常聽到的「飲飲食食」,不止是網上foodie推薦的某處「抵食夾大件」,如何潛心靜氣透過一萬小時的錘鍊,「以意境先行,然後不斷審度製作與意境之間的距離,廚藝上造成的偏差,針對不足之處加以改良改進」(〈下廚一萬小時〉),這看似玄妙且艱辛,但正如百年前周作人曾著文講述在北京十年都未曾吃過好的點心,作此抱怨並非出於「傷害民族感情」,而是生活總需某些「無用的遊戲與享樂」。耗費心力自己一手一腳煮食,不止是滿足口腹之慾,也可是種無用但必需的遊戲與享樂,亦是一種學習。即使一碟常見的「威靈頓牛扒」,無論傳統框架或是具個人特色的創新,其中也可大有學問(〈「威靈頓牛扒」述異〉)。前段時間大熱的韓國節目《黑白大廚》裏最引人注目的Edward LI,令人折服的不止是烹飪知識與技術之廣闊和高超,用豆腐這不變的食材可製作出各種各樣不同的菜餚,還有的便是那個人的修養,烹飪製作每一菜式所帶有的別具匠心的意念與意境。即使將節目製作編排,場景裝潢完封不動複製照搬,依樣畫出個一模一樣的葫蘆,裏面也賣不出那味最具價值的藥。
又比如家中物品的執拾整理,或是扭計骰這一小小的童年玩物,當中其實也有值得領悟的哲思藏身其中。幫前輩或親友整理雜物時會醒悟「捨離偏執,需要智慧,也需勇氣。」(〈囤積與收藏〉),而洞悉扭計骰不止需明瞭六面中心顏色永遠不變的這一「破陣罩門」,更重要的是從中懂得「於紛紜萬象中領悟恆常不變的道理,從來都是東西哲學中的重要一環,惘然迷失與廓然開悟的分野,正是建基於能否洞悉變幻中的永恆。」(〈扭計骰的迷思〉)身邊常發生的平常事,再普通不過的小玩意,原來也蘊藏著如斯道理。
除此之外,《大》之中還談到了命書術數。這些似乎並非佛教產物,不過大眾高舉香燭,倒頭便拜時,其實大多也並無考究面前是哪一派別,即使走進佛殿,面對佛像焚香祝禱,口中念念有詞的亦是姻緣財富,事業生育等等「顛倒夢想」,與求籤算命也許並無二致。關於「詭祕難測」的命理,邵先生引用了馮晞乾先生所言「解讀一個星盤,好比賞析一首命運的詩」,「如此而已」(〈也談命書〉);而關於術數的總結便是「難學易精」,邵先生眼中看來,所謂精妙高深的術數,其中內涵也並非那麼廣博無垠,潛心學習一番後精通此學並非難事。但對於現在有名或無名,自稱精通的術數大師們對於歷史文化,又甚基本的中文文言之造詣理解,恐怕有如信徒們對自身前程般,不禁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而真正可臻於術數,能被看作「學成」,便需如文中所寫:「若能通過算命而對人生有所感悟,且『入乎其內而出乎其外』般從刻板的技法超脫出來,揮灑自如地啟發問者,或助其作出進退取捨的指導,於術數一門可謂始登殿堂;更能有『善算者不易』的心胸,學懂術數而忘記術數,逍遙而遊,那才是大宗師的境界。」
另外一位常被視作散文寫作「大宗師」的董橋先生曾在文章〈那些年我見過不少哈代〉(收錄於《絕色》)裏寫過:「橫豎平日賣文賣的只是心中逝水,腹中的墨水,過份依賴資料,通篇反而變成御花園那般整潔,喪失野趣,喪失閒趣,喪失那份荒蕪的慵媚和瑣碎的悠遊,徒嫌堆砌,也嫌正經」。
邵先生與董先生文章的風格特色當然並不相同,但同樣地,即使兩人所寫文章常旁徵博引,有著大量的資料學問,但毫無賣弄堆砌之感,全屬個人那「心中逝水」和「腹中墨水」,那積累練就的人文修養自然流出寫成。雖在《大》之中並未收錄,邵教授曾在專欄中介紹「藝術歌曲」中的「繪詞法」的手法,列舉舒伯特《冬之旅》組曲(Winterreise)中第一首《晚安》(Gute Nacht)為例,並以此賞析林家謙的〈普渡眾生〉這首不少人常聽的流行歌曲當中編曲創作時蘊藏的匠心與巧思。而在《大》之中也有著不少文章寫著流行曲,電影,書籍或某些串流平台上播放的劇集,但讀來並不覺是一般意義上的影評或書評,又或並非單一地論述某一兩部電視劇作,而是由其引起對於藝術,人生,社會的思考,前者與大眾日常極之接近,但後者卻遠非Netflix般普及。
如書名般,在或大或小的時代下,能夠覓得那藏匿於身邊的「菩提」,維持安寧平靜的心靈,悠然自在蜉蝣其中,這實在是件難事,大概不是看本書就能做到的。
畢竟,知道,領會,與做到,大概是三個境界。但能有所了解,知道多點,有所啟迪,領會多些,與「做到」距離靠近多點,或者已是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