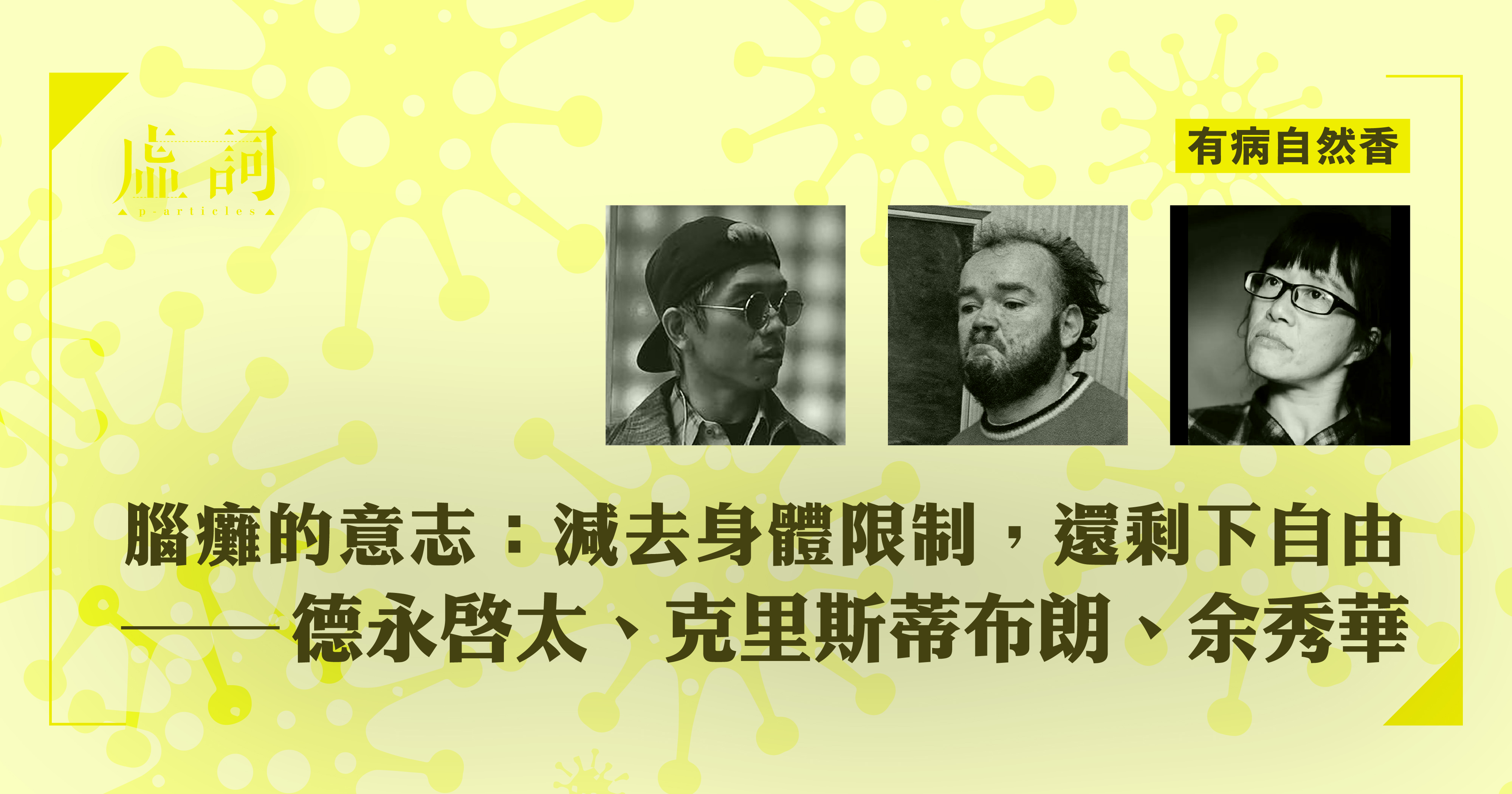【有病自然香】腦癱的意志:減去身體限制,還剩下自由——德永啓太、克里斯蒂布朗、余秀華
腦癱,是Cerebral Palsy的字面直譯,但譯法正確,解讀起來卻讓患者常被誤會。腦癱不是真的指大腦癱瘓,而是因為腦神經受損,導致患者無法控制身體肌肉。所以,癱的往往只是四肢,感官亦可能會喪失,頭腦卻仍然是清晰、健全和自由的。腦癱無疑限制了身體活動能力,但還是有穿過大半生都不認命,用意志活下去的音樂家、作家和詩人。
德永啓太:輪椅上的DJ
疫情禍連東京奧運,國際體壇盛事本來黯淡,但今屆港隊爭氣,坊間反應較往年熱情,就連緊隨奧運舉行、過去常被普羅大眾忽視的殘奧,都同樣成為焦點。日本主辦方固然極其重視奧運場館與宣傳品的設計,其實殘奧亦不馬虎。今屆殘奧以「We Have Wings」為主題,開幕禮上便安排了數十位健全和殘障舞蹈員同場表演,帶出傷健共融的社會願景。更細心的是,於當日主理現場音樂,負責帶動氣氛的DJ德永啓太,本身亦是患有先天性大腦麻痺殘障人士。
先天性大腦麻痺,即所謂腦癱,意味著德永啓太從小便無法像常人自由活動,需要長期與輪椅為伴。不過,德永啓太不甘被標籤為社會弱勢,他依然對音樂、寫作、時裝、潮流等方面興趣濃厚,亦成為他表達人生自由的場域。近年德永啓太在東京積極參與音樂表演,於各大時裝雜誌撰寫專欄,還建立了自家設計品牌。雖然自稱是一位「輪椅上的DJ」,但他並不自卑,反而因為敢於表現自我,無懼世人目光,開始在潮流界得到巨大迴響。

德永啓太就在2018年被《Vogue》選為「World 100 Street Style」其中一員,並邀他接受專訪,談及他以潮人身份推動的平權風氣。《Vogue》形容,作為一名先天性腦癱的藝術家,其惹人注目的特異衣著及其知名度,不但有效消除日本人對腦癱患者的刻板印象。與此同時,社會對殘障人士普遍不太友善,而德永啓太積極打進年輕人主流,嘗試介入流行文化,亦鼓勵了更多以殘障人士出發、顧及邊緣弱勢實際需求的設計。
克里斯蒂布朗:還有左腳就能寫作
且說今屆東京殘奧,另有一難忘賽事。於S1級別(最嚴重殘障)的100米背泳比賽,來自白羅斯的選手Aliaksei Talai雖是最後一名衝線,卻贏得全場掌聲。因為他是在失去雙腳、右臂和左前臂的情況下,單靠半截左臂游到終點。Aliaksei Talai因為小時候一場嚴重意外而終身傷殘,但他未有放棄自己,多年後成為殘奧賽事上得以留名的國際泳手。
而這個「半隻左手」的勵志事跡,教人想起許多年前,愛爾蘭作家克里斯蒂布朗(Christy Brown)筆下的一部自傳小說《我的左腳》(My Left Foot)。跟Aliaksei Talai不同,克里斯蒂剛出生便證實腦癱,先天性頑疾導致其大腦神經嚴重受損,無法自由控制肌肉,因此手腳軟弱無力,甚至不能支撐身體,更不能開口說話。雖則四肢及感官健全,但自出娘胎就跟完全癱瘓沒太大分別。五歲之前,克里斯蒂都不曾說話,頭部、身體四肢亦不能活動,連父母都幾乎絕望,認定克里斯蒂只是一個活死人,將在痛苦中默默度過餘生。直到有一日,躺在床上的克里斯蒂用左腳腳趾將妹妹不小心丟下的顏色筆夾起來,開始在牆上塗鴉,母親見狀既驚且喜,因為克里斯蒂證明了自己至少還有左腳可以自由活動,不是完全殘廢。於是母親開始教他認字、學習用腳寫字,他亦同時投放了大量時間來讀書。
克里斯蒂長大之後,逐漸恢復說話能力,並且從簡短的閱讀筆記開始,決心走上寫作之路。雖然只有左腳腳趾能活動,但母親當時為他買了一台打字機,讓他可以練習用腳打字。從此,克里斯蒂一邊用打字機寫作,另一邊則以腳趾夾著畫筆繪畫。

就在1954年,克里斯蒂22歲,第一部自傳體小說《我的左腳》正式出版。隨著小說面世,特殊身世及其以左腳寫作的事跡,震驚了國際文壇,作品後來翻譯成多種語言,高據各地暢銷小說榜。克里斯蒂成為知名作家兼畫家,繼續默默創作,至48歲逝世時,已先後出版過好幾部自傳小說及詩集,亦成為愛爾蘭其中一位家傳戶曉的傳奇作家。
克里斯蒂去世之後,愛爾蘭導演Jim Sheridan在1989年將《我的左腳》改編成傳記電影,並由當時的荷里活新人王Daniel Day-Lewis主演。《我的左腳》大熱橫掃奧斯卡金像獎,Daniel Day-Lewis憑此角色獲得從影生涯第一個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座,而戲中飾演克里斯蒂母親的Brenda Fricker,同屆亦贏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左腳作家」克里斯蒂的故事,亦因為電影於票房和口碑的巨大成功,得以真正流傳開去。
世人常開玩笑,形容不用腦寫作的人,就是用腳「躺著也能寫」,對於真的躺著用腳寫作的克里斯蒂來說,這自然不太好笑,而「躺著也能寫」不是一件簡單的事。Daniel Day-Lewis曾感慨表示,克里斯蒂這個角色是非常難演的,難在他本人實在無法像克里斯蒂那麼熟練地運用自己的左腳來打字寫作,即使只是拍電影,戲中的大部分情節,他其實要對著鏡子反覆練習無數遍才成功。由此可知,現實中先天殘疾的克里斯蒂,終其一生更是承受著旁人無從體會的艱苦。

余秀華:穿越大半個中國文壇的蕩婦體
克服身體殘障,以創作對抗命運,諸如克里斯蒂布朗的逆流人生,通常都會被後世廣泛傳頌成勵志故事。然而,在中國詩人余秀華身上,卻是絕對不可能發生。就如今日被標籤為「蕩婦體」代表作家的她所言:「勵志個屁啊,是二十年的苦難婚姻把我逼上絕路。」
余秀華生於1976年,湖北省鍾祥石牌鎮橫店村人。余秀華天生壞命,剛出生時因為倒產而腦部缺氧,失救導致腦癱,由於父母是窮困農戶,只能放棄治療,余秀華從小就行動不便,六歲才學會走路,但說話仍然口齒不清,學歷只有中學程度,畢業之後便一直待在家裡。
腦癱、窮困、不善辭令,讓余秀華裡裡外外都深感自卑。而在傳統的農村社會,余秀華更被家人視為無用的負累。因此,就在余秀華十九歲的時候,不想她繼續賴在家裡的父母,便草率為她定了一門盲婚,男方是比她大十二歲的農民尹世平。
余秀華當然明白尹世平從來不愛自己,她只是沒人要的殘廢,所以才會被迫許配給一名找不到娶妻對象,沒有選擇餘地的農夫。夫婦相處並不愉快,但余秀華父母認為,有丈夫外出賺錢補貼,至少她不用餓死。而余秀華在百般不情願之下,還是生了孩子,表面上維持著和諧的婚姻和家庭。但其實整整二十年裡面,兩夫妻聚少離多,尹世平一直出外打工,每年只會回來幾次,見面時再無感情。
其實余秀華曾多次提出離婚,但尹世平礙於面子一直拒絕,絕望的婚姻狀態便從此困住了余秀華。為填補對婚姻的不滿、對丈夫的怨恨、對生而殘廢的無奈,以及打發掉日復一日的枯燥生活,余秀華寄情於閱讀、寫詩。丈夫當然對此毫無興趣,當余秀華開始寫作時,他不但鄙視,更認為妻子只是不事生產浪費時間。
所以,在余秀華那首〈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紅遍中國網絡世界之前,尹世平大概從未想像過,他家中的腦癱妻子、賴活等死的農村婦女,居然會成為著名詩人,而且賺到遠高於勞動半生的收入。是的,余秀華的稿費甚至多到可以經濟獨立,即刻付現金用十五萬人民幣跟丈夫買起/賣掉名份,結束拖累自己半生的婚姻。
「我是穿過槍林彈雨去睡你/我是把無數的黑夜摁進一個黎明去睡你/我是無數個我奔跑成一個我去睡你」
〈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是余秀華於2014年所作的愛情詩,詩中著名的這一段,用字剛烈,勇悍直白,不但將女詩人對愛情的嚮往表現得淋漓盡致,亦揭露了余秀華對慾望落空,無法逃離身體限制的種種痛苦。〈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行文風格別樹一幟,狂野豪放之餘,亦打破了近年中國文藝圈子矯情造作的主旋律,余秀華稱得上是一詩成名,搖身一變成為「網紅」詩人,名副其實是「穿過大半個中國」。
剛冒起時,余秀華曾被譽為中國的Emily Dickinson。但從今日來看,這其實已不準確。美國詩人Emily Dickinson確實行文尖銳,用字簡潔,但她一生孤僻,甚少公開露面,在世時確實沒發表過太多作品,而大部分藏在房間裡的詩作死後才出版。或者當初那個平地一聲雷,那個「你想走你想飛,但是你飛不起來」的余秀華,確會讓人有相同的聯想,但隨著迅速走紅,余秀華人生徹底翻轉,從一介農婦變成中國詩壇聲名鵲起的大紅人,還陸續出版了《搖搖晃晃的人間》、《月光落在左手上》和《我們愛過又忘記》等詩集,而且頻頻曝光露面,上電視節目、上讀詩會,毫不介懷自己的腦癱缺陷。有趣甚至有點諷刺意味的是,曾經說過「寫詩是不能讓人看的,像做愛一樣」,認為詩是私人的,不應被社會炒作的這位女詩人,如今網絡上隨隨便便都可以找到她寫過的詩句,而她和丈夫尹世平的分離怨恨,更隨著2016年她的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的面世而傳遍了整個中國。

爆紅過後,坊間對余秀華詩作及為人的評價變得兩極,有人盛讚其草根真挈,既露骨而前衛尖銳,打破中國詩壇舊貌,但其實她亦招來許多妒嫉和反彈,除了關於「蕩婦體」嘩眾取寵的批評,同時隨著她的過人名氣而被指風格重複,有意將自己偶像化,甚至有詩人質疑她過份自大。可以想像的是,這份自大或多或少源於現實中長年累月的壓抑和自卑感。誠然,成為詩壇代表之後,余秀華更見張狂進取,而當中最明顯的一點,是她非常著跡想要超越海子的成就。
在余秀華之前,「春天」或者一直都是屬於海子的,全中國詩集銷量最高的當代詩人。當然,海子不是真的寫過很多遍「春天」,但〈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實在太過出名,幾乎人人都會背誦。而自出道開始,余秀華很喜歡用「春天」這兩個字,甚至頻密到令人覺得她是故意的,然而,她的春天毫不明媚,卻是伴隨著虛幻、痛苦、短暫,是一個引人走進歧途或提心吊膽的春天。
海子年少成名,而且是北大法學院畢業,典型中國知識分子,但年輕早逝,跟蹉跎半生被婚姻困住廿年的余秀華是兩個極端。網絡上有傳余秀華曾狂言「海子太年輕,我寫得比他好一點點」,真偽難以考究,但余秀華的詩集裡確曾寫過幾首關於海子的詩,包括〈遇見海子〉。
「他在人群裡,我沒有看出來。都是近視的我們/對世界保持著警惕」
「我把太陽放在他曾經放過的位置上/但是從來不反對/風把草籽吹到沙漠上」
余秀華最終沒有選擇成為Emily Dickinson,卻沒有掩飾自己想成為下一個海子的野心。直白鮮明的慾望,無論對於愛情,或是對於文學創作,余秀華就是如此剛烈。但網絡世界的潮流變得很快,穿過大半個中國之後,她擺脫了腦癱、窮困、農婦這些舊標籤,卻又不經不覺被掛上自大、暴發、偶像化的新標籤。
「我有月光,我從來不明亮/我有桃花,我從來不打開/我有一輩子,浩蕩的春風卻讓它吹不到我」,或者余秀華早已成了風潮,甚至穿過了海子,但當過去的作品像春風一樣迎面搧過,又能否再次穿過那個曾經穿過大半個中國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