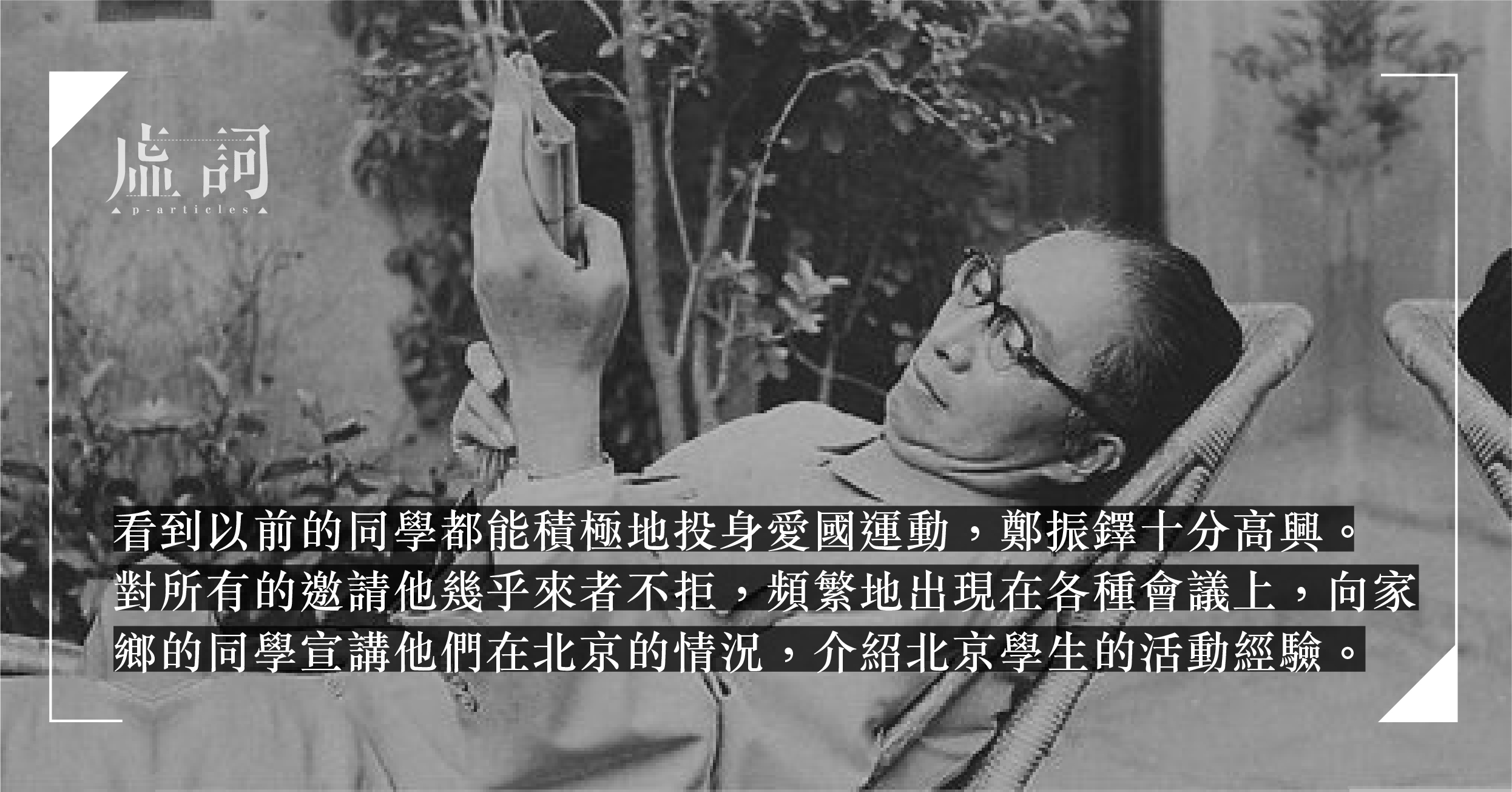【五四百年小輯】鄭振鐸︰風雷中的新探索
現象 | by 書摘 | 2019-05-04
像許多親歷過「五四」的人一樣,從一個學工科的普通學生,到一名優秀的學者和文化活動家,對於鄭振鐸而言,這迥然不同的人生選擇的轉折點,正是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中,不但完全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方向,還為以後的事業開闢了全新的天地。
1919年5月4日,是一個星期天。吃過午飯,鄭振鐸沒有像以往那樣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圖書館去看書,他躺在床上,決定好好放鬆一下連日苦讀而略有些疲憊的身心。自從他下定決心離開家鄉到北京來求學,已是兩年過去了。1918年,他順利地考上了交通部鐵路管理學校英文高等科。這所學校不但學費低,而且畢業後的工作也有保證,再加上三叔的極力推薦,他沒有另加選擇。入學後不久,他偶然發現了青年會的圖書館裡有不少好書,尤以俄國文學名著的英譯本為多,這使他欣喜若狂。以後,他就整天泡在那兒,埋首於那些大部頭的著作中。在這個小小的閱覽室中,他還結識了一些也經常來看書的年輕人,並且和俄文專修學校的學生瞿秋白、耿濟之,匯文中學的學生瞿菊農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他們幾乎天天見面,在一起閱讀俄國文學,討論《狂人日記》,評點國家大事,十分投機。那幾天,正在巴黎召開的和會一直是他們談話的重心。
鄭振鐸剛剛合眼睡了一小會,忽然被窗外的一片叫喊聲驚醒了。他急忙翻身下床,跑到外面的一個空場上去看。只見東面趙家樓的上空正翻騰著濃黑的煙,夾著血紅的火焰,突突地向上冒著。「是哪一家失火呢?」他正這麼想著,忽然看見一個頭上受了傷、裹著白紗布的巡警,由兩個同伴攙扶著,走進了空場上的「警察格子」。沒過多久,他又看見一個學生模樣的人,穿著藍布大褂,飛奔過來,幾個巡警在後追著,追到空場上,把他捉住了。鄭振鐸十分驚訝地看著這一幕,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鄭振鐸(左二)與瞿秋白(左一)等《新社會》成員合影。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趕到學校,正碰上幾個同學在熱烈地討論前一天的事情。他旁聽了一會,又急忙找來了當天的報紙,才知道那場大火是怎麼回事,而他自己的學校因為不起眼,沒有被通知參加活動。
鄭振鐸的情緒立即激動了起來。他一面為前一天近在咫尺卻未能身臨其境而遺憾,一面立即組織自己學校的活動。他首先趕到了馬神廟的北京大學第二院,參加了當天組建的「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成立大會,他作為鐵路管理學校的學生代表,在會上發表宣言,參與討論,非常積極。他的發言給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於許多年後,當時還是協和女大一年級學生的冰心仍清晰地記得那個大個子慷慨激昂的形象。他們還打聽到一些在天安門廣場演講的同學被關押在天安門的兩個門洞裡,鄭振鐸就和其他同學一起為這些勇士送去食物和鋪蓋,但全給軍警毫不留情地攔住了。交涉了不少時間,軟磨硬泡,最後幾乎要破口大罵了,仍是沒有結果,待到他憤憤地回到家中時,已是半夜了。
沒睡多久,叔叔就把他叫了起來,責問他昨天的去向,並且再三告誡他不要多管閒事,這幾天只能待在家裡,不許外出。他一聲不吭地聽著叔叔的嘮叨,心中卻在想著當天要做的事情。急急地吃完早飯,趁著叔叔嬸嬸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家門,又趕往北大去了。
北京的事態愈加嚴重,北洋政府的態度居然十分強硬。5月9日,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離京,引起學界一片震動。北京各大中院校立即宣佈於5月11日一致罷課,以示抗議。各校的學生代表則天天聚在一起開會,商討時局的進展與學界的對策。鄭振鐸在會上遇見了圖書館裡的老朋友瞿秋白、耿濟之和瞿菊農等人,他們也分別做了各自學校的代表,大家在這種場合重逢,自然十分高興。然而,正如他以後所回憶的那樣,在這樣一場大運動中,雖然總的方向和口號是統一的,對外亦能同仇敵愾,但學生們的思想良莠不齊,態度自然也不會完全一致。辯論和鬥爭自是難免,但其中也顯示出「封建性」的「門戶」。像在學生聯合會裡,鄭振鐸等幾個人代表的是小單位,非常不引人注目,也沒有其他大學校的人主動與他們一起新探索活動。他和瞿秋白等人比較熟悉,同病相憐,這群來自俄專匯文和鐵路管理的人便很自然地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小「集團」。成熟老練的瞿秋白當然地成了他們的「首領」,而鄭振鐸無疑是他們中熱情最高、最熱衷於組織工作的一個。
由於風聲很緊,他們時常變更開會的地點,大多定在東城的匯文等幾個教會學校,時間總是在晚上。一個個地溜進去,開完會後又一個個地溜出來,不敢成群結隊地走,還得時時防備有人「盯」著。雖然很危險,但大家仍盡力地工作。鄭振鐸以後對此曾有過十分親切的回憶:「我們都是第一次從事於學生運動和組織工作,所以一切都很生疏。但是,議決了,便去做,誰也不推諉,誰也不躲避。雖然行動很謹慎小心,卻絕對不故意的躲避危險。」(《前事不忘》)
但是,交通部和鐵路管理學校當局卻十分害怕學生鬧事,先是下令全體學生於6月3日分赴京漢、京奉、京浦三路旅行參觀;後來又宣佈取消學期考試,提前放暑假,強令學生們在6月4日回家,還提供了免票乘車的優惠。北京的運動正開展得如火如荼,鄭振鐸根本不願意在此時離京,但叔叔嬸嬸生怕他的「胡作非為」連累他們,極力勸他回溫州,哪怕暫時離開也好,省得他們操心。鄭振鐸也已有兩年因為沒錢買票而沒有回家了,心中十分牽掛母親和祖母,難得有這麼一次機會,他只得同意南下,回溫州省親。
讓他喜出望外的是,北京的學生運動在全國已大有星火燎原之勢,不但上海、廣東紛起響應,即便僻處東南一隅的家鄉小城,也已經感受到愛國巨浪的衝擊。5月中旬,溫州的學生就成立了自己的聯合組織,上街遊行、發佈宣言、集體罷課,一樣幹得有聲有色。他一回到家中,舊日的夥伴便圍住了這位來自運動中心的大學生,要他講講北京的最新動態。看到以前的同學都能積極地投身愛國運動,鄭振鐸十分高興。對所有的邀請他幾乎來者不拒,頻繁地出現在各種會議上,向家鄉的同學宣講他們在北京的情況,介紹北京學生的活動經驗。對他而言,這不過是從一個戰場轉移到另一個戰場。與此同時,他還應老同學之邀參與了《救國講演週刊》的創辦。這份售價僅為五枚銅板的小刊物面向溫州的普通百姓,內容通俗易懂,文字深入淺出,形式生動活潑,文筆大膽深刻,針砭時局毫不留情。給該刊寫稿的大多是溫州各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鄭振鐸自然也是其中非常活躍的一個。雖然作者們多用筆名,我們如今已無法確知哪些文章是他所寫,但可以肯定,這其中必有不少出自他的手筆。這個刊物只出了幾期,便因為冒犯了當局,不但被禁止出版,而且編輯部也被查封了。這是鄭振鐸第一次參與編輯刊物,也是第一次嘗到刊物被查封的味道;自然,他當時並沒有想到,那些以後都將成為他生活的主旋律。
除了編輯週刊,鄭振鐸在家鄉的另外一項重要活動,就是參與了溫州第一個新文化團體——永嘉新學會的組建。這個學會的成員大多是追慕新思潮的年輕人,畢業或正就讀於各地的大學,他們的思想雖不完全一致,但總的說來是力圖更新墨守成規的思想界,「使新舊學術,融化為一爐」(《〈新學報〉發刊詞》)。鄭振鐸雖然不是學會的主要成員,但奔走聯絡很是踴躍,並且首倡出版會刊《新學報》。8月中旬回到北京之後,他還為《新學報》撰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長篇論文《中國婦女的解放問題》,從幾個方面論述了婦女解放的必要性與方法。
這些在暑假前並沒有預想到的實踐活動為他以後的工作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也使他首次發現了自己在這一領域的才能和興趣。之後不久,他就與瞿秋白等人創辦了《新社會》旬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從撰稿到排版校對,事必躬親,使他對編輯出版工作有了更加直觀深入的了解。此後參與籌建文學研究會,主管會務;直至幾年後被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看中,南下上海,他在出版和組織方面的傑出才華方得到更為充分的發揮。
像許多親歷過「五四」的人一樣,從一個普通鐵路站長的後備人選,到一名優秀的學者和文化活動家,對於鄭振鐸而言,這迥然不同的人生選擇的轉折點,正是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之中,不但完全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方向,更為以後的事業開闢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五四」對於他的最大意義其實就在於此。
(文章摘錄自陳平原、夏曉虹主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香港中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