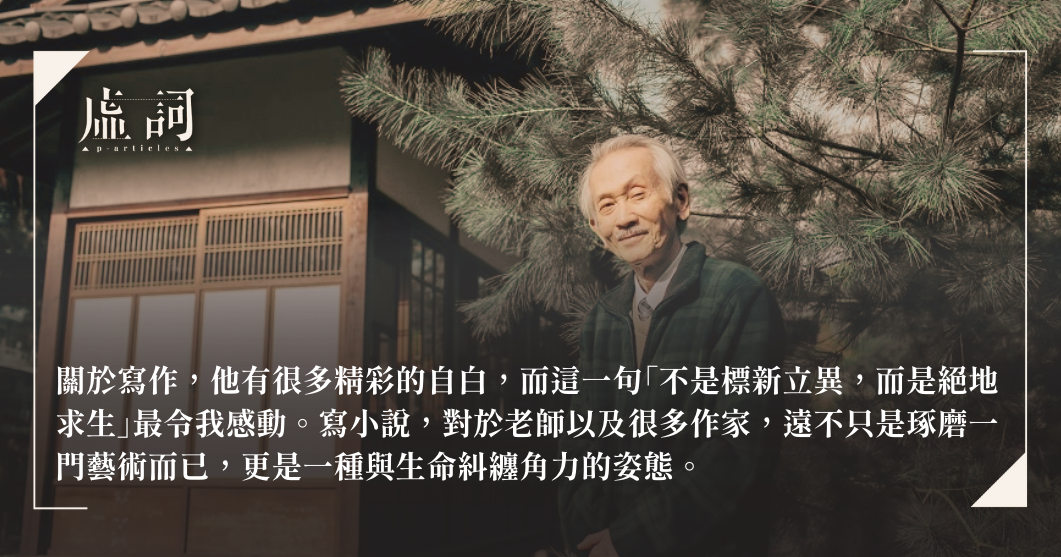我的老師王文興
其他 | by 陳麗芬 | 2023-11-10
「但是我就是要發洩點甚麼,爺就是要扯起喉管號叫點甚麼。」
我的老師心裏住著這個爺,這個爺是在衆人面前沉穩謙和的老師的他我,一直潛伏在那裏,蠢蠢欲動。40歲時,我的老師終於釋放了他,讓他粉墨登場,做一個「背海的人」,扯起喉管好好叫個夠:「操!我操!他媽了個屄!操他娘!狗!狗屄!狗屁!」 嚇了讀者一大跳,溫文儒雅的老師豁出去了,火山爆發,在紙上表演了一場激越的腹語術。爺是老師那怡然外表下狂野恣意的靈魂。
在爺即將現身為爺之時,其實也曾有一次,令人出其不意地闖進江湖,以一個很不同的面貌,狠狠地「發洩」過。1978年當鄉土文學運動正如火如荼,文壇江湖一衆大佬在象牙塔裏打著激烈筆戰,或附庸權勢,道貌岸然,亂扣人帽子,或氣急敗壞反擊,狂飆意識形態。一片喧囂之時,只有我的老師走出書房,異想天開地舉辦了一場空前又絕後的演講會,單槍匹馬,以行動代替筆桿,做足了功課,以具體數據資料駁斥空洞浮誇的高論,批判各家排斥多元聲音的霸道。於是,這個衛道人士眼中的「不孝子」,又被添加了一條污名:「這個教授王文興」。然而,正是這個教授王文興的那一場突兀的「亂入」,在當年口號泛濫的文學論戰中,譜下了最坦蕩、直樸踏實的一章。
爺原就是個憤怒青年,從來都是。在戒嚴時期,我的老師也曾經如許多年輕人,好端端走在街上,便莫名其妙被拉進警局,强制剪短髮。1972年暑假的一天,30歲出頭的老師剛完成《家變》,小説即將在《中外文學》連載之際,必是心情輕鬆,去中南部玩了一趟,就遭遇到了那漠視人權的粗暴行為,而且更因為教師的身份,受盡言語上的侮辱。在那個動輒得逞,人人隨時會被剝奪人身自由的年代,多數人只有忍氣吞聲,以期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怎料事發後兩天,我的老師居然發了封信給警務處處長强烈抗議,信也同時投給國民黨眼中釘的《大學雜誌》刊登。膽大包天,特立獨行,這就是我的老師。
爺一路走來,與老師共同經歷了一些很詭異的事件,目睹老師的遭禁出國、被某系開除、研究室的一場神秘火災、學院内的爾虞我詐.... 看盡了一部羽翼被亂剪的歷史。
而我們卻從來沒有看過老師發脾氣,他總是那麼和顔悅色,老師讓他的小説人物替他發脾氣,有時也替他動粗。他以寫作抵抗生命中的風暴,以暴制暴,他是面對巨人哥萊亞斯的一個少年大衛,以小博大。〈命運的跡線〉、〈大風〉、〈黑衣〉、〈寒流〉、〈草原的盛夏〉、〈海濱聖母節〉、〈龍天樓〉.... 篇篇觸及存在的可怖,渺小的人,在令人畏懼的命運之前,沒有甚麼選擇,唯有逆風而行,意志力就是人的所有。而這存在主義意旨下的荒謬英雄,卻也隱隱間透露出對神秘主義的沉迷。隨著歲月,憤怒與反抗的能量漸漸提升轉化為與神的對話,蔑凟與膜拜吊詭地互換並存。「弑父」的范曄取代了父親,順理成章變成了比父親還大的爺,爺盡情地又「他媽的」更往前一步「弑母」,自我放逐於一切,無法更無「天」,令人悚然心驚。但他們的作者最終的走向宗教,且又偏偏是皈依聖母的天主教,更叫人吃驚。然而這樣的矛盾,在我那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老師又是必然,因為在極端中橫行,以極端剋服極端在老師彷彿是一種本能。
以暴制暴,不僅内容,也是形式。寫作,在我的老師,是一場又一場的出征。別人寫作是靜態的爬格子,在他卻更像是個肉搏戰。他又劃又割又撕,又敲又打,一張張傷痕纍纍的紙片是他的「草稿」,滿佈著只有個人才能辨識的「密碼」,是轉化成「字」前的節拍律動符號。如此怪異罕見的書寫方式,以及慢得不能再慢,悠長的創作過程,早已成為文壇上的傳奇。傳奇之所以成為傳奇,正是因為它反襯出我們對「快」、「多」的視以為然。而那樣一心一意猛力擒拿直感的騷動、主觀經驗的刹那,在一個機械複製,擬像無所不能的時代,更喚起了我們對靈光乍現的「原初」的鄉愁,對「真跡」的想像。
曾經「現代」的「現代主義」文學,如今自然已進入了文學「史」,而老師已被經典化的現代主義文學更帶著一種絕對的純粹,種種都使得「王文興」這個名字,對於諸多後輩,已幻化成一個不可思議的,似乎屬於「過去」的「奇觀」。然而,無論外界如何看他,我的老師始終自顧自的過他的,堅忍執著地仍「每日和文字浴血奮戰,拚殺得你死我活」。儘管他在《家變》後的作品已明顯失去當年聳動的震撼力,他依然故我,無視於所謂後現代的種種「新」潮流,孤注一擲,心甘情願的走火入魔,數十年來,在他稱之為「牢房」的斗室裏,做漫長的「困獸之鬥」,日日如此,義無反顧地投入一場文字上、道德上、信仰上,既微型又巨大的「無休止的戰爭」。
「我已經停止生活,只觀察,而無經驗。」他說。 作為一個作家,有誰敢這麼說?作家—尤其是小説家—不是最有「生活」,最應該有「人生經驗」的嗎? 而我的老師卻總是那樣「大方」地宣稱自己「沒」生活。而沒生活,其實是因為他刻意「戒掉了」生活。為了專注寫作與閲讀,音樂,他不聽了,電影,他也不看了,所有我們以為構成一個好生活的要素都太花時間,也太費神了。創作的「生命」有限,只好去蕪存菁,將「生活」簡化再簡化到「沒有」。生活不等同於生命。決絕至此,看來極為超脫反世俗,然而,如果說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寫作「神話」,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倒反而是一個最顛覆「作家」神話的作家,他身體力行,示範了寫作從來不是甚麼瀟灑風雅的事,作家並非邊寫邊吐煙圈,甚麼靈思泉湧的仙人。創作不是魔法,是勞動,也是工藝。甚至,那些看來最驚世駭俗的文學,往往就生自最單調無聊的生活。
老師既安靜又暴烈地寫著,寫了一生。為甚麼而寫?為「自己」而寫,他說,不為今生,也不為身後的聲名,純粹只為了「寫作當時的充實之感」。關於寫作,他有很多精彩的自白,而這一句「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地求生」最令我感動。寫小説,對於老師以及很多作家,遠不只是琢磨一門藝術而已,更是一種與生命糾纏角力的姿態。「困獸猶鬥」既是自我折磨,又未嘗不是個最浪漫的生存儀式?無中生有,始能在荒謬無意義的人生中,生出沒有自由中的自由。
此刻,我彷彿看到老師和爺在天上,正在「慢讀」我這篇文章。看完後,會不會點點頭,笑了起來,說:果然是我的學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