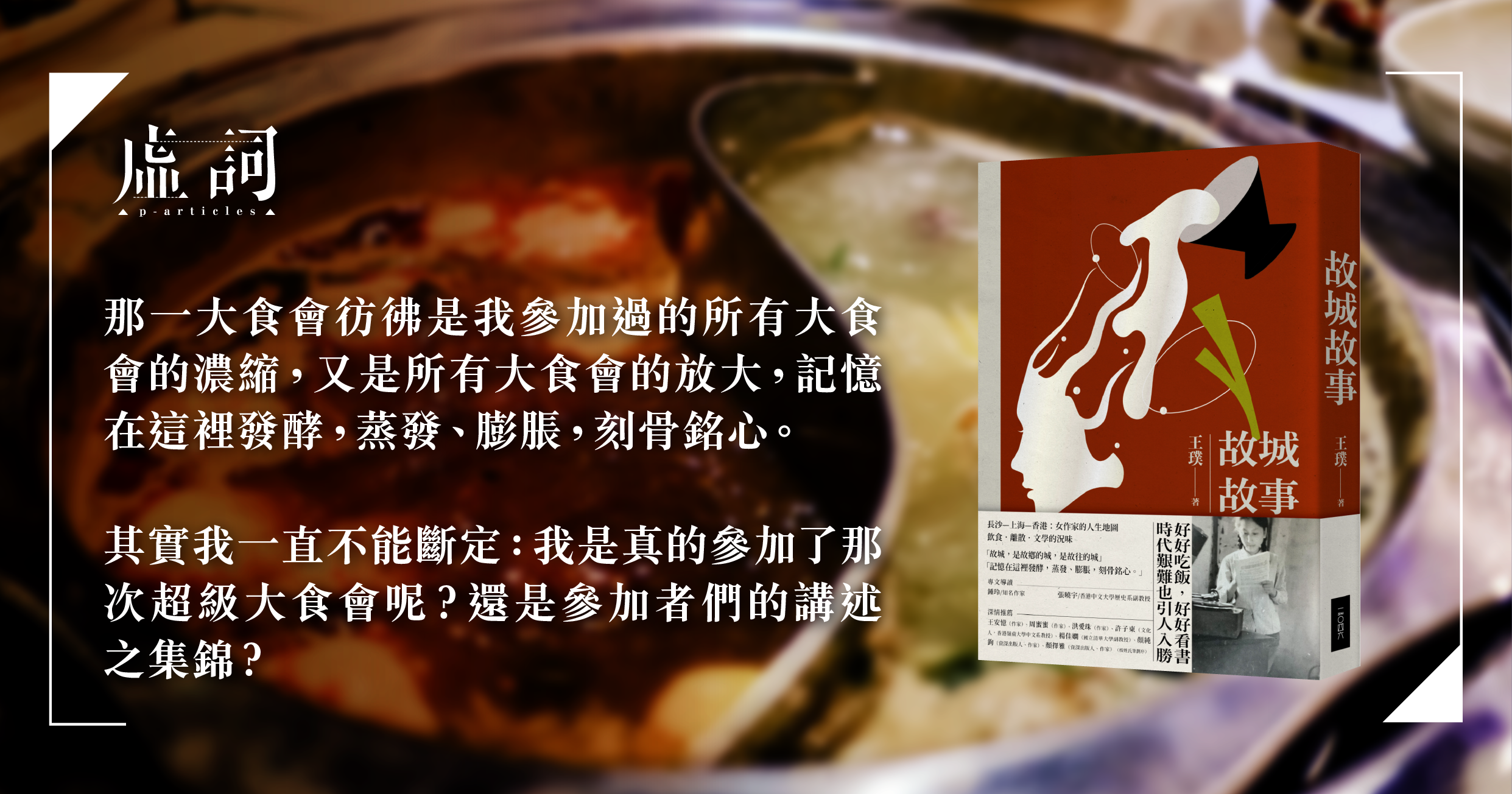【新書】王璞回憶錄《故城故事》——〈大食會(吃的是才子)〉
書序 | by 王璞 | 2023-09-14
我曾描寫過香港大學生的大食會:在《貓部落》〈三十七號仔之歌〉裡。在那部總共十三章的小說中,這一章是我最為得意的一章,其中的人物和背景貌似香港,其實許多細節來自我的華東師大記憶。是上世紀八〇年代大陸大學生大食會與本世紀初香港大學生大食會的合體。(必須慎重說明:為免麻煩,這裡提到的人名皆非真名,多借用小說《貓部落》一書中的人物綽號。)
大食會乃香港俗語,意為一班朋友相聚一堂,胡吃海喝。就其生動性而言,比華東師大時代我們口中的「聚餐」,更接地氣。大者,狂也,一幫被那飯堂青菜肉丸大排吃得「口裡淡出鳥來」的學子,將一些胡亂搜羅來的食物聚集一處,以一些也是胡亂搜羅來的鍋盆碗盞煮炒燜拌,海吃海喝。
與〈三十七號仔之歌〉的大食會相比,我們當年的大食會要清貧得多,參與者們也沒有香港大學生那麼放浪恣睢。可以說,〈三十七號仔之歌〉的大食會是我華東師大記憶的一次想像性釋放。
二十一世紀初,當我那在香港中大唸書的兒子向我講述他們一幫同學在出租屋打邊爐的情景,十多年前麗娃河畔大食會的一幕幕,便不由得在我腦海中浮現。那時我正在苦苦構思著一部長篇小說。故事和細節都有了,卻找不到一條能把那一切貫穿到一起的引線。這一下,突然之間,它出現了!那條上下求索多時而不可得的引線,只消把它一拉,嘩啦啦,嘩啦啦,那整部小說就像自來水一樣流瀉而出,只須拿個盛器接著就行了。
華東師大三年,我參加過多次大食會,小型的、大型的;拉出去的、打進來的;興之所至的,精心策劃的;師出有名的,無緣無故的,但不知為何,最後的思緒總是定格在那個夜晚,那個房間,那群人。對,那一大食會彷彿是我參加過的所有大食會的濃縮,又是所有大食會的放大,記憶在這裡發酵,蒸發、膨脹,刻骨銘心。
其實我一直不能斷定:我是真的參加了那次超級大食會呢?還是參加者們的講述之集錦?
那次在九舍九二一室舉辦的大食會。九二一室,那大概是師大宿舍中房間最大、人數最多的一間了,四五十多平米的空間,放了九張雙層鋪,住了九名研究生。他們各自用書架或布縵在房間裡割據出自己的一塊天地。至今回想起來我仍然驚奇:那間房子真大呀!九分天下之餘,居然還在中間留出了一塊空地作為其住客會友的公共空間,給他們提供了舉辦大食會的地利。
一隻大電爐放在中間那張大桌子上。電爐上放了個足有臉盆大的鋼精鍋。鍋上熱氣騰騰。那充斥了整個房間的複雜氣味顯示,鍋裡面有多種食物在沸騰。
有位評論過我小說的香港學者曾好奇地問我:「為甚麼你小說裡一寫美食就是打邊爐呢?」
當時我愕然:「真的嗎?」
過後我翻查一下他評論中提到的那幾篇小說,果不其然,幾乎篇篇都有關於火鍋、也就是「打邊爐」的的描述。而《貓部落》中的大食會,也是一場火鍋盛宴。
小說中打邊爐的場地是香港村屋,其實很多細節是師大九舍那間大房子的寫照。
九舍位於學校中心地帶,一座小石橋令它與夏雨島藕斷絲連,麗娃河遙遙在望,中文系小樓則與之隔林蔭道相依,而樓下就是當時師大校園裡唯一的一間書店——校園書屋。
八〇年代是中國思想解放鼎盛時期,國門初開,各種四九年以來被隔絕的西方思潮鋪天蓋地而來。各種系列各種流派的思想文化名著、歐美乃至拉丁美洲各國的現當代小說被源源不斷譯介。我們的校園書屋雖然迷你,但書店經營者裡大概有高人,讓書店得國內學術風氣之先,幾乎天天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史哲新書出售。書店外面立有一塊小黑板,上以彩色粉筆書寫的新書預告日日更新。每有重量級新書出售,大家就奔走相告,到了開售日就早早跑到門口排隊搶購。
一九八六年那個周末的晚上,我跟在梅兒後面走進那間大房子時,手裡就拿著剛在書店買到的一本新書。
先前,作為那房子的居民,桑穆、阿易幾次邀請我們參加他們大食會,都被我婉拒。我向來不喜湊熱鬧,跟他們又都不熟。梅兒去過一次,回來跟我興奮地述說東西如何如何好吃,氣氛如何如何熱烈,參與者都有誰誰誰,大家的言談如何如何趣味橫生。
「小德從他老家帶來了東北粉條,列米帶了他媽自己包的小餛飩,還有意大利通心粉,你沒有吃過吧?是桑穆的朋友從意大利帶給他的,好吃得來!大立吃了一碗又一碗。大立你知道吧?就是那個中文系第一號才子。外語系第一號才子約翰也來了。他剛從美國回來。講了好多美國事情。還有小右派,那可真是個活寶,他只要一開口,就把大家笑得肚子痛,可惜我口才太差學不出來。」
她說的前三項都不怎麼吸引我。大食會當然氣氛熱烈。那些男生能作出甚麼好東西來我則不存奢望。師大才子我也在各種場合見過了不少。那正是師大才子輩出的年代,中文系更是老中青三代才子咸集之地。你在中文系小樓裡轉一圈,總能碰上那麼幾位。
不過最後那一項卻有些令我心動,一天到晚寒窗苦讀,聽笑話是最好的調劑了。小右派的活寶之名我早已聽聞,不過大家見面都在教室和會場,我想像不出他那一副苦瓜面孔說笑話時是甚麼樣。所以這日阿易又來邀請我們,正好我又要過去買書,就答應了。
時隔二十八年,許多曾經轟烈的人與事在我心中已了無痕跡,可我清晰地記得我們走進房門的那一景。沒錯,我是真的參加過那次大食會,一進門就迎向我的那個人、那兩道閃亮的目光煥然眼前,歷歷如昨,他是桑穆。
那張盤據在大桌子旁邊的其他面孔,由於熱氣騰騰,由於人頭湧湧,我都看不清。只有這張迎向我的面孔清晰而生動,不甚優美的細部消隱在了蒸氣之中,只剩下那流露出聰明智慧的主線條,如同一幅由藝術家勾畫出的素描,看去煞是親切。
「你真漂亮。」他說,燦然一笑。
有位作家曾經描寫過桑穆的笑容,他也是我們的華東師大校友,說是「當他那張嚴肅的面孔上綻開了笑容,那可真是嚇人」,但我怎麼跟他感覺正好相反呢?在我眼裡,那張憨厚面孔笑起來時,一雙小眼睛就瞇成了兩道縫,眼角朝下彎彎,從那裡面射出來的光芒是真誠的,是熱烈的,是誠懇的,使你由衷地相信,他說出的話絕對出自真情實意。
不過,老實說我當時雖然心有所動,卻並沒把那句話放在心上。畢竟,我早已過了戀愛季節。那年我都三十六歲了,兒子都已四歲,我與兒子他爸從熱戀到形同陌路的經歷,讓我對婚戀失望到了極點。如今拼命擠進了大學校門,動力之一就是要逃出那已經到了無解地步的家庭困局,拿到學位,遠走高飛。
那天我們吃了些甚麼、喝了些甚麼、又談了些甚麼,其實我已經記不太清了。它跟我在師大參加的所有大食會混成了一片。我想,無非是一幫從精神到肉體都處於飢渴狀態的青年學子在肆意消費青春,朦朧醉眼中,一切都在膨脹,「⋯⋯今日在谷底,明朝衝雲霄,三十七號仔個呀個個是英豪。」也許,《貓部落》裡那首〈三十七號仔之歌〉,那天夜裡已經在我心中萌芽。
不,其實我還是記得一些甚麼的。要不怎麼每逢回憶起師大大食會,第一時間湧上心頭的總是那天大食會的情景呢?對,我想起來了,突現在其他所有大食會的朦朧霧氣之上的,是桑穆那張興奮的面孔,以及他旁邊的那顆碩大無朋的腦袋,柏拉圖。
現在,我清晰地看見了柏拉圖那張與桑穆一樣興奮的面孔,不過跟桑穆那張白裡泛黃的瘦臉不同,柏拉圖的團團大臉因吃得興起通紅通紅,活像煮熟的龍蝦。
柏拉圖是中文系研究生中的二號才子。一號才子是他同門師兄。那是一位面目清臞神色沉鬱的青年,望去儼如從容就義時的中共烈士瞿秋白,光憑這一點就足以讓我們對他心生崇拜了。但柏拉圖的形象則活像其師兄之反諷,寬厚紮實的肩膀上扛著一顆令人無法忽略的大頭,說得好聽點是天庭飽滿,說得難聽點是肥頭大耳。
其實柏拉圖並非九二一室的住客,但他生有一副即食即消的肚腸和一隻對美味有特異功能的鼻子,九二一室一有大食會,他總能及時聞風而至。
那日一見此君在場,我進門時歡快的情緒便有點黯然。儘管不止一次有人遙指著他向我推介:「看,那人就是文章上了兩次《讀書》的柏拉圖呀!」儘管我也已知道,柏拉圖他不僅有文章上了《讀書》等熱門期刊,還有一篇更牛逼的文章因其離經叛道的觀點犯了忌,以半地下的形式在全國大學校園瘋傳,我卻對他敬而遠之。
我讀過他那篇地下流行的宏文,當華麗的文采、出位的言論所引起的震盪過後,我並不感覺自己比讀它之前聰明了點兒或是充實了點兒。況且我不喜歡那種自信滿滿的腔調,經過文革大字報的洗禮,我對一切張揚文風都有過敏反應。
(編按:本文節選自王璞回憶錄《故城故事》「大食會」一章,分兩次刊載,第二篇為〈大食會上的理論派〉,標題均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