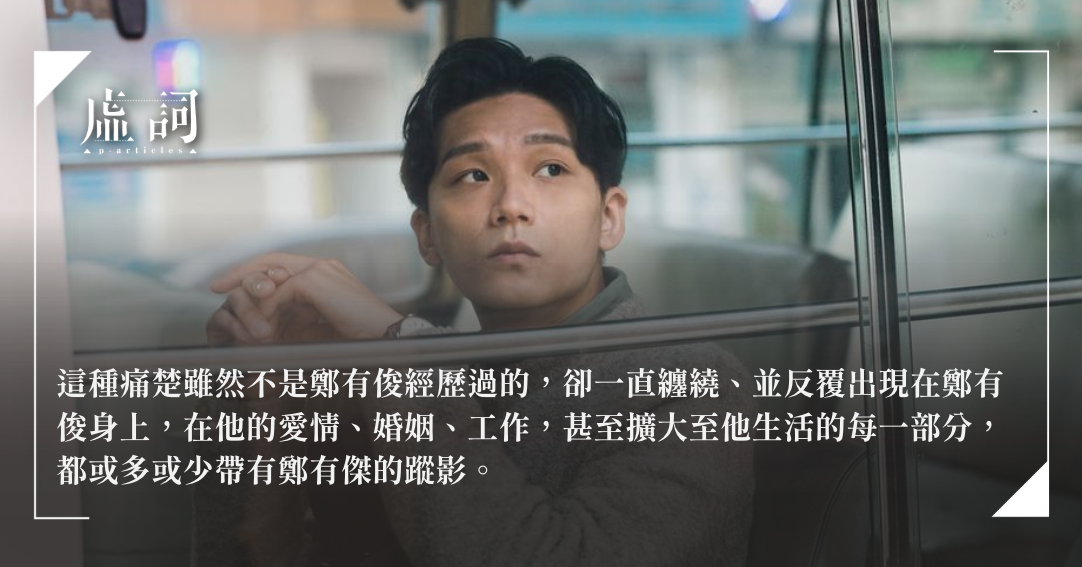《年少日記》榮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和觀眾票選最佳影片,葉嘉詠撇除原生家庭問題、學童的心理健康等議題,集中討論電影中的日記和配音兩個細節,突顯文字與聲音與角色設定的關係。她認為電影由一封沒有署名的遺書開始,而遺書必需與「年少」合併討論才有意義,「年少」比「少年」所指涉的更為廣泛,藉此叩問大眾或許經歷過、旁觀過的痛苦。 (閱讀更多)
香港如今無恙否?──略說紀錄片《詩》
詩人崔舜華在台看《詩》,想起遠方香港的尋常風景,惟現況就是去了香港卻再回不去香港。眼見黃燦然現居深圳,廖偉棠安家台北,想來皆是離港人,以離港之眼凝望在港眾生,誰都不免是永恆的異鄉人,她認為這也許是導演許鞍華刻意取捨的距離。香港故事如此難說,崔舜華身為一個曾被香港深深擁抱的異地人,留下一句「香港,如今無恙否?」 (閱讀更多)
《年少日記》的有俊和有他的《4891》
《年少日記》引來全城對學童精神健康的關注,雙雙首先認為此電影可分為兩部分:「年少日記」與「餘生」。他再從盧鎮業早前出演過黃妍的一系列MV作比對分析,書寫年少日記的,有其「哀傷的作者」,而世界讓鄭sir承受痛苦,他卻以對學生、新的少年的陪伴作為如歌的回報;結尾的天台作為一個異世界之門,鄭Sir與有傑重逢,是補償了多年前沒有正式道別的虧欠。 (閱讀更多)
《東尼瀧谷》與《在車上》裡的聲音
影評 | by 劉梓潔 | 2023-11-28
每當劉梓潔套進那雙黑皮鞋時,就會想起被封為「最忠於原著」的村上春樹改編電影《東尼瀧谷》。若問〈東尼瀧谷〉小說在講甚麼?劉梓潔想就是「孤獨」兩字,她認為市川準將「孤獨」改編到極致,後來對拍攝現場實務更加了解之後,對《東尼瀧谷》更加敬佩。她再談到濱口龍介想在《在車上》做的,是將語言聲音這項技藝逼迫到極致之後,探觸超越語言、甚至無需聲音的所在。 (閱讀更多)
《白日之下》:受害者濕透的身體是否公義的不在場證明?
影評 | by 凜 | 2023-11-15
白日之下,本應是莊嚴而神聖的,但在這威光下,惡行原形畢露。凜分析《白日之下》的兩個場景,指出報館的燈光在彩橋之家被揭發惡行後,與殘疾人變成無家者後產生強烈對比;而尾段一場大雨所隱含的意義,正是對曉琪作出關於公義的靈魂拷問,曉琪分不清楚令視線變得模糊的是自己眼眶容不下的淚水、殘疾人和家屬們飛濺的唾液、還是為白日提供不在場證明的雨水。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