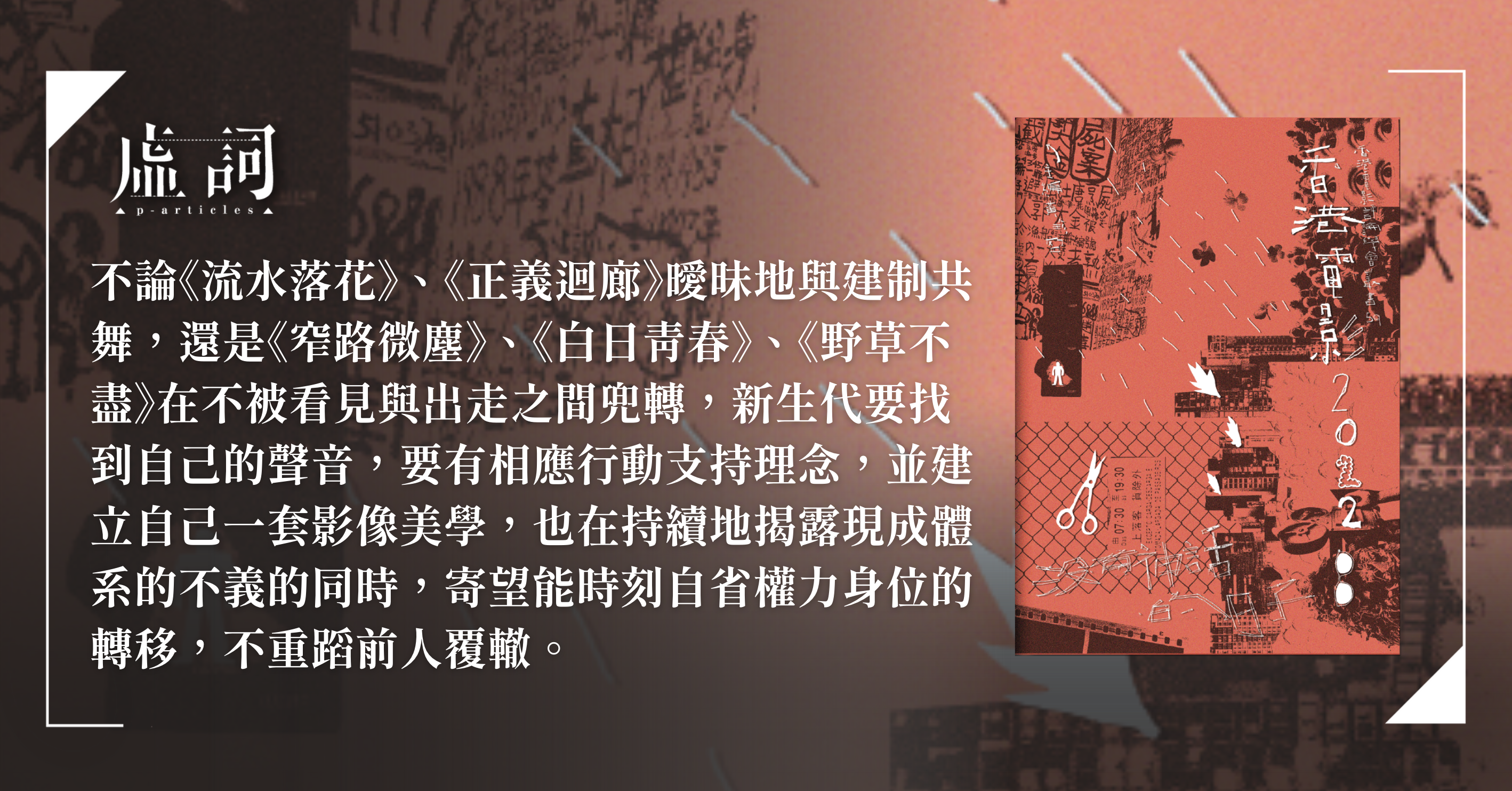《蒼鷺與少年》紛亂時代的自白與叩問
宮﨑駿再度食言,時隔十年後以最新作品《蒼鷺與少年》復出,延續其反戰思想。石啟峰分析二戰倖存者的主角——牧真人如何壓抑著喪母創傷,走進魔幻,卻終於選擇回到殘酷現實;他又以同樣經歷二戰的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從存在哲學說明真人的界限處境,及其超越自我的反思。 (閱讀更多)
從香港詩到香港詩人,祛魅的觸動——談許鞍華《詩》
詩人李顥謙認為即使近年風氣改變,一說到香港的現代詩與詩人,還是可以感到一些文青或評論人的蔑視針對,更徨論當下很多詩人不為人所知的邊緣處境。是故許鞍華的紀錄片《詩》有著一個非常關鍵的意義——香港詩與香港詩人,不僅值得由一位名導演拍進電影,而且更應該獲取一個被公開注視、公開討論,通行於時代與歷史的資格。 (閱讀更多)
三齣殺人後如常生活的活地阿倫電影
活地阿倫第五十部電影作品《迷失幸運兒》上映,何兆彬認為這部電影充滿活地最愛寫的元素:上流社會、愛情、生命中的抉擇,與《歡情太暫》和《迷失決勝分》相似,三部作品都有「殺人後犯人沒有被抓,如常生活」的驚人橋段。他再作比對分析,發現這三部作品的情殺橋段出現了變奏,而《迷失幸運兒》沒有以往抹之不去的罪惡感,罪犯終被命運懲罰。 (閱讀更多)
在香港談詩,我們談的其實是甚麼?——《詩》影評
午後,一列小火車試探地向前發動,或許莽莽撞向牆壁,又或許引起一些注意。紀錄片《詩》裡最富詩意的隱喻,來自幾分童稚——詩人廖偉棠害羞的兒子Marcus,對正在拍攝的爸爸感到好奇,以車代人率先發出探問。這列被笑言為「超現實」的玩具火車,其實也在導演許鞍華手裡,輕輕推向觀眾。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