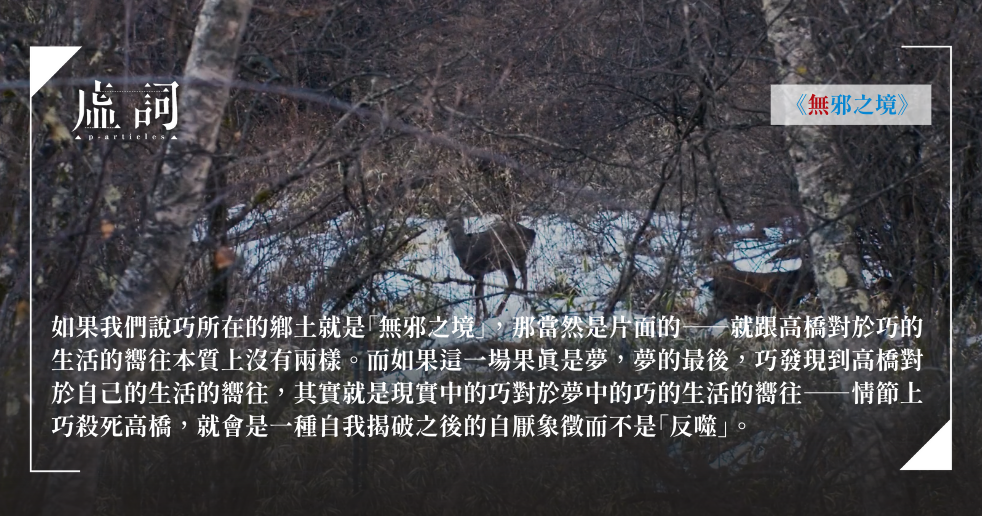半箭之鹿——巧——高橋:關於《無邪之境》的兩個問題
不少評論都已經通過資本、自然、溝通、暴力等關鍵詞來理解過《無邪之境》(悪は存在しない,2023)。這部電影最耐人尋味的地方莫過於其結局——我們當然可以借助資本、自然、溝通、暴力等自情節中萃取出來的關鍵詞來理解結局的象徵意義——也就是電影作者安排巧(大美賀均飾)殺死高橋(小坂竜士飾)的「動機」(——肯定是為了表達一些甚麼,所以才要把結局安排得那麼莫名其妙的吧!),不過,似乎很少評論從「反噬」以外、情節本身來理解結局——也就是說,巧的殺機似乎缺乏動機。
總之,結局是一個問題;“does evil exist” 是另一個問題。似乎,一種比較廣為接受的說法是,邪惡在自然不存在,存在在人那邊。資本(及其相關、鄰近概念,現代、文明、工業、消費⋯⋯)與自然(原始、天然⋯⋯)對立,前者入侵「無邪之境」,溝通(談判)失敗,於是訴諸暴力——又或者,換個中性點的說法——暴力發生,以半箭之鹿/巧為執事——這種善惡無分、因果自負的暴力,就是所謂「反噬」。
巧說鹿不會襲擊人,除非是半箭之鹿,走投無路,才會有人受襲。受襲的人大概(在這件事上)是無辜的吧——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會偏向覺得鹿的行為算不上惡。巧與半箭之鹿之間、在象徵層面幾乎可以畫上等號——他意圖(或企圖)殺死高橋,就是「半箭之鹿的逆襲」(?)——這算是惡嗎?好像不能不算吧?他既不是「血統純正」的「原居者」(一方面,「血統純正」並非不辯自明,另一方面,即使是又怎樣?),又不是野生動物,他是個人,而高橋又多少有點無辜,就算不無辜也罪不至死吧。而如果半箭之鹿的逆襲無邪、巧的襲擊有惡,那「資本/邪惡—自然/無邪」這樣的二元對立關係還是那麼不辯自明的嗎?(還有,高橋被「反噬」,他的工作伙伴黛[渋谷采郁飾]卻未遭波及,為甚麼呢?又或者,這表示甚麼呢?)
總之,以上就是《無邪之境》的兩個問題了。本文試圖在兼顧到情節的情況下,給出讓兩個問題都能自圓其說的解讀。友人說也許,只是作者沒有透過映畫把一切交代清楚、沒有把該展開的都展開——也許是這樣吧,那樣,以下就是縫罅的填充,形狀不規則、有沙石氣泡,也是誠不得已。
1. 空鏡
在我看來,電影的最後幾組鏡頭耐人尋味,電影的第一個鏡頭也是——為甚麼要花那麼長的時間拍天空森林呢?跟幾位朋友說起,都說自己差點要睡著了。我也是。還好有咖啡。儘管整部電影基本上都不快,但第一個鏡頭也未免、還是、顯得緩慢。這樣對待第一個鏡頭最先讓我想到Kelly Reichardt,但在她的電影裡至少我可以期待一下,這列車廂過了這一鏡就結束了(First Cow, 2019),又或者,這條船過了這一鏡就結束了(Certain Women, 2016)。天空森林,沒一點變化,好像它是存心讓觀眾睡著一樣(然後再用樂音的嘎然而止來「嚇醒」你們)。
難道,第一鏡是進入無邪之境(where evil does not exist)的路徑?不過,如果「無邪之境」果真是一個境域,它的疆界落在哪裡?(這就牽涉到「第二個問題」了)而且無論是日語還是英語片名,「無邪」就是「無邪」,都沒有境域的意味。雖然第一個鏡頭的時間真有夠長的,我還是沒能想出足夠合理的結論。
直到諮詢會上,巧說營地的化糞池會污染到井。
2. 井、境、本我
這一節只是某種啟發,而不是電影解讀本身——熟悉村上春樹,就知道村上春樹的小說裡總是有井,《聽風的歌》裡的火星的井、《挪威的森林》裡的草原的井、《發條鳥年代記》裡的乾涸的井⋯⋯等等。而有一種說法是,井老是常出現,是因為日語裡的井跟「イド」(精神分析裡的 “id”,本我)同音。
營地的化糞池會污染到井/id,這可以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有「無邪之境」,id就是了——無善無惡,它就只是生的需求與欲望,libido在那裡如水流動——《發條鳥年代記》中的水象徵了生命、命運;〈荒原〉(T. S. Eliot, The Waste Land)裡沒有水,表示沒有生機、希望。
無邪之境/井是地下水所在之處——地下水至清至純,是物,但又是生命,而沒有生命的惡意,流動靜止順勢幾道,是以無邪。
不過對村民而言,污染到井本身也許並不是問題,問題是水往低處流,流到村民這邊,這才是問題,與此情節對應的象徵意義,是id裡面本該秘而不宣的欲望外顯為與善相左的惡行——比如殺人想像的付諸實行。惡行在甚麼時候會發生呢?比如是ego(自我)鬆懈下來的時候,比如喝醉,比如入睡。
3. 入睡
循此,在我看來,第一鏡可能存在的潛在意義就是——那是一個把ego「關掉」的「儀式」。所謂「儀式」,在此是一種意圖的演示:祭祀不是亡靈一定收到,禱祈不是神明一定聽到,聽到不一定給你回應,回應也不一定是答應。所以我沒有真的睡著,電影也其實不是意圖讓觀眾睡著,而是演示出「讓觀眾睡著」的意圖。也就是說,暗示了電影其實是發生在「關掉」ego之後——也就是夢。
「關掉」的ego就是巧的ego。
這樣的話,結局的莫名其妙就可以理解了——因為夢本來就莫名其妙。它的價值除了在有趣如仙境(Wonderland)之外,就是對象徵和隱喻的分析與判讀——這樣的話,巧的行兇就沒有追究動機的必要了。
第一鏡就是躺卧的視角。
4. 妻、花、高橋
夢境是不能如願的欲望如願的場所。
T同學說不知道為甚麼要兩次出現相框裡一家三口的全家福,我說不知道為甚麼巧兩次忘了去接女兒。好像有一種說法是,巧的妻死於肺炎,而忘記接女兒,是肺炎的後遺症。不過,如果真的曾存在一個死去的母親,為甚麼女兒沒有一點憂傷?
我把妻所在的相框理解為現實滲入夢境的窗口,像《盜夢空間》(Inception, 2010)裡Mal(Marion Cotillard飾)在Cobb(Leonardo DiCaprio飾)的夢中閃現一樣。從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邏輯看來,可以是,其實巧的妻根本沒死(還有可能她「此時」就睡在巧身邊),而女兒跟妻要好多於跟巧要好,於是在夢中,巧(的id)讓妻死去,家就成了自己跟女兒獨處的空間了。巧沉默寡言,電影中並不見他特別想跟女兒親近——這一點大概是貼近現實的,在夢中,女兒會親暱地給巧餵吃的——你礙著我畫畫了,他卻這樣對女兒說。
即使如此,女兒仍意願與他親近。他希求女兒對自己的愛,這就是他的欲望了吧——是單向的、無需付出和維繫的愛(沒有要指出他自私的意思,畢竟只是夢)。因此,他總是忘了去接女兒。
再提一個更「沙石氣泡」的假設——巧其實就是「高橋」。夢醒時分,他可能會發現自己(的妻沒有死,以及)蘧蘧然與高橋沒有兩樣——他並沒有住在山林鹿道,而是跟高橋一樣,住在東京(搞不好高橋就是他的鄰居、同事甚麼的),討厭工作,希求返璞。
這個夢一次過滿足了巧的兩個願望——親近女兒,以及親近自然、鄉土。
5. 自然、鄉土
親近自然、鄉土,這個願望尋常、合理之至,「隨意春芳歇」——城市有城市的惡意,鄉土有鄉土的純樸——
也有鄉土不同於城市的惡意。喜歡《水葬》(蘇朗欣,2020)的L同學說看《無邪之境》想到《水葬》,他說《水葬》讓我想到最近讀泉鏡花的《夜叉池》(夜叉ヶ池)。《水葬》中的「原居者」是善嗎?た們的惡跟城市的惡如出一轍。《夜叉池》裡的村民難道不可惡得教人欲除之而後快?「官方」的西門豹來到「地方」,揭發出「河伯娶婦」(《史記.滑稽列傳》)的惡,把巫嫗、三老投之河中,這是文明對於原始、愚昧無知的折服。難道外來的就必然是入侵,而「原居者」的必然是無邪?
上舉的三個例子,都有水和女性。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認為,人類對於自然的壓榨實際上出於與男性壓迫女性相同的邏輯。高橋說想結婚,結婚之後就有人照顧了,現在太寂寞,這跟他希望住到鄉下的動機一樣,是出於對自身現狀的不滿,而伴侶也好,自然、鄉土也罷,都是他試圖滿足自身願望的「工具」。我想,這也許就能理解為甚麼高橋要死而黛能被「放過」——黛被植物刺傷了手,那是一道標記救贖的「聖痕」(stigmata)。
因此,如果我們說巧所在的鄉土就是「無邪之境」,那當然是片面的——就跟高橋對於巧的生活的嚮往本質上沒有兩樣。而如果這一場果真是夢,夢的最後,巧發現到高橋對於自己的生活的嚮往,其實就是現實中的巧對於夢中的巧的生活的嚮往——情節上巧殺死高橋,就會是一種自我揭破之後的自厭象徵而不是「反噬」——只有水噬才可以天地不仁、善惡無分地奪取生命。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