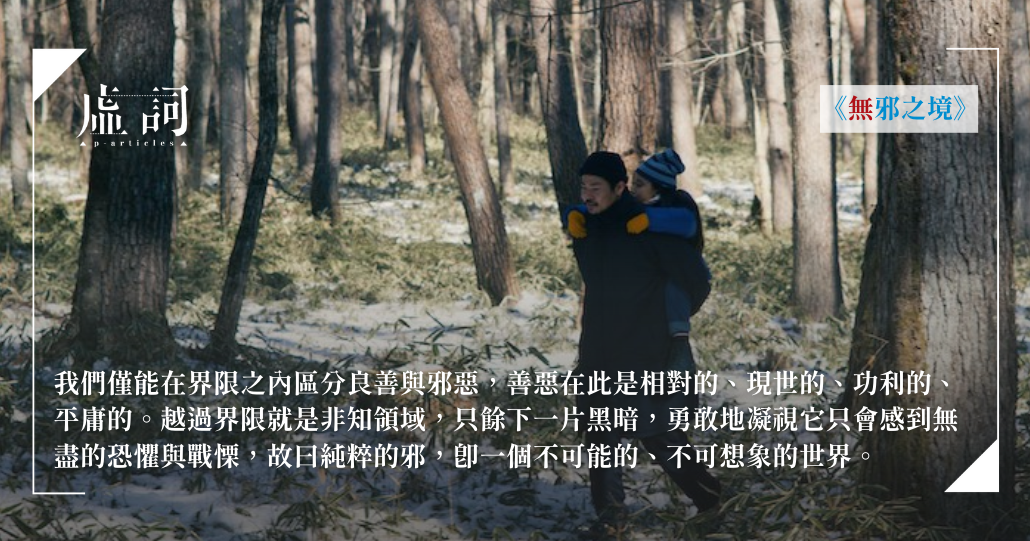論《無邪之境》——論人類命運:原初、辯證與辯證的終結
影評 | by 海鹽 | 2024-02-01
無邊的樹林、詭秘的音樂、自然的迴聲,默不作聲的生命。
建構出一個靜態的場域──原初自然。對於我們這些「現代人」,一切都是神祕而陌生。於是,我們焦急地向原初自然的場境投擲無數疑問,試圖尋求理性解釋,好讓它在我們的認知體系裡覓得一席之地,但得到的卻只有沉默。不可理解與無以名狀,使我們感到挫敗與鬱悶。
直至原初自然的人類住民出現,我們找到了一絲線索,彷彿在迷宮中拾到一幅殘缺的地圖,在陌生的黑暗中有了些少方向。於是,我們緊隨着那些住民的目光,理解本來全然陌生的自然。
在那裡,沒有語言而只有聲音、沒有食物與禮物而只有自然的恩賜、沒有建築與造物而只有同一片土地。於是,沒有人、動物與自然的區分,生命即自然。所有生命棲居於土地上,一切都按着土地的原初時間與原初秩序緊密交織、共生與依存,沒有多而只有一,一切環環相扣,沒有分拆來理解的可能。這是一個靜態封閉的無分別整體,獨立自存,沒有善惡之分,沒有認知的可能,人們無法為它命名,就像一只貓咪從出生起就生於一個狹窄的環境,從沒有外出的經歷,便不能知道室內和室外的區分,這狹窄的環境對牠而言,就是一個整全的靜態世界。
直至資本世界的入侵──一個之於原初世界的反題──開啟了歷史辯證機器,把原初世界捲入動態的運動與衝突,「原初世界」方有被認知及被命名的可能。換言之,我們所稱的「原初世界」是在「資本世界」(他者)對其侵略時才首次顯現,「原初世界」才能擁有自我意識,從而辨認自身、命名自己,我們才能區分兩套世界的符號秩序。
原初與資本:秩序、衝突與暴力
原初世界裡頭,人們閒適安穩地過着詩意的田園生活,安定於自己的能力與身份階序。他們擁有美感化的身體,非語言文字的去感受着大自然裡的一切細節,而沒有絲毫功利的痕跡:傾聽着流水聲、觸摸着樹木、品嘗着香料、步行於叢林之間,瞧着被枝椏修飾的天空。自然在他們的世界裡被賦予神聖的地位,生活於是圍繞着「山神」與「水神」而展開,住民與自然成為密不可分的共同體:小女孩將撿拾到的羽毛化成禮物送給村中長老、本來在東京開店的鳥冬店店主因甜美的水而遷居於此。
然而,資本世界卻是一個體系,企圖將一切人事物商品化,為所有東西標示價錢,使一切失卻內涵而變得面目模糊,貨幣成為衡量萬物的尺度──成為上帝,接着,理性文字作為上帝的奴僕,將所見的壓縮為上帝可理解的。資本體系的信徒就是盡其所能進行交換、交易、投資,以累積資本,最終接近上帝,甚或成為上帝。這種商品化的內在驅力注定使資本世界不停向外擴張,將不同事物轉化為「商機」,好讓資本體系理解及吸納,成為其一部份。這是一個西方現代性的計劃。
資本世界的爪牙終於要伸向原初世界,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勢在村莊召開「諮詢大會」──當代的戰爭號角──試圖開發及吸納原初世界,用錢與商機作為「招徠」,呼籲居民支持。這是一套與原初世界截然不同的,甚至可稱為異質的符號秩序,根本不能被資本世界的符號所理解,於是看似溫和的「雙贏的方案」就是一種傲慢與暴力,一場單方面掠奪。意圖之明顯,換來的當然是原初世界的否定,在「諮詢大會」裡,居民群起反對,或動之以情,或說之以理(用資本世界的語言),或向資本世界的使者大聲疾呼。
隱蔽的暴力:理解之不可能
資本世界的使者們遭遇挫折,他們被居民嚴肅而不屑的臉相深深震撼了,他們不單發現自己的傲慢與片面,並且挖掘到自己為適應資本世界而早早埋葬了的人性面向。於是,他們在車上唸唸有詞,哀悼着那個早已死去的自己,在自我的墓碑前懺悔。
於是,他們把車子再次駛回原初世界,試圖理解原初世界的秩序,並為自己贖罪。可是,他們是貪心的,沒有殺死功利的身體,不願意殺死資本世界的自我,那麼,他們是不可能在原初世界裡復活的。最終,他們心中的「試圖理解」毋寧是虛偽而一廂情願,他們期盼的只是在原初世界裡工作,而不是勞動與生活。他們的行為彷如那些自以為是的大學生,沒有放下一切的覺悟及行動,然後繼續維持着自己的優勢地位,去短暫扮演露宿者,體驗一個月的露宿者「工作」──訓街,就對露宿者的生活侃侃而談,用巴塔耶話語來批評,他們只是在「設想一種沒有焦慮感的純粹的智力遊戲,這種設想是毫無意義」,無疑是一種自我欺騙。
打着「悔疚」、「理解」及「尋回自我」的旗號進入原初世界,卻沒有徹底放棄自我的覺悟,在原初世界以及其住民的眼裡,只是一個用來掩飾自己暴力的藉口,他們只是在滿足自己的甚麼都想要體驗的慾望;且在他們掌握更多原初世界的資料後,便能更有效的把原初世界整合進資本世界,如同早期的人類學家,打着學術的旗號融入殖民地的生活,以使宗主國能對殖民地進行更有效的統治。而原初世界則按照他們自欺的程度作出懲罰,輕則被叢林的尖刺所傷,重則喪失性命,他們為自己對自然所施加的隱蔽暴力,付出了代價。
辯證的終結:自然的反撲及棄發展的呼嘯
電影裡充滿了對立的隱喻。
主角的女兒在整部電影裡的大多數時候都是沉默的;而主角所敘述的鹿,在被單獨獵捕時,或者看見自然世界的住民時,都是沉默的。筆者認為,女兒與鹿都象徵着自然本身及其中的生命,而主角就是熟悉自然世界運作的預言家。明顯的,那兩個資本世界的使者,就象徵着資本世界的人類;使者們深入自然世界的每一步,則象徵人類發展自然的步伐。
在電影臨近尾聲,使者帶着複雜而又簡單的意圖闖入自然世界,而不再像第一次來訪般僅停留在自然的入口──村莊。隨着使者的深入,主角警告他們說,鹿會在原初世界被開發後變得燥動或具攻擊性,這意味着一個預言:資本世界的入侵會使自然世界變得失序,不可預料,且有機會對其作出反撲。使者好像聽不懂勸阻,或因無知而置之不理,在徑直邁向主角家的路程上就受了點傷,意味着主角的預言正在靈驗,自然世界會隨着深入的程度作出相應的反撲;最後,一位使者一鼓腦兒地再往前走,深入到鹿的水源時,大霧臨離,鹿對其作出深沉的凝視,而主角的女兒倒地並流下鼻血,主角於是上前勒死使者,這象徵着資本世界的入侵已接近自然世界的生命根源,使自然世界大傷元氣,而資本世界的人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用他們的生命進行獻祭。畢竟兩個世界本是同一的,只是資本世界的人未曾意識到罷了。於此,資本世界消逝並與自然世界重新歸一,反題的消失意味着辯證運動的終結,善惡的劃分消失了,自然世界復歸平靜。人類的生命獻祭,使自然復歸神聖與潔淨。
筆者認為,電影向觀眾展示發展邏輯的極致,終會導致兩敗俱傷的惡果,自然還可因此而重新,人類卻會因此而遭到重創,於是作者渴望人們選擇另一路,懂得及時把發展剎停──棄發展,即放棄經濟發展作為目的之邏輯。如同那個因受輕傷而止步,未有前往鹿的源泉的那位使者,她停在屋裡待着,便瞧見與另一位使者截然不同的世界,那裡只有美麗的曙光,她凝視着那道光,不能移開視線,驚歎震撼於當中的希望,或曰絕望。
我們僅能在界限之內區分良善與邪惡,善惡在此是相對的、現世的、功利的、平庸的。越過界限就是非知領域,只餘下一片黑暗,勇敢地凝視它只會感到無盡的恐懼與戰慄,故曰純粹的邪,即一個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世界。
只有邪,故無邪。棄發展的世界,或資本世界的終結之地,就是無邪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