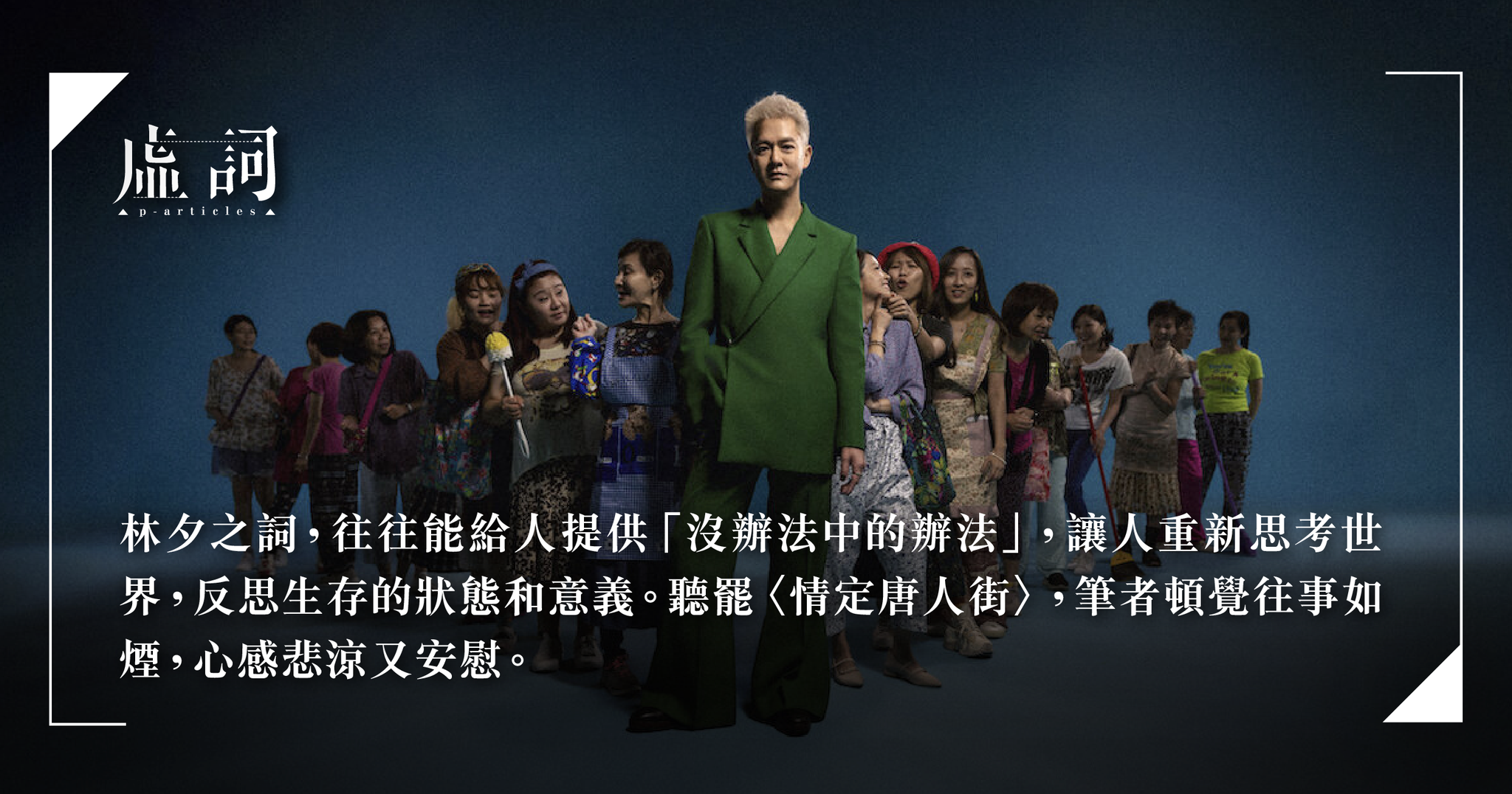想像的永恆避世島——談林夕〈情定唐人街〉
哪個時勢能沒有歌?近年,書寫移民的歌詞甚多,諸如〈留下來的人〉、〈Ciao〉、〈On My Way〉等,統統記錄時代,與大眾同泣。〈情定唐人街〉是林夕在2023年的第二首作品,大抵亦是他近年第一首以移民為主題的歌曲。筆者並非詞評人,但聽着這闋怪誕、歡快、悲涼又充滿玩味的歌曲時,心有戚戚焉,故聊以本文輕談隨想,冀能稍解愁思。
紅袖添香要安靜繁榮
遊蕩一街已驚擾全城
能讓我們長留在這家園
要牽手報讀家政
正歌甫起,先有「紅袖添香」之典,意思是有年輕女子伴讀,非指艷福無邊,乃指雅致、溫馨的生活。首二句中,人們不必到處「遊蕩」,只要「安靜」過活,就能得到「繁榮」,這彷彿帶有「適宜留在舒適居所」和「歲月靜好便好」的暗示。然而,若以暗黑角度觀之,則或有隱喻:「添香」有延續之意,詞中不少「紅袖」之人來「添香」,高姿態地「遊蕩」和「驚擾全城」,正是為了讓「安靜繁榮」延續下去。(但「安靜」是否就等於「繁榮」?明明「安定」二字也協音,且較常與「繁榮」組成短語,詞人此處偏偏用與「繁榮」較有衝突的「安靜」,予人「無聲勝有聲」和「安靜即繁榮」之感,難道有弦外之音?)那麼,到底「家園」指留守地抑或移居地?視乎採用何種解讀吧。但不論怎解讀,若我們選擇於自己所身處的這片「家園」活下去,便必須「報讀家政」,即學習好好照顧自己。
情像酒家靠仿舊馳名
人像新聞有幾多長青
惟願我們名字像對春聯
對得久遠便相稱
接下來,詞人再用「舊」和「新」,以及「馳名」和「不長青」作對比。「人像新聞有幾多長青」似帶反問語氣,說明人生在世若寄塵,昔日曾登上新聞的碩大事情,又或甚麼偉績和崇高理想,浪潮過後,原來只是滄海一粟。縱然可惜,但事已至此,倒不如延續深情,開一間遠近馳名的「仿舊酒家」吧。且讓我們製造一個集體回憶的儲存空間,興建一個虛幻的理想國,此或更能流芳千古。至於「惟願我們名字像對春聯」,「惟願」一詞雖略帶無可奈何之意,但「春聯」是精巧又吉祥之物,人把「名字」寫於其上,彷彿便能互相遙望並祝福彼此。這更說明「我們」雖有距離,但又平行地走着——物理上的「久遠」,總無阻我們內心「相稱」,無礙我們並駕齊驅。由是,本節或已暗示「唐人街」未必真實存在,但卻美好非常。
混世不知有秦漢
只聽過秦漢
映畫翻映再映
歲月於這裏暫停(你若早知道劇情)
蝸居中寫食經(我也擅長算命)
副歌部分,林夕真正帶領聽眾進入新建的避世島。詞中,「秦漢」二字出現了兩次,尤其引人注目。觀乎古典文學,〈桃花源記〉或能作副歌之注腳,陶潛曾這樣寫桃花源內的人:「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仔細一想,詞中的「唐人街」豈不正是今人夢寐的「桃花源」嗎?由此可見,詞中「秦漢」借代動盪歲月,「混世」則作「混沌的世界」解(這裏「混沌」一詞並無任何褒貶),所指正是這片從零開始的新世界。
承上所述,這節歌詞似乎在談理想世界的人對歷史的認識。詞中用「不知」和「聽過」,前者指不了解,後者指略有耳聞,皆反映了「島民」的後代其實未必親眼目睹歷史,上代的光輝日子只能憑口耳相傳。至於看「映畫」,筆者想起了林夕在〈你們的幸福〉(2011)中「牽手看偶像連續劇哭哭笑笑/輕輕鬆鬆」的畫面。兩首詞作裏,主角所處之地有異,但情境卻稍有相像:人們且看大城小事,不看小城大事,那似乎是種麻木所帶來的幸福——有時,麻木是為了避免更深的傷害。
然而,「看映畫」是否完全指那種由麻木而生的幸福?未必然。若作另一解讀,「映畫」也可包括史實紀錄,此時,重播映畫遂成傳頌歷史之法。事過境遷,雖然避世島上世世代代的人只聽過「秦漢」,沒親身經歷;但在那裏,史實能映於眾,也未嘗不是好事。當然,聽眾亦未嘗不可將「映畫翻映再映」聯想成人們重播創傷的行為。若作此解,後人把歷史當「睇戲咁睇」,是否在賞鑑舊人之痛?抑或在學習以史為鑑,練習不要忘記?也許筆者想太多了,不過「你亦早知道劇情」和「我也擅長算命」,其實又足見「我們」深諳歷史,同時深知不躲進避世島會有怎樣的命運和結局。故這節看似輕鬆又風騷,實則喜中帶悲。
不但如是,上文論及「秦漢」之意時,筆者還浮想聯翩,竟赫然想起了王昌齡的〈出塞二首(其一)〉:「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若用之以解讀〈情定唐人街〉,則更見「秦漢」一語的戰爭感。而讀者亦不難進一步推想:避世島上的人不知有「秦漢」,不代表世間的戰火現已停止——真正的戰事不一定要明刀明槍。更甚者,詩中的「人未還」,亦彷彿在訴說着一些未遂的理想,想念着一些離去了的人。不過此際再三懷緬,亦空餘感慨,「秦漢」誠然已過,但故人一去兮不復還⋯⋯那麼「龍城飛將」又何在?或已退隱島上,或已消失無蹤,也不便多說了。
世道崩壞,惟有自救。避世島裏歲月暫停,一切停在最燦爛的瞬間,這不失為絕佳的精神寄託。詞中「蝸居」二字指窄小的居室,鮮用以形容外地的空間,這使筆者感疑惑:到底「寫食經」的人是留守者抑或移居者?也許兩者皆是,因「蝸居」雖常指物理上的生活空間,但聯繫至心靈格局亦無不可:內心堡壘雖小,但人在其中,也能看得遠大,活得自在。至於「食經」,此語顯然比「食譜」更勝一籌,突出了人們愛烹飪成痴(非貶義),將主歌中「報讀家政」的生活態度發揮到極致。與〈你們的幸福〉中「飲飽吃醉是容易極的快樂」的生活相比,「寫食經」乃是一種鑽研,生活感更強,層次亦較高。它是人們在新世界慢慢適應過來的證明,而這新世界,可以是留守地、移居地,甚或想像裏的「唐人街」。不同人居於不同地方,卻能過着相似的生活,此令筆者覺得這句(甚至這節)甚具畫面感,宛若一個似遠還近的多重鏡像。
重拾不變心情
重蹈不變風情
如外邊風聲(秋風)吹不應
應該繼續高興(春風滿面圍爐)
(來做春茗)
「外邊風聲吹不應」之句,無疑深化了避世島隱密、安全但被孤立的形象。詞云「不應」,或指風吹草動難以察覺,島民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風聲、雨聲不再聲聲入耳(由外至內),同時可指:即使偶爾有人重拾雄心壯志,外面也無人和應(由內至外)。當然詞中的「不應」不怎負面,因不論好壞,人們仍可在避世島重構各種「不變」,定格當初的快樂和風情,歡天喜地。(此刻筆者又想,黃偉文填詞的〈隱形遊樂場〉(2023)中,人們同樣在建造「夢幻」(「置身廢城/仍可建造人類最夢幻剎那」),但這「夢幻」的長度只有「剎那」,而〈情定唐人街〉的「夢幻」卻「永恆不變」。如此對比,可見兩首詞作的對讀空間甚大,值得聽者探究。)
至於「應該繼續高興」,則令筆者想起潘源良填詞的〈今天應該很高興〉(1988)。該詞副歌云「今天應該很高興/今天應該很溫暖/只要願幻想彼此仍在面前」,哀思全出。兩首作品同寫離散,但角度和感情卻大相逕庭:林夕似用移居者的角度書寫(移居地是想像的「唐人街」),當中「應該」指「很應該」,語氣堅定,展望着永恆不變之快樂;潘源良則似用留守者的角度書寫,大多憶往,慨嘆良朋無法聚首,當中「應該」既帶「理應(但不能如願)」之意,又有「相信會(很高興和很溫暖)」之意。(當然,這種美好的「相信」只建基於幻想,其實更添悲哀。)雖說前者樂而後者悲,但潘源良所說的「幻想」,難道不似林夕筆下快樂的「唐人街」嗎?
另外,第二次副歌中「風聲不應」改為「秋風不應」,與「春風滿面」形成強烈對比,值得留意。所謂「秋風秋雨愁煞人」,但避世島卻一點「秋風」也不入,反而處處春意:詞中人物「春風滿面」,聚首一堂辦「春茗」,甚至名字也像「春聯」般相稱。由此可見,現世中各散東西之人,其心靈總能在想像裏的「唐人街」再遇,一起「圍爐」,而那裏更是忘憂之處,充滿「春」之生機。然而,這種「新春」是否真的能使人重生?誠堪聽者深思。
情是金曲你早是名伶
情定一生會一世時興
來讓我們停在上個紀元
你想心醉便飲勝
筆者認為此詞的時空跨度甚大,因之前幾節歌詞多述空間,這節則多談時間:「金曲」必經歲月淘洗而留下,「名伶」必定是有一定年資而站得穩腳的戲曲演員,而「上個紀元」指上個時代,故此段談過去、現在與未來,即是談永恆。由於情像「金曲」般永垂不朽,故這一刻,八、九十年代移居避世島的人已是「名伶」;若前瞻未來廿載,這刻移居避世島的人又成了一代「名伶」。由是觀之,隨着年月,人們會視避世島為故鄉,在這異地「情定一生」,落地生根。但如此之說,到底是喜是悲?也許喜大於悲,至少在此你能及時行樂,「古老當時興」,想「心醉」便可「飲勝」。何況,在這道美好的「唐人街」,舊情永不退,將會流行一世,流行生生世世。
有污清聽便不聽
還在唱著情共永
再不驚我們轉性
最後一節裏,「情共永」一語借代「情是金曲你早是名伶」的「金曲」,再次強調了避世島之永恆。另一邊廂,此語又見於潘源良填詞的〈半夢半醒〉(1988)中「明晨無夢也可情共永」一句。〈半夢半醒〉所談雖是愛情,但這小句,又正好呼應着〈情定唐人街〉中,人們安康舒泰的生活情態(劫後餘生)。所謂「好夢由來最易醒」,然而,無夢也可情共永。憑着腦海裏的一道「唐人街」,縱使夢醒,我們也能在另一維度繼續航程。
離散的人,總會在更高的地方相遇。詞末,詞人彷彿提醒我們應努力找尋屬於自己的「唐人街」,因為這永恆的避世島,就是我們一直夢寐的、集體的心之安處——找到了,自然能「情定」;情定了,自然不怕「轉性」。一直以來,唐人街是個文化符號:在陌生(或不再熟悉)的地方重新構建往事,延續舊情。故筆者認為,本詞的「唐人街」未必真實存在,但那的確是一個世外桃源,是我們各自在腦海用心「倒模」的複製品——只要我們擁有相同的回憶和想像,在那裏,我們便會再遇,更能永續舊情。
不過,永續舊情是否最理想?倘抽離一點看,全詞所說未免過於美好,反而令人細思極恐。常言「變幻原是永恆」,惟「唐人街」絲毫沒有變易,恰若一盞永遠長開的燈。所謂「不變」之下,其實潛藏悲涼。詞人云「有污清聽便不聽」,這雖不像〈你們的幸福〉中「愛思索便會福薄」那種程度的麻木(從沒清醒過的無知),也許較像一種不麻木但也不激憤的生活態度;但是,這種態度似乎未算睿智,亦非舉重若輕。
以「情像金曲你早是名伶」為例,「金曲」傳頌萬世而永不滅,「你」則成了名伶而永不逝,此見避世島裏好像沒時間概念,一切彷彿「上咗神枱」,不來也不去。又如「唐人街」是尋夢者的永恆樂園,裏面馬照跑舞照跳,是永恆的「春天」,悲哀之「秋風」永遠吹不應,一切全向「快樂」傾斜。但仔細想想,這真是我們的追求嗎?有時候,我們大抵忘了「不變」比「變」更可怖:「烏托邦」本來就指美好但無法實現的理想世界,只是我們的靈魂不甘心死去,又不願在現實生存而已。說白了,在這道想像的「唐人街」,當初求「變」之人只求「不變」,人人沉醉過去,再沒有哀愁,再沒有死亡,只有永不停止、不分晝夜的狂歡——這其實是一片極樂世界,而我們渾然不知,我們處於彌留狀態。
近年林夕作品產量不算多,但每首作品,均承載着深意。由〈最後的信仰〉、〈你好嗎〉至〈情定唐人街〉,林夕彷彿與大眾同呼同吸、休戚與共:先是結伴撐過飄搖時期,祝你心理愉快;繼而一起堅持活下去,好好療傷,相信微光;最後提醒你拾回自己,好好照顧自己,以心態決定境界,並一同約定於想像裏的烏托邦再聚。林夕之詞,往往能給人提供「沒辦法中的辦法」,讓人重新思考世界,反思生存的狀態和意義。聽罷〈情定唐人街〉,筆者頓覺往事如煙,心感悲涼又安慰。雖然「唐人街」是似樂實悲的虛幻國度,但若失散的人終在高於現實的地方再次連結,它大概已是那個最佳的心靈落腳點了⋯⋯
生與死之間,我們無路可走,只好穿過狹縫,躲進桃花源。這道想像出來的「唐人街」,正是每一個人翹首以盼的避世島,正是每一個人心心念念的故鄉;當你長留其中,與其再問「何時何方何模樣」,不如直說「此心安處是吾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