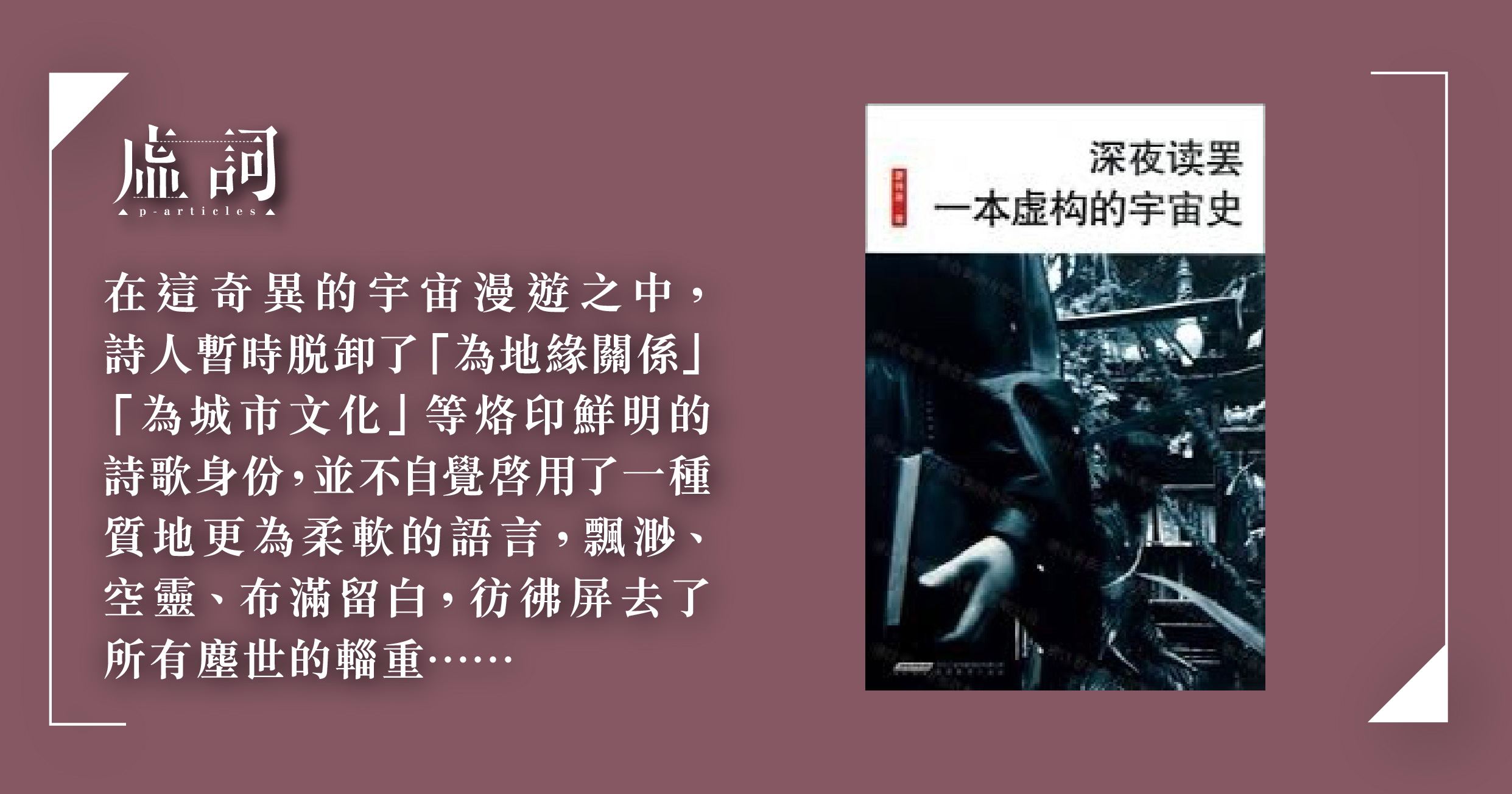時空、身體與「玫瑰小史」——廖偉棠《深夜讀罷一本虛構的宇宙史》細讀
書評 | by 李曉 | 2023-01-14
一秒鐘後我們灰飛煙滅,
無所謂忘記,無所謂記起;
當一千年前在巴格達,一個阿拉伯人
低下他焦灼的額頭貼近我的胸膛——
有什麼東西碎了,我聽見那嘆息一樣的聲音。
合上眼我就飄浮在那些肥皂泡星辰之間,
它們並不存在——就像這地球;
然而總有土壤無中生有,供這些文字
和憂鬱一併淤漫。
這黑暗的爪子扼扣在我肩上——這星光
把一具宇宙的玻璃身軀劃傷,
塵世的王垂下原子頭冠冕。我剝蝕:
在圖書館的廊柱上吹過,火星的猩紅風。
一個人影漸漸走出我的身體——我的虛構,
他旋轉在一個塵埃錯雜的角落,
彷彿他是宇宙的精神。荊棘布滿
大千世界,我的一隻手指的邊緣。
彷彿一個虛空就來源於這手指的一次觸碰。
沙崙的玫瑰重疊萌生,我拉下這沙的頭巾,
一個人影開始說話,那是引擎輕轉的歌聲:
無所謂驅動,無所謂明暗,
一秒鐘以後我們相愛,失散,重新找尋。
《深夜讀罷一本虛構的宇宙史》,廖偉棠
在廖偉棠總結性的詩集《半夜待雪喊我》中,寫於2001年的《深夜讀罷一本虛構的宇宙史》被收錄至輯一部分,屬於詩人早期的代表作。俯覽全詩,首尾對稱式的設計遙相呼應,似有一種大巧若拙的周全趴伏在直陳的語言背後:「一秒鐘後我們灰飛煙滅/無所謂忘記,無所謂記起」「無所謂驅動,無所謂明暗/一秒鐘以後我們相愛,失散,重新找尋」,詩人藉助語序的顛倒,在視覺上營造出一股上下圍攏之勢,彼此咬合如《包法利夫人》中男主角的兩次出場,分別安排在開端與結局,用其寡淡無望的生活封堵所有浪漫的願景。這牢靠的框架結構既留足了思維漫遊的篇幅,也為想象設下界碑,彷彿一雙擎住行腳的手,避免旅程因過於遙遠而發生偏移。同時,考慮到這兩處「一秒鐘」在形式上的相似,我們不妨將其重疊看待,那麼間隔之間的內容便可視為短短一秒當中詩人由出離到復歸的「漫遊」過程——時間尺度的壓縮雖造成了一定的言說壓力,卻也為詩意空間的拓展帶來可能。
事實上,廖偉棠本就是一位擅長將書寫推至「極境」後再「絕處逢生」的詩人,他的《一九二七年春,帕斯捷爾納克致茨維塔耶娃》便是一支復沓於苦寒雪夜的末世舞蹈,一個相遇瞬間的無數延伸;他也早在命題伊始就為本次書寫埋下險象,且這危機至少是雙重的:「史」與「宇宙」的勾聯分別從時之漫長、空之邈遠的意義上註定了範疇的不可窮盡,從何處落筆、至何時收束將成為挑戰;以「讀罷」這一完成式動作統攝於無垠的宇宙史前,預示着詩歌未必會單純從「閱讀」的內容或行為過程出發,其背後潛藏的主語「我」反卻具有強勢的介入性、導向性,那麼這樣一個實存之「我」及其所處的現實環境該如何內聚那浩瀚的虛構之力,並在有限的詩節中吐納均勻?針對前一重考驗,詩人採取了上述截斷式的約束策略,並開始着手構建自身與宇宙的互動關聯:
當一千年前在巴格達,一個阿拉伯人
低下他焦灼的額頭貼近我的胸膛——
有什麼東西碎了,我聽見那嘆息一樣的聲音。
注意,這是前一刻還困足於秒針針尖之上的詩人完成的一回精彩的躚躍,其冥思流動如牧童遙指,出乎意料地引向了巴格達的奇特情境,詩歌視野也隨之遼闊起來。從本質上看,無論是「一千年前」的溯洄、「一秒鐘後」的瞻望,抑或古文明之於現代文明的感召,促成這斗轉過程不致突兀的,仍舊是那反覆出現的「時空」關係,它經由語言織就、拉伸、變形,將現實世界中線性、三維的時空律令一一解放,供詩人更進一步馳騁於虛實之間。
因此,接下來的詩行無不呈露着狀態被動搖、存在被瓦解的跡象。「合上眼我就飄浮在那些肥皂泡星辰之間/它們並不存在——就像這地球/然而總有土壤無中生有,供這些文字/和憂鬱一併淤漫」,這部「虛構的宇宙史」對認知的「刷新」毋庸贅言,值得玩味的是,憑藉對漢語詩意天然的敏感,詩人在此作出了使語音、語義各自「獨立」的嘗試:「它們並不存在——就像這地球」「然而總有土壤無中生有」,音律上的相諧使這兩行銜接順暢,似具有天生的吸引力;而前者對存在之否認與後者的「無中生有」卻在意義上互相背離,於無序間脫胎出一股斥力——音義上的相吸相斥不僅使文本迸發磁鐵般的張力,還似乎模擬出了事物在「宇宙史」中的生存狀態。這狀態或可直接徵引詩人在本節末生造的詞語「淤漫」加以描述,介於厚重與輕盈之間、攀升與墜落之間、積聚與渙散之間——彷彿一種極境,在真空中充塞。
但詩人並無意於一場純然朝向虛空的冒險。以往,廖偉棠曾在多個場合談及對現實與虛構的看法:「我一直在嘗試做到,當我看現實的時候,我心裏有一個博爾赫斯的座標;然後當我看那些不存在的、那些虛構和那些幻想的時候,我心裏也要有一個惠特曼的座標把我拉住。」在這首宇宙詩中,其「若即若離」(廖偉棠語)的詩學觀念也未曾削減,尤其是當我們帶着檢驗的目的返回關照時,便會發覺詩人在開頭就已設下平衡虛實的支點:身體。
「低下他焦灼的額頭貼近我的胸膛」,身體在此處乍現又旋即偃息,因未及時延展而容易被讀者忽視。但自從首次現身,它就充當了類似「靈媒」的核心角色,令兩個相去甚遠的時空依靠「額頭」與「胸膛」發生交匯、交流。這門「沉默的語言」之於詩人的重要性在後續調度中得到深入顯現。
「這黑暗的爪子扼扣在我肩上——這星光/把一具宇宙的玻璃身軀劃傷/塵世的王垂下原子頭冠冕。我剝蝕/在圖書館的廊柱上吹過,火星的猩紅風」,行至此節,詩人已進入深度漫遊的狀態,選詞和構詞上更是不自覺流瀉出「以覺代知」的審美特色——比起知識性詞彙的鑲嵌,「黑暗」「星光」「火星」更像詩人信手從宇宙體表摘來,簡潔、素常(偶爾也略顯單薄),且並不打算通向更深處;其自身也未嘗執迷思維上的攀登,而是致力於將內在認知轉化為對外物的賦形,譬如肩膀被「黑暗的爪子扼扣」,通過肢體傳達夜深時無端的壓迫之感,以及隨後的「大千世界,我的一隻手指的邊緣/彷彿一個虛空就來源於這手指的一次觸碰」借指尖接觸溝通實虛,包括他在類似題材的《當我們坐在冥王星的冰塊旁哭泣》一詩中寫道:「如果我忘記你/就讓我的左手忘記我在你脣邊拾火的乾脆/就讓我的右手忘記你小腹的戒指」,都試圖用身體託載更多難以言狀的情緒,將調動官能體會的任務交付讀者,強調參與,並追求一種心有靈犀的默契。
但在詩人那裏,靈肉絕非始終合一,二者時有對峙、割裂,甚至彼此陌生,故而便有了第四節「一個人影漸漸走出我的身體——我的虛構/他旋轉在一個塵埃錯雜的角落/彷彿他是宇宙的精神」。早在先前調用表層感官時就可預料這一結果,詩人雖對身體無限器重、將其視作貫通自我與世界的樞紐,但在下一秒靈魂便出於某種感召,為融入宇宙而急於脫卸那同樣是由身體造成的隔膜。這長期存在的矛盾在廖偉棠近年寫就的《給肉身的留言》中展現得更為尖銳:「而你鮮豔無礙,入夜時你的射線凌亂不明/幾乎絆倒夢裏的我,當我嘗試盜取你的藏品」。
當詩歌徜徉於變動不居的時空、即將迎來尾聲之際,猝然開放的玫瑰突兀異常,璀璨異常:「沙崙的玫瑰重疊萌生,我拉下這沙的頭巾/一個人影開始說話,那是引擎輕轉的歌聲」。正像美國作家格特魯德·斯坦因在詩中所暗示的,「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僅僅是喊出事物的名字,就能喚起與之相連的所有意象和情感,這結晶了太多意義的景觀猶如一根引線,牽涉出半部有關玫瑰的文學小史。
這就不得不提及廖偉棠曾出版的同題讀書隨筆集,此詩正是作為卷首的序詩,被安放在了最為顯眼的位置。並且,他在封底介紹道:「這是對一個由蘭波、里爾克、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策蘭、凱魯亞克、切·格瓦拉、鮑勃·迪倫、勒克萊齊奧、特朗斯特羅姆等星宿組成的精神宇宙的導航圖。」至此,將視線最後一次移回詩歌開頭,那灰飛煙滅的「我們」正由含混逐漸明晰為詩人及其追憶的數位文學先師,他們身形重疊如玫瑰,彼此激盪,漫長地迴響;詩歌也因而見證了詩人面對和處理文明存在之焦灼的全部過程,由「剝蝕」至「萌發」,由「嘆息」至「歌聲」,精巧的結構最終閉合為環形;「無所謂驅動,無所謂明暗」一行的前移更令詩歌在語境的輪迴中完成了一種語勢上的推進,猶如博爾赫斯在《另一個人》中的自我對話:「等你到了我的年紀,你也會幾乎完全失明。你只能看見黃顏色和明暗。你不必擔心。逐漸失明並不是悲慘的事情。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將意義由遺忘之必然的灰心撥轉成了「重新找尋」之必然的和解。
在這奇異的宇宙漫遊之中,詩人暫時脫卸了「為地緣關係」「為城市文化」等烙印鮮明的詩歌身份,並不自覺啓用了一種質地更為柔軟的語言,飄渺、空靈、布滿留白,彷彿屏去了所有塵世的輜重,只凝神諦聽太古、玫瑰初綻與遠方文明的胎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