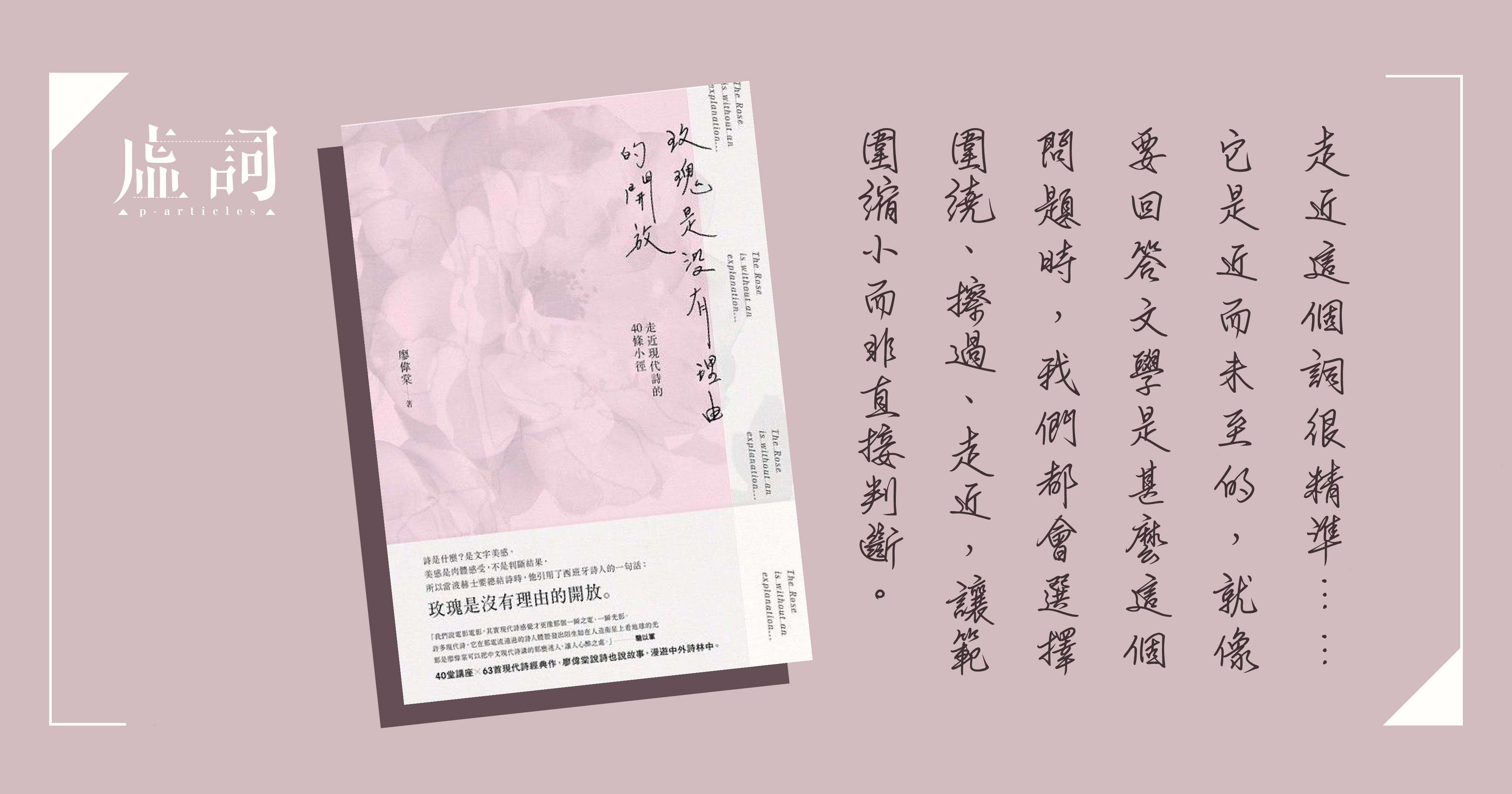走近而並非走進現代詩的分岔小徑——讀廖偉棠新書《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
由台灣新經典文化出版,廖偉棠於今年五月面世的演講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是一部賞析現代詩的文集。本書的副標題是「走近現代詩的40條小徑」,走近這個詞很精準,因為如果說了走進,會落入一種武斷的定義陷阱,強迫著回應「詩是甚麼」、「文學是甚麼」的龐大命題。因此,它是近而未至的,就像要回答文學是甚麼這個問題時,我們都會選擇圍繞、擦過、走近,讓範圍縮小而非直接判斷。
《玫瑰》一書原本是廖偉棠三年前的一個現代詩課程「詩意:關於新詩的三十種註腳」,後來擴寫結集成書。四十篇文章有時連貫,有時跳躍,看似即將建立體系,馬上又脫疆奔跑。比如說其中一章就寫道「這篇文字是特別寫的番外篇」,證明了書存在著一個「本番」。但本番在哪裡,是否就指原本的三十場講座?其實不能這樣理解,因為這四十條現代詩的小徑,都是一些用以理解現代詩的點,讀者自行連結成線與面,建立屬於我們對於現代詩的理解和體系。本番和番外,在於作者自己在思考這部演講集時哪些靠近核心,與我們讀者的排列未必相同。也不必非要相同,解讀的自由總是不需要理由的開放。
給新手讀者介紹甚麼是神秘的「詩意」
《玫瑰》是一本面向現代詩的新手讀者(如我)的入門讀物,如在書背上印刷的宣傳語句:「是一部最淺白親近人的詩歌導覽手冊」。其實它不淺白,某程度上還挖掘得很深。如果說它淺白親近,是因為它並非一部學術論文,但論述與引用的詩也有其脈絡和背景,適合入門者也適合進階讀者。全書以討論中國古詩與現代詩的背景開始,展開了這百年以來關於音樂、形式等等主題的回顧,並潛入不同關於自由、政治、反抗、詩是否一種慰藉的命題。
這些命題都很龐大,但廖偉棠也嘗試把它們講得輕鬆,比如談到分行,他就寫「分行的正確打開方式」;談到愛情,「愛情應該讓我們都變得更廣闊」,拿捏著深度與輕鬆的界線,這些都是淺白親近的部分,營造出與作者本人聊天的感覺。
這種有意識的句子與調整難度,使得文初提出的問題(跳躍、未必連貫)等自行消解了,因為《玫瑰》原本就並非一部學術著作,沒有義務一步一步走進深處。如果它是這樣,也就不是40條小徑,而是一條漫漫長路。這些小徑互相突入,切開彼此,但又互相纏繞,像一長串混合的詩句讓我們自行拼裝出屬於自己的詩觀。我們包圍、收緊、抓取著關於「詩意」的理解。
所謂的「詩意」,可以理解為文學性,又或是陌生化,有可能會被理解為神秘主義,或是被學院收藏起來不與大眾分享的秘笈等等。但廖偉棠自然意識到這一點,於是他很慷慨地使用了兩章談論神秘主義:「我們從世界裡,從我們生命裡,感受到了神秘;我們要努力去說出來,即使這個神秘是不可說的。」
「詩的言說是在它感知到了世界神秘之後,它再去生產神秘,而且它衍生出來的神秘,尤其在現代詩裡面,必須是一個開放的門,讓我們讀者通過這個門去感知和去產生自己能夠領會的神秘。」
讓詩維持神秘,並以語言逼近與折射它;讓詩維持是詩,用散文與演講去拆解與重組它;神聖化與袪魅連續進行,在損害詩意後重建它,重建再拆毀,周而復始。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我們觀察它,並以文學讓它再開一次。
香港的詩歌就是「番外」嗎?
先前提到了書中有一章「番外」,其實是一種謙遜之詞,因為這章其實是廖偉棠引用自己的詩歌〈一切閃耀的都不會熄滅〉。為了與引用的大師與前輩們作出區隔,就說這是番外篇。在我看來,這章才是本番,也是全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章節,這個點所折射出來的其他點,連成一線來理解就是「香港詩歌」。就如寫一本論文,論文的核心絕對不是引用了甚麼,而是作者本人。
《玫瑰》的其中一個核心,是向現代詩的讀者袪魅:「跟許多其他類型文學的遭遇一樣,詩歌也有一個地域鄙視鏈。比如說香港詩歌,它們被歸為粗俗與保守。」在這種思考中,與香港詩歌作為對比的是中國詩歌,也是外國詩歌,但廖偉棠所做的自然不會是加深這樣的偏見,他以飲江的語言、也斯的城市詩、西西的童心與語言實驗等展現出香港詩歌獨樹一幟的地方,來迎擊這樣的觀念。
其中一個較為有趣的觀察是,廖偉棠看見中國一些詩歌網站或朋友圈討論一首詩好不好時,他們不會說好不好,美不美,前衛不前衛,而是這首詩牛不牛B。他歸納道:「這來自於他們幾十年來教育裡一直有的一種英雄主義意識,詩歌追求成為英雄,詩人追求成為英雄。在英雄的意識的影響下,詩歌一味地高大上。」英雄主義以外,還有戰鬥意識強烈的文字,使得詩歌變成戰鬥文藝。
而香港詩歌不玩這一套,引用北島的詩就是「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廖偉棠在《玫瑰》裡用了很多篇幅介紹香港詩歌,就連全書最後一章講到「無解的詩意」時,也選擇了淮遠。幾年前在台北詩歌節,廖偉棠說淮遠是他最欣賞的香港詩人之一,淮遠的〈跳蚤〉在廖偉棠看來,是一個迷宮,也是一連串交叉的、錯誤的、旋轉迴環的道路,它似是處處出口,卻又半遮半掩。「這首詩沒有答案,你可以選擇自己去代入。」
中心是牛B,邊緣就是自由;中心鄙視邊緣,邊緣以自由與無解對它比起中指。詩是挑釁的,是番外的,是指向南方的:「甚麼是南方的文學?我希望它是濕潤的,我希望它是草莽的,我希望它是沒有那麼多對某個中心的仰望的。」它游移在外圍,並不建立據點,如若《玫瑰》一書,並不提供一個體系。它整本書都是番外。德里達說,結構的中心位於外部。因為只有外部才能觀照結構,結構本身只有牛B。牛B哄哄哄小孩呢。
詩歌是打破與重新建立的過程
在走近現代詩的40條小徑中,我們讀到了好些危機,比如牛B,比如某些自由詩實在太自由了不知道在搞啥,如果以圍繞的比喻去思考,它們就是些距離「詩意」比較遠的部份。但與此同時,廖偉棠又舉了鴻鴻的一首〈青海湖詩歌節朗誦詩晚會直播集句〉為例。這首詩的背景是鴻鴻參加了中國的青海湖詩歌節,這個詩歌節相當牛B,被稱為世界最大的詩歌節,一百個詩人在湖邊作詩,吹奏這個湖有多牛B。由於實在太過荒謬,鴻鴻決定這樣寫:
是詩人製造了神
它想要從憤怒中哭喊著衝出來
儘管你早已不再是你
感謝南朔山天然富鍶礦泉水的大力支持
這首詩很棒,但它的句子不是「詩意」的,詞彙也不是。它沒有厲害的修辭,也沒有神仙般的比喻鏈。這首詩厲害的地方除了場域與詩人本身的際遇外,更是句與句之間的空隙。詩意在空隙之中,它是散的,是斷開的,但接起來又鋒利如刀。它砍破了些慣性,重組了閱讀方法。
詩要打破些甚麼,又重新建立它,比方老套,比方神秘主義,比方強權,比方學院派與意識形態壟斷,這是《玫瑰》一書反覆強調的論點。打破意味著散,散文的散,散裝的思想藏在40條小徑當中,廖偉棠以他的邏輯建立了番外與本番,我們讀者又以自己的閱讀慣性重組自己的體系。詩歌就像一種久坐過後的拉傷,此後一切意識都圍著它轉,復健過後,觸碰文學的力度與方法都不一樣了。在各種文類中,詩應該是最接近拆卸這一端的。
以演講與散文談詩,是不得不為之,正如我們談論小說或戲劇等,都不得不借助散文的特質。然而當我們想像如何去安排一場課堂,一本演講集時,甚至書寫散文等文類時,詩的間隙與並排就能幫助我們思考。怎樣似斷非斷,怎樣的排列會使材料更為尖銳?在散中折射秩序,在此處倒映他方,排列、包圍、作者先行以點連線,讀者再自己拼裝。讓詩意不斷被拆卸重建,讓精華在過程中哭喊著衝出來,詩意不再是詩意,感謝《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