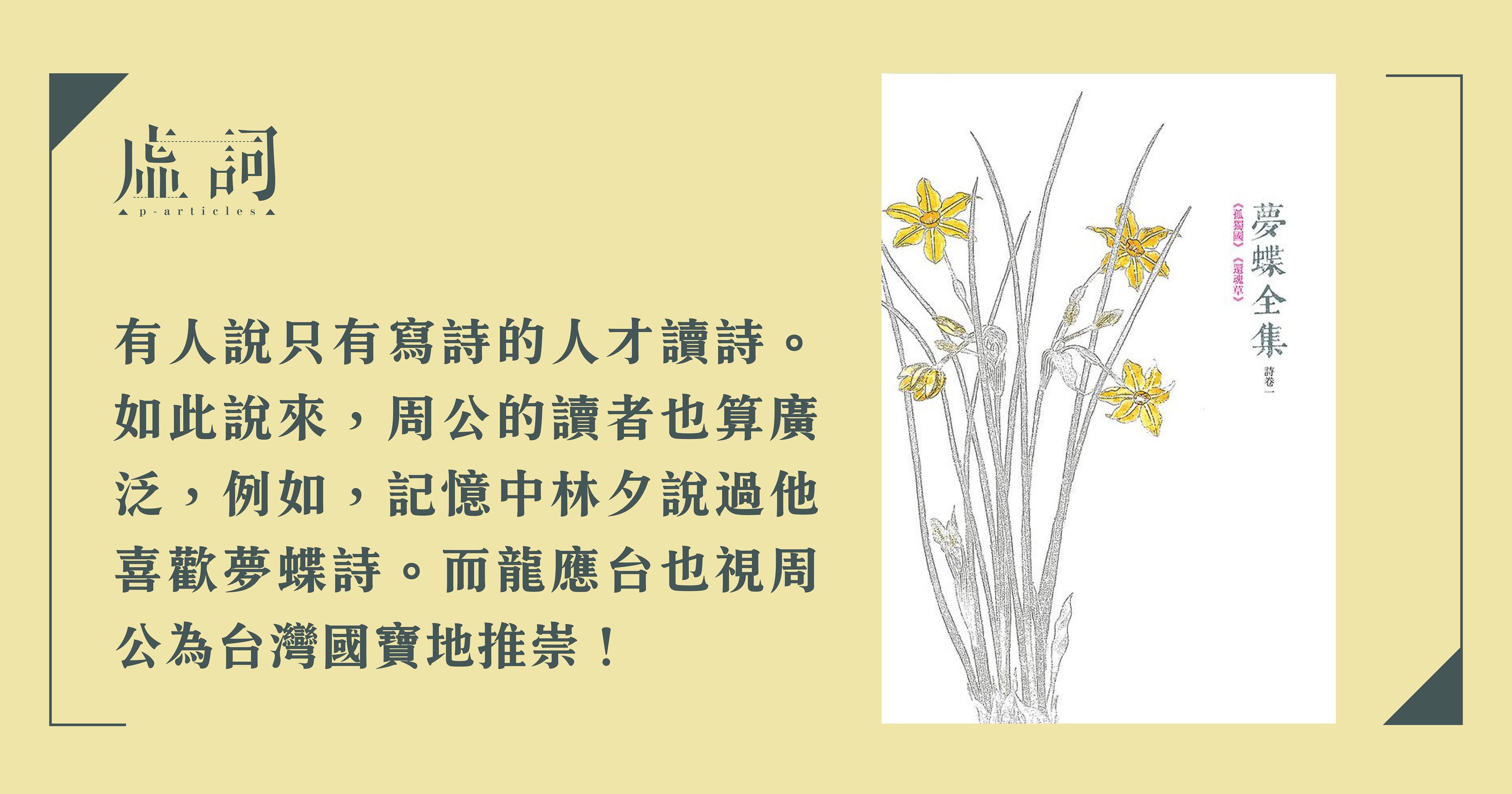第十四朵白菊花——《夢蝶全集》序
「虛詞」轉載前言
五冊的《夢蝶全集》於今年——周公百歲冥誕——由台灣「掃葉工房」出版,實在是華語文壇可喜可賀的盛事。編輯的是堪稱為保存周詩大業而鞠躬盡瘁的曾進豐教授。曾教授又竟然邀請我這位身居異國多年,中文早已生銹的過時文青寫序。他大概因為知悉我與夢蝶詩也真算是綣繾半生。
但愛也不一定是完全盲目的,尤其是談文論藝。為什麼我是周詩迷?這其實是對我個人的生命很關鍵的問題。是我讀周詩,還是周詩讀我?曾兄的來鴻忽然變成一項挑戰,彷彿要為自己「半生的閱讀」甚或是「半生」交待。總記得周詩〈焚〉中的這一段:
面對遺蛻似的
若相識若不相識的昨日
在轉頭時, 真不知該怎麼好
捧吻, 以且慚且喜的淚?
抑或悠悠, 如涉過一面鏡子?
忽然收到曾教授給我的這份「作業」!是「且慚且喜」,但不太「悠悠」。寫著寫著,竟然寫了兩萬多字。太喧賓奪主了。於是開始刪,現在剩下六千多字。希望日後能夠把那些刪除的部分再組織為相關的文章發表。反正「周學」是一早已經成形。
詩的讀者少。有人說只有寫詩的人才讀詩。如此說來,周公的讀者也算廣泛,例如,記憶中林夕說過他喜歡夢蝶詩。而龍應台也視周公為台灣國寶地推崇! 他們都是才情橫溢的作者,卻不算詩人,但這充分顯示了周公跨界的魅力。
很感謝「虛詞」願意轉刊此序,協助推廣。我希望,也相信周夢蝶的詩作將會長存華語文學史。
***
那應該是 2001 年吧!我帶著新近完成的劇情片 《情色地圖》出席不同的影展。其中一站是南韓的全州電影節。電影節某晚安排了一個派對,接待的小姐卻強調,這是很有唐宋遺風的房子。牆上的字畫倒是確切的華夏文化成品。當時我看到的這幀水墨,上書「結廬在人境」!電影節的嘉賓中包括了幾位來自國內的導演。我們也是剛剛一起坐下來。忽然看到那幀畫,我不禁向他們說:「看到陶淵明的詩嗎?」
大家忽然有片刻的靜默,然後一位國內導演有點尷尬地向我說:「我們不熟悉陶淵明!」
其實每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沒有什麼尷尬或抱歉的必要。
觸發全州淵明詩的回憶,是因為最近重讀的周夢蝶詩中的這幾行:
淵明詩中無蝶字;
而我乃獨與菊花有緣?
淒迷搖曳中。驀然,我驚見自己:
知道「淵明詩中無蝶字」當然熟讀舊詩。但「獨與菊花有緣」的周夢蝶於近代華語文學史上,明顯是個偶然,是個例外。當然詩之成就,與國學修養沒什麼絕對的關係。但他是同時能夠與陶淵明和莊周對話,而把華文現代詩推往形而上探索的哲理詩人。
夢蝶詩.淵源
我認為華語文化在過去半個世紀有四座藝術奇峰:張愛玲的小說、侯孝賢的電影、林懷民的現代舞、周夢蝶的詩。其中三峰座落在台灣。四大名家的作品,我都曾撰文探討。但對個人來說,淵源最深遠的卻是周公的詩。
反正,《還魂草》已經是伴隨了我三十多年的詩集。最近翻看那些當年吸引,衝擊我的段落,譬如:
當審判日來時,當沉默的泥土開花時
你將拌着眼淚一口一口嚥下你底自己
縱然你是蟑螂,空了心的。在天國之外,六月之外。
──〈六月之外〉
總在夢裏夢見天墜
夢見千指與千目網罟般落下來
而泥濘在左,坎坷在右
我,正朝著一口嘶喊的黑井走去……
──〈囚〉
這些詩句,葉嘉瑩說:「可說是頗為費解的現代化的詩句了,然而不必也不須更加解說,我們豈不都能……感到一份震撼?」無疑詩句可以是「費解的」,然而是否「不須解說」?我不知道別人的感受。不過我從來沒有想過那是些不需要「解說」的詩。從香港發現《還魂草》的初中跳到八十年代末期── 我已經到了紐約,在社會研究新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唸碩士。某學期,耶魯大學名教授哈羅德 • 布魯姆 (Harold Bloom) 也來客席教了一科「美國現代詩」,我於是去旁聽。記得他當日班上討論的美國詩人──Elizabeth Bishop, James Merrill, John Ashbery──全都於今日成為經典了。
旁聽這課程結果對我頗有衝擊。一直感到周夢蝶是世界級的作家!為什麼不譯為英語,介紹給異國讀者?碩士畢業作業彈性較大。當時我的決定是把《還魂草》英譯,並附論文為序。
答十三問
周詩之中,舊學的典故是所有華語讀者都需要面對的。然而周公通過閱讀中譯,加以消化琢磨之後引述的洋文典故,英譯者不可能不考究出處。當時我感到唯一的解決方法是直接詢問周公,所以寫了一封信,請台灣的一位僑生朋友譚俊立代我傳書。周公覆信給俊立,他再轉寄來紐約給我。這封答我十三問的信寫於 1989 年,真是悵望三秋了。
談周詩自然千頭萬緒。先看〈聞鐘〉:
雪塵如花生自我底脚下。
想此時荼蘼落盡的陽臺上
可有誰遲眠驚夢,對影嘆息
說他年陌上花開
也許有隻紅鶴翩躚
來訪人琴俱亡的故里……
看他如何解答我查詢詩內「紅鶴」的典故。他解釋說:紅鶴一詞,借自《搜神記》: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
然而他說:「拙作不言白鶴,而言紅鶴者,以自識情根未斷,世緣欲捨難捨故也。」他因「情根未斷」而改「白」為「紅」!「紅」於近世通常被理解為熱情、激情的顏色。而傳統的紅則用於婚禮。但周詩的紅似乎更有特定的文藝指涉 ──他的紅豈不通往《紅樓夢》?我們知道曹雪芹的巨著又名《石頭記》。而《還魂草》第一部份〈山中拾掇〉的引言是「一塊石頭,使流水說出話來。」是石頭帶出了語言 ── 也就是生命 ── 的開展。
余光中說無論翻到周夢蝶詩集的哪一頁,「讀到的都是寂寞」。要是周夢蝶詩是關於寂寞,那是說,也關於慾望。當然王國維曾經認為:寶玉的「玉」是與愛慾相通。
色慾論
周公學佛參禪,受基督教吸引,也曾經自承自己個性傾向「自虐」。而傳統宗教當然都是建於「禁慾」之上。著述《色慾論》(L’Érotisme) 的法國小說及哲學家巴塔耶曾經指出:愛情與詩都是一份浪漫的形態,以打破人個體的孤立。若慾望明顯地是愛的動力,詩背後的慾望則幽微深邃。但慾望之為慾望,慾望之生發克服,消泯孤立、寂寞,而融入另一個體,或更大的某種整體。洶湧,或難以不洶湧的慾望令人懼怕,傳統宗教視慾望(恆常難以被社會規條控制)的實踐為骯髒不潔,因而禁慾被奉為聖潔。
巴塔耶語:「現代人面對聖潔時,無法擺脫恐懼與震悚,因為面對被禁之物而生出畏懼。」我們試看〈一瞥〉的這兩句:
當門開半扇──
你底光華使我暈眩
「你」是否這半開之門外,(彷彿在偷窺的)的苦戀禁慾者底「禁物/禁色」,因而令他受如長江大河般的「暈眩……壓迫」感的襲擊?巴塔耶也說:「愛慾其實接近聖潔……不是說它們是同一的……而是兩者都連結著尖銳強烈的經驗!」(223-253頁)
我想這是周公寫的許多「抒情詩」可以在《還魂草》與其他富於宗教感的作品燦然並列,令詩集擺盪於救贖、聖潔、孤寂、淒清、無助、激情的主題及經驗之間。之所以是「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
當然《還魂草》最重要的元素還是禪佛哲思的引渡。〈孤峰頂上〉並沒有用筆墨形述詩的主體得道成佛,進入涅槃,然而那宗教性的狂喜「恍如自流變中蟬蛻而進入永恆」躍然紙上。詩中有句云:「想六十年後你自孤峰頂上坐起。」六十當然是一甲子。但據說當年周公相信自己會壽盡六十,所以出現了這些細節。這也解釋了周公為何在〈燃燈人〉內加了一個註,引述帝釋化為羅剎後向釋迦說的偈:「生滅滅己,寂滅為樂。」即是超越生死,或接受死亡。所以《還魂草》靈慾掙扎的進程,生發於死亡陰影之下,而周公奮勇成篇。這也再解釋了詩作深層的一份迫切緊張。
當然,若周公真的於六十歲大去的話,《還魂草》會成為一輯《武昌街遺書》。書出版時他 44 歲。若根據這組詩的敘述邏輯,〈孤峰頂上〉 之後,將是主體的寂滅與沉默。而華語文壇之幸是周公的詩作並沒有停止。
俗世的救贖
後期周詩仍有不少講究澈悟與解脫。但《還魂草》的建構及重大基調是某類(宗教式的)修行,基本上強調冀願「出世」。而與這種「出世的救贖」相比,後期的許多周詩,與讀者分享的視野,毋寧是一種「俗世的救贖」。
於這現世、俗世中,詩人的語調不再是那麼愁慘的。例如〈九宮鳥的早晨〉完全歌頌生命的愉悅。即使是有關「孤清」,詩人亦進入了另一層的辯證。在〈於桂林街購得大衣一領重五公斤〉裡,詩人是因蘇格拉底「兼身(結婚)之必要」之語而描述「爭執著」的「獨身與兼身/荒涼的自由/與溫馨的不自由」。既然能夠與「溫馨的不自由」爭執,「荒涼的自由」當然不自認理虧,或不幸。
詩集 《十三朵白菊花》、《約會》都輯了不少詠物詩,可以是詠動物 ── 鴨、鳥、蝸牛、蜻蜓;詠植物──草丶竹、蘑菇;或詠靜物、景物。若所謂「命運」只是人的個性、環境與機緣千絲萬縷地攪拌而成的「事件」,那晚期的周詩,特別是這些詠物詩內,恆常地為「命運」作肖像。茲舉〈白西瓜的寓言〉為例。白西瓜是「只有瓤;/無子,亦無皮」的明月。於此,周公神妙地重新想像蘇東坡「月有陰晴圓缺」之句,藉此曉喻讀者。也許周公因而題詩為一則「寓言」吧!
這白西瓜「也不曉得是誰下的種」,但這種子似乎是陰陽同體,又極可能被一股生之慾望激發,於是:
……一想到愛與被愛
那不能自已的美與渴切
白西瓜……
便不能自已的
熟了
成熟為圓滿朗月,卻開始或因此而飽受折磨,而缺缺缺。此外,它還需要面對別的災害。在這則「寓言」中,周公把「天狗噬日」與「蟾蜍竊月」的神話揉合改編為「蟾蜍噬月」。他的解釋是──蟾蜍其實是天狗的「饕餮」的弟弟。這貪吃的蟾蜍把月吃了,但終究仍要把這白西瓜再吐出來,這「窈窕依舊,清涼與皎潔依舊」的白瓜,其「最可口的這邊,恰是早年/被齒及的這邊」。末段的結論:
得瓜者,復為瓜所得
而成為瓜。成為
可圓可偏可半可千江的傳說
「陰晴圓缺」的重點還是「否極泰來」。試看詩中所用之典:〈水調歌頭〉及天狗與蟾蜍兩個傳說之外,沒有特別的宗教暗示或喻意。此所以,周公晚期的這類詩,我稱之為「俗世的救贖 」詩。〈白西瓜〉的主旨應該是自我的完成。另外一首呼應這主題的詩是〈疤〉,詠的是竹。詩人視竹「……身上的每一環節/全是疤。痛定的淚與血……」。
月會缺會圓,竹的身上會長竹節。這些詩的敍述效果,依稀都是某個特定的命運底描畫。〈疤〉內,甚至有這樣的句子:
在可以無恨的
感激之夜。你為自己的成長而俯仰
這類詩句的視野彷彿很接近葉嘉瑩所說的「將悲苦泯沒於智慧之中……以超然俱化」。但並不盡然,因為〈白西瓜〉和 〈疤〉並非周夢蝶晚期詩作裡最具代表性的。自我的救贖與完成,並非一定自發或必然。
〈焚〉 估計是《還魂草》稍後的作品。〈焚〉 是愛慾之烈焰。而焰之源是一片「霜葉」。這是「雪中取火」的矛盾意象。但氷霜當然也可以傷人。詩裡的「我」在「削髮日」──向情緣告別的那天──「被焚於一片旋轉的霜葉。」「我」於是稱往昔為「天譴……劫餘的死灰」!是的,不能自己的愛是個詛咒。從「霜」到「死灰」,有「愛比死更冷」的意味。而這份激越悲楚充斥著《還魂草》。
相信也差不多是同期的〈積雨的日子〉,語調有了轉變。這也是周公的詩步入較為散文化的階段了。這詩有實景,有日常生活的語調。中間有這麼一段,在「無所事事的日子。」「我」偶爾:
涉過積雨的牯嶺街拐角
猛抬頭!有三個整整的秋天那麼大的
一片落葉
打在我的肩上,說:
『我是你的。我帶我的生生世世來
為你遮雨!』
貌似沖淡的文筆,其實把愛侶「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狂情,「生生世世」的山盟海誓,濃縮於這蒼涼的意象──一片因風吹雨打而飄墜於敘事者肩上的落葉。在詩的第一段,步入牯嶺街的主體是「我」。然而於末段,涉過牯嶺街拐角的是「他」,是因為「自己也像秋天一樣的渺遠」?然而主題轉換帶來的一個效果是:自己已經與自己有了距離,即是可以客觀地觀己了。而這距離應該肇自記憶 ──「我」可不是已經承認了:「記憶……是久遠劫前的事」?究竟是因為牯嶺街,落葉,還是節令與地域的結合,令落葉像輕搭於他肩上的手,「柔柔涼涼」地觸動了「我」既渴求又想迴避的消息與回憶?對落葉為他遮雨的承諾,「我」只夷然地回應說:「雨是遮不住的」,尤其在多雨的季節!
〈積雨的日子〉裡沒有《還魂草》內血與淚的痛切。然而請留意這「涉」字── 踏過牯嶺街的步履並沒有「也無風雨也無晴」的瀟灑。有的只是昔日的「我」變成今天的「他」底脆弱與一點哀思!然而不論「我」,還是「他」於牯嶺街拐角:是否在埋怨自己不應舊地重遊?
但這葉的意象仍然宣告了──愛的回憶,無論怎樣殘破脆薄,如何沒有能力遮擋今朝或明日的風風雨雨,但那仍是生命的一點庇蔭,救贖與祝福!
命運的沉思 ──「亞膜‧花蒂」
周公不少詠物詩是些命運的肖像,由無奈或一些自勵之語織出。但瀰漫晚期詩作的,不少是有關命運的沉思。〈蝸牛與武侯椰〉裡的蝸牛/武侯,為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悠悠此心……有誰識得」?真的只是為劉備「一顧再顧三顧」草蘆,「而四出五出六出」祁山,才無悔地卒於五丈原?隱蔽詩中的是這個問題:諸葛武侯是如何受觸發而覓得自己的命運?它/他是以指揮若定的雙角──不可及的智兼更更不可及的愚── 對抗、駕馭命運?還是它/他被命運駕馭?
對個別與個人命運的思考一直持續到周公暮年,幾近入棺之前的詩。例如〈我選擇〉 的最後一句是:
我選擇不選擇
那是否等於被命運選擇,讓命運為個人選擇?
宣告上帝死亡的尼采,曾猛力攻擊基督教的論點之一是 ── 「善者得求」的宗教信仰令人懦弱地拒絕面對天道不公不仁的可能性。他激勵人重燃古希臘劇場的「悲劇感」以正視時代及個人的災劫苦楚。
葉嘉瑩把周公與陶淵明相比時提出「將悲苦泯沒於智慧之中,而隨哲理以超然俱化」。我的閲讀發現後期的周詩誠然顯現了更多的融合生活的智慧。但周公不曾把悲苦超然「俱化」。七十九歲時寫的〈斷魂記〉裡,詩人慨嘆「七十九歲的我頂著/七十九歲的風雨/在歧路。歧路的盡處/又出現了歧路」。酸澀與迷失,「血」字與「淚」字在夢蝶詩中仍然伴他到老。這是周夢蝶往返於傳統與現代之間,他個人所特鑄,不否定,不放棄,坦然地不「俱化」的悲劇感。所以〈斷魂記〉 的起首是:「魂,斷就斷吧!」往後,有人 ──是作者自我身外身的對話者?── 向迷路者指點方向,聲稱他倆是「吉人遇上了吉人」,而「災星即福星」。
尼采鼓勵現代人保有悲劇感。但輔助著,支撐,揹負著這悲劇感的是他所珍視的一個意念及情感:「亞膜‧花蒂」(amor fati )。原文是拉丁文的「亞膜‧花蒂」,其定義是──對命運的愛,對個人命運的愛。
十三朵白菊花
而人,像周公這樣的詩人,如何去愛命運 ──即是愛全部,自己的人生?
〈斷魂記〉內 「災星即福星」之語是最簡化的態度。而反映這主題,最微妙地與悲劇感辯證,以召示最後仍是無條件地愛一己命運的作品,是與詩集同名的點題詩〈十三朵白菊花〉。
詩人自述該詩的靈感來自某天,「我」重返書攤時,發現有人遺下一束白菊花。這令詩人震動,「一念成白! 」而「震慄於十三/這數字。無言哀於有言的輓辭」。「白」是喪禮的顏色,而菊花亦是上墳拜祭時經常用以供奉的花。所以詩人忽爾想像自己早已是逝者亡靈,如今接受祭祀。看著他自己街頭的書攤,「頓覺這石柱子是塚,/這書架子,殘破而斑駁的/便是倚在塚前的荒碑了!」
白菊花之緣較 〈桂林街〉舊衣店之遇合更為飄渺──於二手故衣之內,詩人仍可以發現了一個名字而生親近之感。但這次,他完全不知道贈花者是誰。然而詩人相信無名的贈花者「定必與我有種/近過遠過翱翔過而終歸於參差的因緣」。而縱使這因緣只涉一次,便已足夠「生生世世了。」是怎麼樣的「生生世世」?這並非牯嶺街上的帶雨的落葉,而是肯定能遮雨庇蔭呵護他的生生世世,所以詩人才會:
感愛大化有情
感愛水土之母與風日之父
……
菊花啊!複瓣,多重,而永不睡眠的
秋之眼:在逝者的心上照著,一叢叢
寒冷的小火燄。……
從菊花,詩人看到水土風日的滋潤,宇宙之情,生者與逝者的相接緬懷。十三是不祥的,白菊更彷彿是一種詛咒,但「災星即福星」。所以這變成了詩人的「菊花緣」。人生世上,這豈不已是最早最後最重大的緣分?於是詩人宣告:感愛!感念!感激!
這首詩內,淚字仍然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詩人把贈花之舉,喻為一炷祭墓的「心香」,那亦是這位無名贈花者的流下的「宿淚」。儘管這裡依稀出現了《紅樓夢》還淚的典故,但性別似乎已經不重要,只是廣義的感應著因緣,報還世間恩情所灑之淚。此外詩末「我」「猛笑著。在……垂垂的淚香裡」是懷抱悲劇感的詩人,驚喜於一點因緣的恩賜,滴下感動與感激的淚。〈十三朵白菊花〉 是筆者所接觸過的華文現代詩中,少數對「亞膜‧花蒂」amor fati 「命運之愛」最深刻動人的表白。
周公晚期詩中的因緣,無疑蘊含著佛家的想像。但亦可以俗世地理解為最廣義,宇宙性的愛情、親情、友情,甚至陌路人之間互動的同胞物與之情。他的好些晚期作品源出唱酬之詩 ──給陳庭詩、余光中、翁文嫻的都有。這當然是他對友誼的回應。
我們許多周迷都感激曾進豐先生對周公生前死後的看顧,及不辭勞苦地詮釋,整理他珍貴的文學遺產,於這詩與夢都式微的世代。曾先生竟然委託我這個仍未交出功課的譯者,為周公全集寫一篇序文,實在令我羞慚。但這給了我於多年之後,重讀《還魂草》,周公的書簡,及他晚期的三本動人的詩作。
也提醒了我:是應該重整英譯《周夢蝶詩選》這計劃的時候了。
原來當年我去信周公,曾提出了十三個問題,那可曾令他感到不祥與不安?
而三秋之後,我寫的這篇文章,充斥著不少臆測,可否算是我第十四次的提問?
是周詩問我?還我問周詩?
充滿惆悵,感激及緬懷之情的此時此刻,我想像拙文是我獻給周公精魂的第十四朵白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