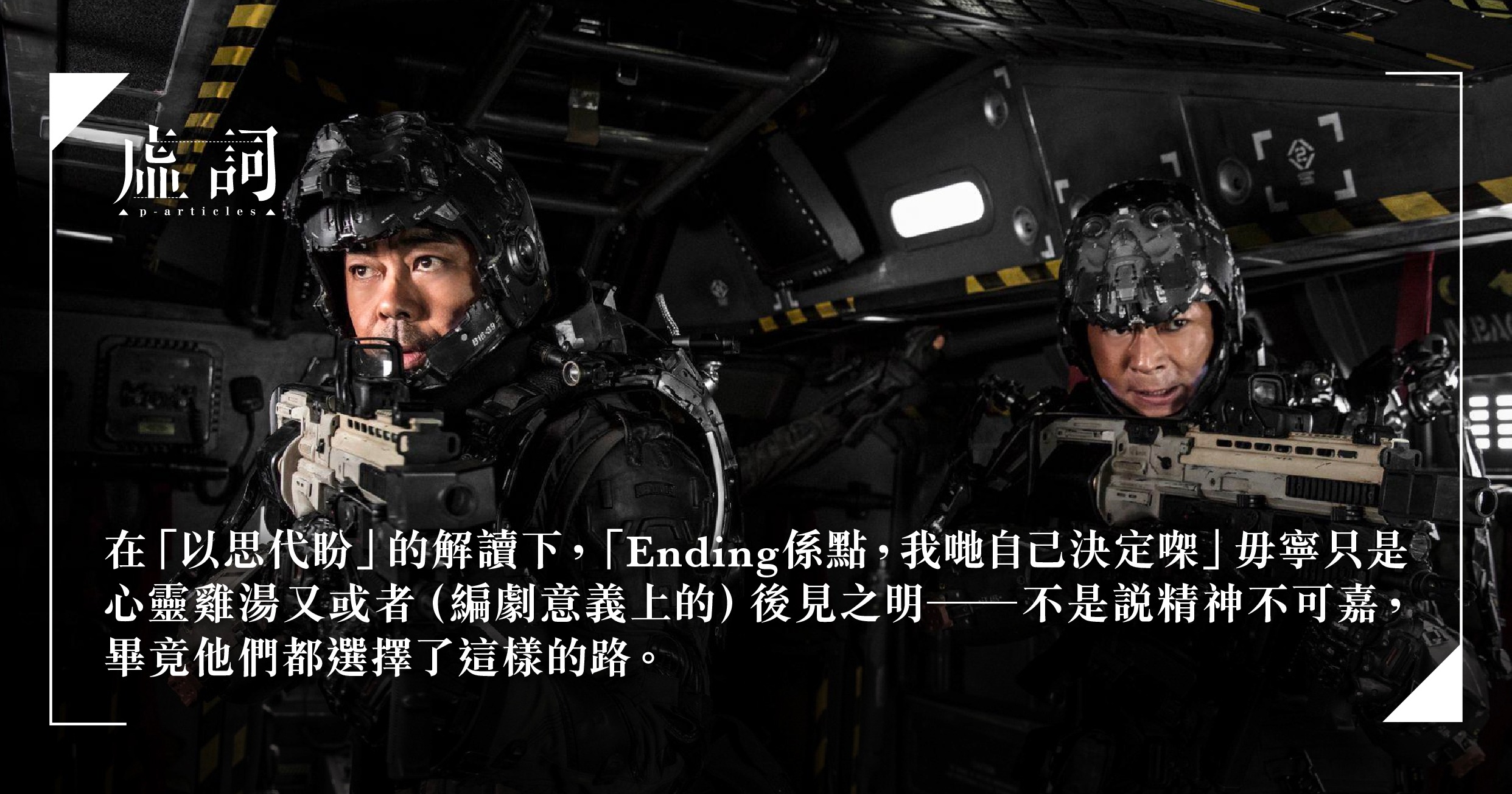《明日戰記》:刑天與明天的距離
影評 | by 雙雙 | 2022-10-12
此時,《明日戰記》的票房已迫近6338萬。作為近來最受熱議的電影,很多影評早已探討過電影與現實之間的對應或不對應關係(後者比如是地名上的去語境化 (decontextualize))。而把《戰記》抽離機甲科幻片和香港電影的語境,它最使我深刻的就是三句對白——第一句肯定是未看其片先聞其聲的「天幕就係我,我就係天幕」,其次是作為電影主旨而刻意(且)重覆的:「Ending係點,我哋自己決定㗎。」和不無巧思的:「刑天?打到你冇明天!」在電影情節上,「明天」自然屬於「我們」而非「刑天」,但在我看來,「刑天」和「明天」毋寧是銅板的兩面——而這個銅板的「公定字」正正決定著「我們」的ending:一邊是「Ending係點,我哋自己決定㗎」,一邊是「刑天就是我們,我們就是刑天」。
「Ending係點,我哋自己決定㗎。」
臭鼬(姜皓文飾)拋出對《天外奪命花》的劇透和「影評」(「Ending好慘㗎,外星人贏晒,地球人輸晒,睇唔睇都罷啦!」),好讓重生(劉青雲飾)接上「Ending係點,我哋自己決定㗎」的點題「金句」,但臭鼬和重生說的「ending」自然不是同一碼事:《天外奪命花》有《天外奪命花》的「我們」,《戰記》有《戰記》的「我們」,後者的ending是否極泰來,花葉重生(「花葉重生」不是成語,是西西肥土鎮系列中的女性角色,本名葉重生,後冠夫姓——但在此未嘗不貼切),重生之言在ending之前看來是受希望的感召(或對希望的召喚),ending之時則成為讖語,但對於《天外奪命花》呢?「你盡力做,但唔等於你會做得好」,更遑論成功。
《戰記》的任務,成功與否實際上取決於三個變項:戰機隊成員(人類)、機械人,和基因子彈。譚冰和重生爭論過關於信機械人/槍還是人的問題,而泰來(古天樂飾)義憤填膺地質疑任務是否值得戰機隊「搏命」,也只是針對顯影液、亂流和潘朵拉的攻擊性來講,偏偏最「可疑」的基因子彈卻沒人講——「P7N9型病毒」是四天前的研究成果,基因子彈就更別提了;陳蒼松博士說「相信」只要把病毒釋放在潘朵拉母體,就能讓它停止生長,「相信」所留有的「學術性餘地」,也不免令人不安。但電影卻「蠱惑」地把(戲內戲外)所有人的注意力調動到觸目驚心、physical的危險上,而無視了虛無縹緲、biological的藥效;戰機隊可以靠意志和智力打敗內奸、機械人和潘朵拉,但如果至關重要的基因子彈無效低效,大概只能望天打卦,又或者求諸魔法了——他們在潘朵拉正要殺傷居民之際擲出子彈,幅員遼闊的潘朵拉旋即在居民面前歸於沉寂,正讓我想起Frozen II(魔雪奇緣2)結尾,Elsa用她的冰魔法在千鈞一髮之間把巨浪凍結,挽救了岸邊王國的場景——「明日」科技之神奇似乎也去魔法不遠了。
潘朵拉和異形
《戰記》的劇情同時令我想起另一部續集電影:同為未來戰爭片的Aliens(異形2)。故事講述主角Ripley在太空漂流多年,返抵地球時得知女兒早已去世,又馬上要隨團前往遭異形入侵的LV-426星球基地,搜查期間意外地救出唯一倖存的Newt,其後,Ripley發現同行的Weyland-Yutani集團代表Burke為了商業利益草菅人命(Burke不久就得到報應);在Ripley等人準備離開星球時,她為了拯救Newt而孤身深入基地地庫,碰上異形母體 (the queen),經過一輪決鬥後終於把對方掉出太空,而Ripley和Newt也建立起了超越血緣的母女情誼。
在《戰記》中把楊霖咬死的小怪物與異形們 (aliens) 在形態上和生產上都有相似之處——牠們來自潘朵拉母體,潘朵拉母體也一如the queen,作為幕後黑手藏身地底;像保護自己眼球一樣保護 (guard it as the apple of his eye) 天幕的李昇與拼命維護公司利益的Burke亦功能類近——而我認為最值得討論的是「Newt – 盼盼」的關係:
一方面,盼盼的「出身」與Newt相近:Newt在危機四伏的廢墟中獲救,其後認同喪女的Ripley為母親,正如失去思思的泰來在醫院中救出盼盼,並視之為女兒,於是,兩者同被劇情賦予了希望與延續的意味——但「希望」的含義和厚度又似乎不盡相同。另一方面,在相似之外,《戰記》以相同的格式來命名泰來的「兩個女兒」,使「盼盼」顯然地成為了「思思」的變體回歸——這是Newt之於Ripley所無的一層意義——這種「以盼代思」的安排能被如何解讀?
思思、盼盼和Newt
雖然字典沒有「思盼」的詞條,卻聽來耳熟,才想起是〈星塵〉歌詞中的一句:「念掛一體的我們思盼閃閃星光」,在這用例上兩字字義被視為如出一轍,但實際上存在一些微妙的差異和歧義,以至在電影中代表著兩個南轅北轍的方向。前者代表廁身於「明日戰記」者對「昨日」的依戀,「思」有想念、掛念之意:如果不計作為片頭背景的戰鬥畫面,電影的第一幕正是泰來向思思展示以前的地球——他對「以前的地球」的思念透過她來呈現,並投射在對她的命名上;但除此之外,「思」還可以表示想、考慮、動腦筋,是行動前的內心的權衡過程。「盼盼」則是從當下的「戰記」指向「明日」——「盼」通常表達對未來、前路的希望、想望;又或解作顧、望,是純粹的動作。
在Aliens中,Ripley透過Newt來重獲母親的身份,並以為保護Newt而展開的殊死決鬥來完成電影的motherhood主題;Newt在廢墟中存活多時而得救,也表現出了小女孩看似(雙重)弱小實質上堅韌得超凡脫俗的生命力。然而《明日戰記》終歸是「男人們的故事」,側重其利斷金的brotherhood,於是,盼盼自然顯得平面、單薄,對於劇情張力也貢獻甚微——觀眾為「男人們」所付出的情感,斷估要比對盼盼的多得多——畢竟,「喱次任務唔係為咗自己,係為咗所有嘅人」,「男人們」乃為16萬普羅大眾(以至全人類)而戰,盼盼也只能算是段小插曲,是「男人們」沿路打怪時「拾取」的精神道具。故此,盼盼也僅止於是(劫後)餘生與新生的象徵,而她的名字——一如片中其他角色(重生、泰來,以至潘朵拉),也不過是作為萬佛朝宗於「希望」的眾多能指之一。
那麼,在此的這些「希望」從何而來?似乎全然出於「他」們的自信和在「冇B計劃」的形勢下背水一戰的決心,這是「盼」的部分——「思」呢?也並非全然闕如,泰來和譚冰的衝突就是體現,卻是點到即止,基因子彈的成效於是由始至終都被毫無根據地當作設定 (setting) 的一部分來接受。究其成因,要麼是因為他們被總部某種掩眼法所瞞過——那大可援引諾蘭電影Prestige(死亡魔法)中的一句對白來回應:“You don’t really want to know. You want to be fooled.”;要麼,他們的希望是出於「信政府」(總部)——或者,科技,或者兩者是分不開的——一廂情願的信仰。這個過程正是「以盼代思」的演繹,而這種「希望」在我看來不無危險性。
刑天與明天的距離
「刑天與明天的距離」有三重意思——在語音上,兩者近到只差一個聲母 (j/m),所以臭鼬才有那句機智的對白。
而在傳說中,刑天被斬首而不死,「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無頭,首先就是沒有「未來」的表現——刑天與明天的距離是無限——卻仍以志逆(天)意。陶淵明的〈讀山海經.其十〉把填海的精衛與刑天並置,說她/他們「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在詩人看來,刑天堅持「昔心」似是為了不可待的「良辰」,大抵是對戰勝之日的來臨心存盼望。無頭的第二重含義卻是失去「思」的能力,「盼」就變成了一種虛妄的「望」,這一如尼采對潘朵拉 (Pandora) 神話的詮釋:「希望」仍在盒中,是為了讓人抱有希望,才會繼續堅持在苦刑中逗留。
「男人們」最終迎來「明天」,他們的希望和堅持算是盡了人事,基因子彈的奏效與否卻是沒有保證的「成事在天」。假如基因子彈無效低效,「Ending係點」就會倒干相向,成為對他們自信和盼望的莫大諷刺——他們不亦如「盼而不思」(「以盼代思」的極致)的刑天一樣,徒然地舞動干戚對抗無影無形的敵人,而「良辰詎可待」?在此看來,刑天與明天作為他們的兩種ending,也不過是一步之遙。
「條路點行,係由自己決定。」
在「以思代盼」的解讀下,「Ending係點,我哋自己決定㗎」毋寧只是心靈雞湯又或者(編劇意義上的)後見之明——不是說精神不可嘉,畢竟他們都選擇了這樣的路:泰來由直升機到裝甲車,重生由裝甲車到步行——但如果必需點題,多年前《無間道》的那一句或者來得更為適合:「條路點行,係由自己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