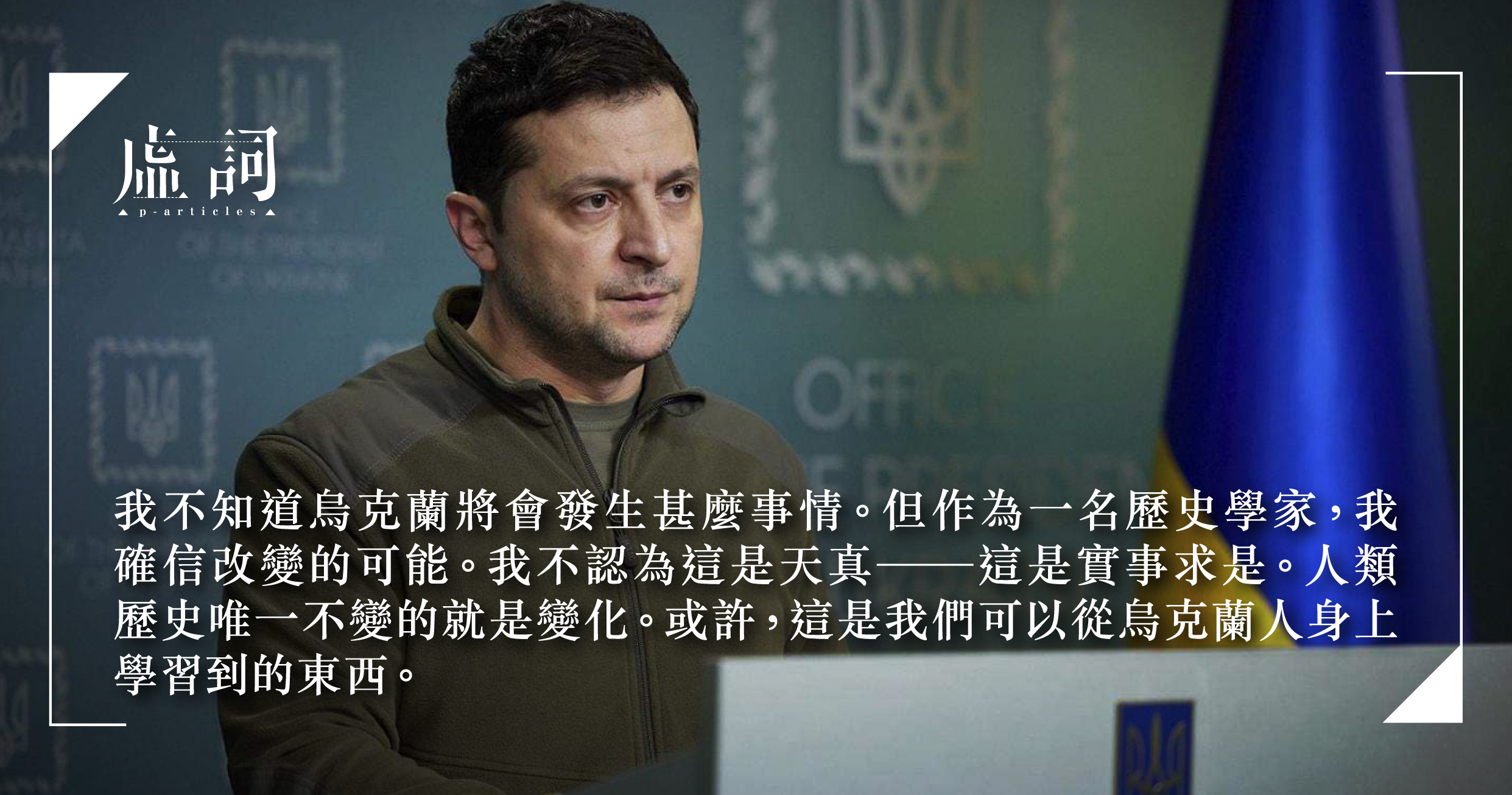烏克蘭危機與人類歷史的方向
時評 | by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李敬恒譯 | 2022-03-17
處於今日烏克蘭危機核心的,是關乎歷史與人類本質的一個基本問題:改變是否可能?人類能否改變他們的行為方式?還是歷史只會永無休止地輪迴,而人類終究注定要重演過去的悲劇,除了舞台的陳設,什麼都不會改變?
有一種觀點斷然否定改變的可能。它辯稱世界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叢林,而唯一能夠阻止一個國家吞噬另一個國家的就只有軍事力量。從來如此,而且永遠如是。那些不相信叢林法則的人不單只欺騙自己,更危害自己的生存,斷不會活得太久。
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所謂的「叢林法則」根本就不是自然法則。人類創造了它,亦能夠把它改變。與流行的誤解相反,根據考古記錄,首次有明確證據支持的有組織戰爭僅發生在 13,000 年前。即使在那之後,也有許多時期並沒有任何關於戰爭的考古證據。與萬有引力不同,戰爭並非大自然的基本力量。它有多激烈與是否存在,取決於背後的科技、經濟與文化因素。隨著這些因素改變,戰爭亦會發生變化。
這些變化的證據隨處可見。過去幾個世代,核武器已經將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轉化成瘋狂的集體自殺,迫使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尋找不那麼暴力的方式來解決衝突。儘管大國間的戰爭─例如第二次布匿戰爭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以來都是大部分歷史的亮點,但在過去七十年來,超級大國之間已經再沒有發生任何直接的戰爭。
同一時期,全球經濟已經從以物質為基礎轉型為知識型經濟。財富的主要來源曾經一度是金礦、麥田和油井等物質資產,但今時今日卻是知識。通過武力你可以奪取油田,卻無法獲得知識。結果,征服產生利益的能力每況愈下。
最後,全球文化亦發生了結構性轉變。許多歷史上的精英—例如匈奴族長、維京首領和羅馬貴族—都對戰爭持肯定的態度。從薩爾貢大帝到墨索里尼等統治者,都試圖通過征服來令自己永垂不朽(而像荷馬和莎士比亞這些藝術家亦樂於助長這種幻想)。其他精英,如基督教會,亦把戰爭視為邪惡但無可避免。
然而,過去幾個世代,這個世界在歷史上首次被一些把戰爭視為既邪惡而又可以避免的精英統治。就算像小布殊和特朗普這樣的人─更不用說那些默克爾和阿德恩般的領導人,跟匈奴人阿蒂拉或哥德人阿拉里克都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家。他們通常帶著對國內改革而非征服外國的夢想上台。而在藝術與思想的領域,從畢加索到寇比力克,大多數頂尖角色都是以描繪戰鬥中毫無意義的恐怖,而非讚頌戰爭發動者而聞名。
由於這些變化,大多數政府不再將侵略戰爭視為促進其利益的可接受工具,而大部分國家也不再幻想要征服和吞併鄰國。認為只是軍事力量阻止了巴西征服烏拉圭或西班牙入侵摩洛哥這種看法根本毫不正確。
和平的指標
眾多統計數據表明了戰爭的衰落。自從1945年以來,由於外國入侵而重新劃定國際邊界的情況相對罕見,亦沒有任何一個國際承認的國家因遭外國征服而從地圖上消失。內戰與叛亂等衝突依然存在,但即使把所有類型的衝突都計算在內,在 21 世紀的頭二十年裡,人類暴力造成的死亡數字也少於自殺、車禍或與肥胖相關的疾病。火藥的殺傷力已變得遠比食糖更低。
學者就確切的統計數據爭論不休,但重要的是看到數字背後的意義。戰爭的衰落既是心理也是統計現象。重點在於「和平」一詞的含義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和平只意味著「暫時沒有戰爭」。當身處1913年的人說「法國與德國和平共存」,意思只是法國與德國軍隊當時沒有直接衝突,但誰都知道它們隨時可能爆發戰爭。
近幾十年來,「和平」的意義已經演變成「難以相信會有戰爭」。對許多國家來說,被鄰國侵略與征服已變得幾乎不可想像。我在中東生活,所以非常清楚這些趨勢也有例外。但認識到這些趨勢至少跟能夠指出那些例外情況同等重要。
「新和平」並不是統計上的意外或嬉皮士式的幻想。這一點清楚反映在經過冷靜計算的預算案中。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政府都感到十分安全,平均只將大約 6.5% 的預算用於武裝部隊,而把更多支出投放在教育、醫療保健與福利之上。
我們傾向覺得這一切皆是理所當然,然而它卻是人類史上一個驚人而新奇的事物。幾千年來,軍費都是每個王子、可汗、蘇丹和皇帝的預算中最大的項目。他們幾乎沒有花一分一毫為人民大眾提供任何教育或醫療協助。
戰爭的衰落並非來自神蹟或自然法則的改變。這是人類作出更好選擇的結果。它可以說是現代文明最偉大的政治與道德成就。不幸的是,源於人類選擇也意味著它可以逆轉。
科技、經濟與文化持續變化。網絡武器的興起、人工智能驅動的經濟和新興軍國主義文化,可能會導致一個比任何我們見識過的還要糟糕的新戰爭時代。要安享太平,要求幾乎每一個人都作出正確選擇。相反,僅僅其中一方的錯誤選擇,便足以引發戰爭。
這就是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應該關注俄羅斯威脅入侵烏克蘭的理由。假使強國吞噬身邊弱小國家再次成為常態的話,將影響世上所有人的感受與行為方式。回歸叢林法則的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結果,將會是政府犧牲其他一切來急劇增加軍事開支。原本應該撥給教師、護士和社會工作者的款項,將會轉而投放在坦克、導彈和網絡武器之上。
回歸叢林還會損害各國在預防災難性氣候變化或監管人工智能與基因工程等顛覆性技術等問題上的全球合作。要與隨時準備消滅你的國家一起工作談何容易。而隨著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軍備競賽升溫,武裝衝突的威脅只會進一步加劇,造成一個極有可能毀滅人類的惡性循環。
歷史的方向
如果你相信歷史不可能改變,並且人類從未、也永遠離不開叢林,那麼剩下的唯一選擇,就只有扮演捕食者或獵物。面對這樣的選擇,大多數領導人將寧願以頭號掠奪者的身份被載入史冊,將自己的名字加到那醜惡的征服者名單中─那些要應付歷史考試的可憐學生還必須把它們牢牢記住。
但或許有可能作出改變?或許叢林法則只是一個選擇而非無可避免?如果是這樣,任何選擇征服自己鄰居的領導人,都會在人類記憶中佔據一個特殊─遠比你那平平無奇的帖木兒更為糟糕─的位置。他將會作為人類最偉大成就的毀滅者遺臭萬年。就在我們以為已經離開叢林的時候,他把我們硬拉回來。
我不知道烏克蘭將會發生甚麼事情。但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確信改變的可能。我不認為這是天真—這才是實事求是。人類歷史中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或許,這正是我們可以從烏克蘭人身上學習到的東西。幾個世代以來,烏克蘭人最懂得的就只有暴政和暴力。他們忍受了兩個世紀的沙皇專制統治(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變中倒台)。曾經短暫地嘗試獨立,但很快便遭到重新建立俄羅斯政權的紅軍所粉碎。烏克蘭人隨後經歷了可怕的人為的滅絕大饑荒、斯大林的恐怖統治、納粹佔領和長達數十年催毀人心智靈魂的共產主義獨裁統治。當蘇聯解體時,歷史似乎保證烏克蘭人會再次踏上殘暴暴政的道路—畢竟他們還懂得什麼其他的東西呢?
可是,他們作出了不同的選擇。儘管有那樣一段歷史,如此難以忍受的貧困以及各種看似無法克服的障礙,烏克蘭人還是建立了一個民主體制。跟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不同,烏克蘭的反對派候選人一再成功取代時任議員。在 2004 年和 2013 年面臨獨裁統治威脅時,烏克蘭人兩次起義捍衛自己的自由。他們的民主是新事物。「新和平」也是如此。兩者都很脆弱,都可能不會持久。但兩者都是可能的,並且有機會可以紮根。所有老舊的事物都曾經簇新過。一切一切,都取決於人類的選擇。
(原文載於The Economists 9th February, 2022)
〈編按:作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以色列歷史學家兼思想家,著作包括「人類三部曲」的《人類大歷史》、《人類大命運》、《21世紀的21堂課》,2002年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專研中世紀史與軍事史,現任教於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