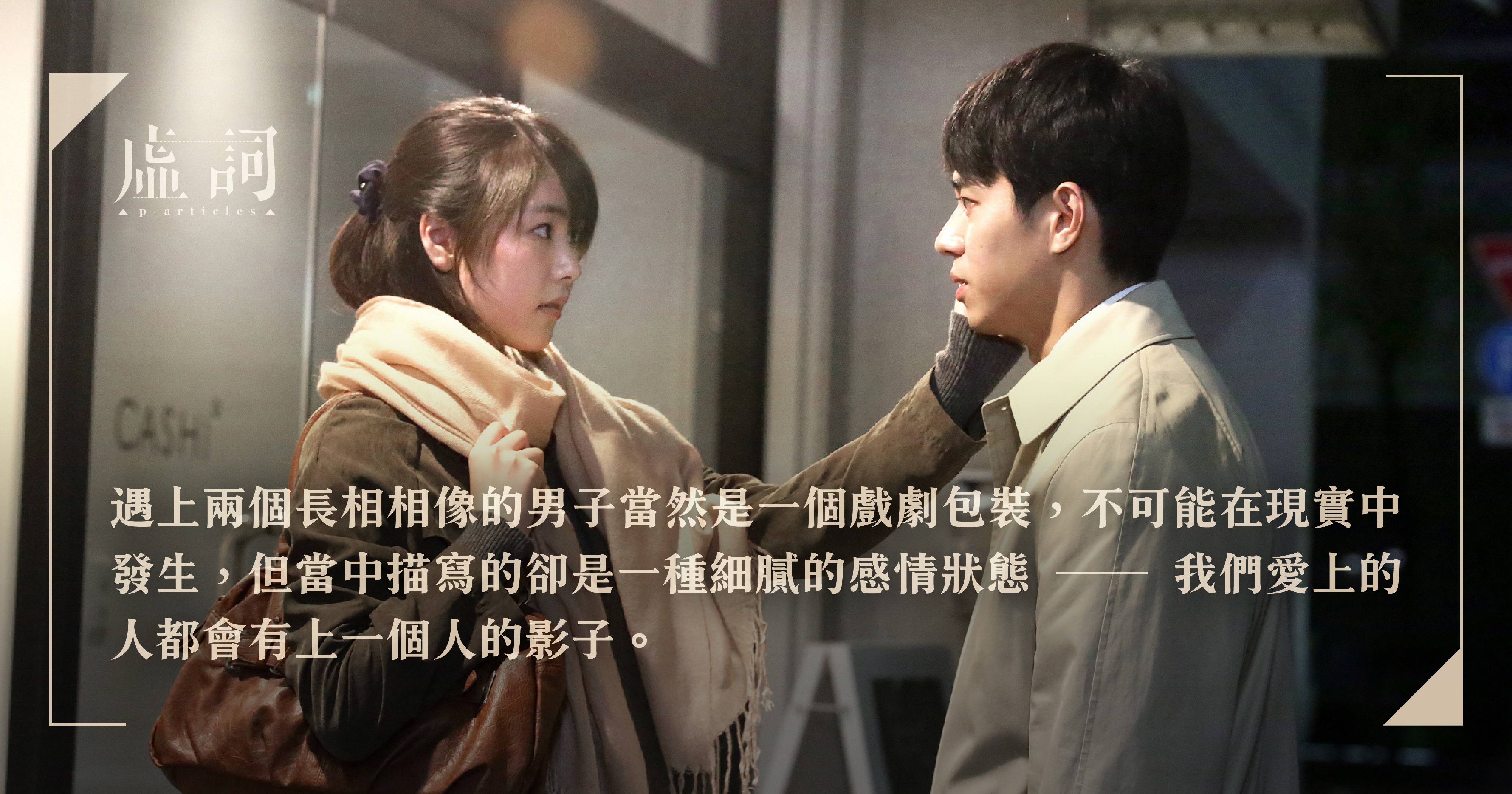女性電影的愛情成長 —— 濱口龍介《睡著吻別 醒來抱擁》
在一個政治正確的爭議年代談女性電影,彷彿是把自己丟進一地泥濘裡。最近百老匯院線重上日本電影導演濱口龍介2018年的作品《睡著吻別 醒來抱擁》,一個女人愛上兩個男人的故事,像重新提醒了我們女性電影的核心所在,其實是女性如何從中體現自己的主體性,如何在故事裡反映她們的內心。
包括近來大受歡迎的短片集《偶然與想像》(2021),濱口龍介近年幾部導演作品(《歡樂時光》(2015)、《睡著吻別 醒來抱擁》)都以女性角色為故事核心。不是說以女性角色為核心就直接等於女性電影,重點是女性如何透過故事中的經歷,得以發展、探索和表達自我。而在《睡著吻別》中,這個經歷就是愛情。
愛你像我前度
《睡著吻別》的故事並不複雜,女主角朝子在故事開初愛上一個叫麥的男子,一見鍾情。雖然被好友警告過,又見識過麥率性而為的行事性格,愛情的魅力畢竟甜蜜誘人,深陷而不自知。直到一日麥突然人間蒸發,戀情無疾而終。朝子搬到東京以圖重新開始,卻又意外遇上一名跟麥長相一模一樣的男子亮平,兩人的感情在大地震的陰霾下開展……
遇上兩個長相相像的男子當然是一個戲劇包裝,不可能在現實中發生,但當中描寫的卻是一種細膩的感情狀態 ── 我們愛上的人都會有上一個人的影子。我們在每段感情關係中遇上的當然是一個又一個獨立且不同的個體,但感情關係同時是一個有著回憶、有著過去經驗的連續體,過去會影響現在,也有種說法是一個人會喜歡上具有相似特質的人。這就如朝子在電影中坦言,如果亮平不是長得很像她的前度麥,她可能不會喜歡上他。
故事給予主角朝子的難題正正在於,她如何在過去與當下交互影響裡,明辨和區分自己的感情。即是說,她喜歡上長得很像麥的亮平,會不會只是對於麥的不捨;又或說,因為有著過去的影子而愛慕,最終會不會是一場災難。故事發展不在於感情關係最終可否修成正果,或提供任何浪漫情節供觀眾消費代入,而是在於朝子如何經歷、如何選擇、如何認識和終於可以表達自我。這一出發點,或許正是女性電影跟一般愛情電影的不同之處。
愛情的高速公路
電影中,朝子被描繪成不太會表達自己的女性,這種內斂,或許跟社會不太鼓勵女性表達和發展自己的父權文化有關。一個不被鼓勵表達自己的人,自然對一己的自我陌生。
就如電影其中一場,朝子在東京的室友瑪雅邀請亮平和他的同事耕介到訪,瑪雅為她的劇場演出跟耕介爭吵起來,場面調度上,身處廚房的朝子是畫面裡站在最後一排、最小的、被隔離開來的那一個人。與此同時,這場戲也是朝子少數敢於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她反駁耕介對瑪雅的表演的否定,說自己的確為瑪雅的表演而感動,因為自己無法做到。這或多或少表明了朝子的複雜心境,她絕非無話可說,但要站出來表達和成為自己,她無法輕易做到,她羨慕別人可以做到。
瑪雅和耕介都是敢於表達自己、坦誠相對的人,或許亦因此在感情上較為順利。一個不太會表達自己的人會順利嗎?或許都可以,只要不去觸碰內裡的暗湧。電影裡屢次出現的長途車程,正正就是朝子這種心理狀態的具體化身。在跟亮平一同到仙台協助地震災民,乃至後來麥再次出現的私奔之旅,都出現了相同的長途車情節,相同的高速公路大橋,朝子一樣坐在副駕駛座,平穩入睡,相信車輛會帶她到遠方,然後她醒來,總是問那句「離開高速公路了嗎?」。分別是,亮平領她回家,麥則領她中途停在一個甚麼都不是的地方,一樣率性。
長途車某程度上是朝子對於感情關係的寄托和委身,放心把自己交托給一個人,她可以安然入睡。這或許也是主流文化給予女性的愛情允諾,只管把自己交托出去,一切可以平穩發展。朝子最初對麥一見鍾情,後來在大地震的惶恐時刻與亮平相擁,出於激情也好,出於感激也好,她的愛情是夢是忘我是高速公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她永遠是那個坐在副駕駛座的人,無須獨自面對自己。
夢醒難分
睡和醒,是《睡著吻別》的核心意象。在後來跟麥的私奔之旅上,朝子自道,她覺得跟亮平的多年感情像是一個甜蜜的夢,以為自己變得成熟了,現在她終於醒來,原來一切都沒有變。她可能沒想過,自己始終沒能放下對麥的感情,現在知道了,便是醒來。
但怎樣才算是醒?怎樣才知道自己不在夢裡?這種充滿懷疑論色彩的問題,似乎不易回答。朝子是否始終愛著麥而錯把亮平當成了前度的替補?是否因為失去了一段感情所以透過另一個人來填滿?如果她愛麥,她是否也愛亮平?愛情曾經是非理性的傾心和寄托,以為愛可以一直愛下去,副駕駛座的位置可以永恆不變,高速公路一直伸延到遠方,只管追隨。但到頭來,這個「愛」的概念原來才是最大的那場夢,坐在副駕駛座的自己終究無法引領方向,不知道下次醒來又會身在何方。自己的不由自主是因為始終沒有好好把握「自己」。
電影中,岡崎太太總是提到一個年青時的愛情故事,關於她一個人在清晨坐新幹線到東京,只為跟情人吃一頓早餐。乍聽之下好像一個浪漫故事,但後來岡崎太太偷偷跟朝子說,這位情人原來不是後來的丈夫,也即是說,她亦曾忘我地深深愛過一個人,記憶夠她回味,只是他不是後來那個。
所以岡崎太太不再愛那位曾經的情人了?朝子最後捨麥而去,是因為她不再愛他,或不夠愛他了嗎?可能不是。《睡著吻別》把朝子引領到愛上兩個長相相像的男子這個戲劇包裝,讓兩段愛重疊,讓她在兩段關係中猶豫和困惑,就是為了最後這個答案 ── 其實愛情沒有the one and the only one,在所有經歷的最後,不過是妳的選擇。或許妳不是不愛了,那份愛曾經使妳困苦,曾經令妳犯錯,但妳最後願意去選擇,願意離開那個副駕駛座,離開那輛車,願意成為妳自己,妳才終於醒來,願意背負自己。
終於,電影裡最後一次長途車程,朝子一個人乘車到大阪找回亮平,即使她犯下難以彌補的錯失。她選擇,所以她背負。她對亮平說:「我不會再依賴你了。」這一刻,她才在愛情中真正成長,完成了親密關係中的個體化。
女性的情慾實踐
有一種對電影的觀感是,電影情節其實是朝子在壞男人與好男人之間選擇,一個情人一個丈夫,所謂典型的感情兩難。這種說法,都對,都不對。
這套說辭,最終都只會落到男人的較勁和典型化上,矮化了電影裡的女性心境變化和情感上的主導,乃至自我的發展;而後者才是《睡著吻別》作為女性電影的核心所在。而且這套這辭其實也在典型化女性的情慾態度,暗示女性最終或只能二選其一,把情慾的多元實踐簡化成試卷裡的選擇題。
的確,麥和亮平飾演著兩個性格各走兩極的男子,一個風流率性一個溫柔厚實,似乎暗示著兩種對親密關係的慾望投射。然而,電影結局亮平和朝子一同看著原先的新居旁的那道河流,亮平說原來它骯髒,朝子卻說它美麗,在在說明了最後兩人在心態上的分野,也是電影想要提出的對於愛情的省思。如果那道河流是一個愛情的比喻,經歷過朝子的私奔,亮平看見的是愛情的不純,是一種美夢的破裂;而朝子則自愛情的成長中前來,不只對愛情有更深的體認,最重要的是她不把愛簡化為一種「不由自主」,而是有所錯失,有所選擇,從中體現人的主體意志。
回到根本,為何朝子最初害怕跟亮平提及她和麥的往事,以至麥其實是她喜歡上亮平的其中一個原因?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在父權制的一夫一妻文化裡,如果兩人的感情牽涉了第三個人,多多少少貶抑了男人對女人的絕對擁有權。《睡著吻別》以一種奇特的三角關係(亮平長得像麥),挑戰朝子與亮平之間的親密關係。雖然電影中段朝子曾經向亮平坦誠此事,而亮平以一貫的體貼態度輕輕帶過,但最後還是以朝子必須面對心魔的方式,把這個感情關係的震撼炸開來。
這樣說並非以情慾實踐的原因為朝子對亮平造成的傷害開脫,實際上朝子亦知道傷害或已不可挽回,電影的結局也沒有表明兩人到底和好還是從此分別(亮平跟朝子說,可能一輩子都無法原諒她。朝子只點頭回應:嗯。)。但這段三角關係中,真正從愛情的「夢」中醒來的,可能就只得從兩份愛中認清了自己的朝子。而最不自由的,其實是表面看來隨心所欲,但實際上只是走馬看花,無法跟任何人亦無法跟自己建立真實關係的麥。
作為女性電影
如果要為《睡著吻別》的感情觀給出一個理想答案,或許就是岡崎太太。她不把常常唸在嘴邊的熱戀故事視為對婚姻的不忠,反而從容地跟朝子坦白自己也曾深深愛過另一個人,而且視這份愛為自己的驕傲。擁有不同的愛,又可以從中指明一個人,這顯示濱口龍介的電影世界裡,女人在愛情中游刃有餘的可能。正如台灣性別研究學者何春蕤在《豪爽女人》裡所言:「她們最討厭的是那些拚命想用一生的承諾綑住她們的行動的純情男子,那些想要她停駐下來僵滯一生的男人。」
誠如《偶然與想像》的三個短片故事,女人可以是出過軌又能放下對前度的執著的女人(《魔法》),可以是看似一無所有但以一個意外的吻誘惑曾是性伴的男子的女人(《門常開》),亦可以是過上婚姻生活但跟另一個陌生女子一同面對往日遺憾的女人(《再一次》)。女性電影跟一般的愛情電影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戲劇發展不限於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浪漫互動情定終生happy ever after,它訴說的是女性在其中遇上的困頓和疑惑,不同的嘗試和失敗,正正因為失敗,使我們看到當中的複雜性,以至現實中各種不同的可能。感情關係的結果或許不是電影的重心,而是在過程中,看一個人如何掙扎。
《睡著吻別》裡,朝子最後說骯髒的河流很美,正正體現了這種在嘗試和失敗中面對自己的精神,也是導演濱口龍介在幾部電影裡細膩描繪的女性處境。把《睡著吻別》簡化成女人投奔好男人的故事無疑是捉錯用事,因為最後的答案不在別人身上,而在那幕朝子凝視大海的特寫鏡頭裡,她第一次看見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