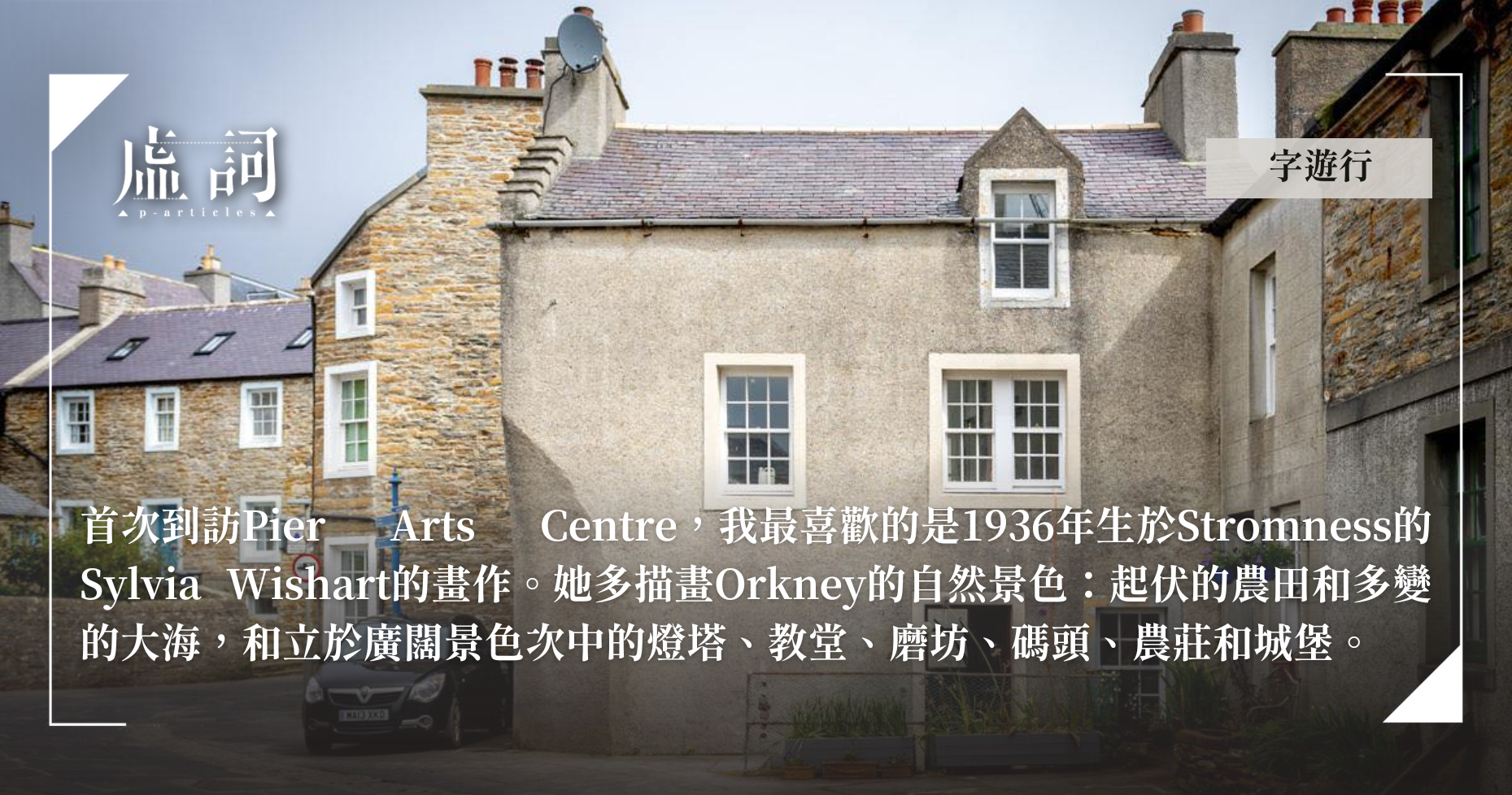黃嘉瀛與「島島共鳴」遠赴蘇格蘭奧克尼群島,當地面積僅約香港一半,多年來卻盛產藝術家,古語有云:「只要你輕刮地面,考古文物就會浮現。」他們參觀最北海岸上的美術館「Pier Arts Centre」,最令人神往的是美術館並不是由財閥巨擘或是政府主導設立,而是由反法西斯、反越戰的作家Margaret Gardiner和藝術家朋友們一起建立,內裡收藏大量現代繪畫和雕塑作品,被認為是英國20世紀藝街最優秀的收藏之一,黃嘉瀛分享其中最喜歡的是Sylvia Wishart的田野景觀畫。 (閱讀更多)
【字遊行.巴黎】持手杖寫人間喜劇
惟得今年夏天遊走於巴黎的巴爾扎克故居紀念館,書房裡的扶手椅與寫字桌並不登對,承載他身軀的背墊和坐墊繡有華麗的花飾,伏案的書桌卻蓬頭垢面,彷彿背負着浮華的花都綺夢,面對的卻是貧瘠得可憐的人生;另一間房盡是巴爾扎克改動過的手稿和排版稿,他的認真成就了可讀性高的文本,讓讀者得益,卻造成自己的財政損失;陳列室擺放著那支名杖,金色旋紐鑲滿青綠色的小花,成為他撰寫《人間喜劇》的寫作靈感。 (閱讀更多)
【字遊行.法蘭克福】歌德作為賴特的肖像
場景是人來人往的法蘭克福機場,旅客頂多把這裏視作憩腳站,最有興趣還是購物和填飽空肚,突然出現這尊高大威武的人像,穿著另一世紀的服裝,彷彿時空倒錯。歌德的雕塑如山般屹立不倒,冷眼看底下桌椅的人群聚了又散,有人閤上平板電腦,也懶得開口與手提電話交談,食指猛敲塑料套,也不是發送文字,拍一張眼前的照片,上傳到Instagram,面對愈來愈先進而又原始的資訊,不知歌德有什麼高見? (閱讀更多)
【字遊行.倫敦/巴黎】賞墳
字遊行 | by 廖子豐 | 2024-03-27
廖子豐當過導賞員,亦是導賞團常客,特別是墳場和死亡相關的導賞。近年他參加了英國倫敦海格特墓地導賞團(Highgate Cemetery Walking Tour)和法國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Walking Tour),分別令他對生死和導賞都有所反思。同樣是當地最有名的墳場,但導賞員的選材和講解帶給他兩個截然不同的感受。參加導賞團的時候,觀賞景點以外,其實導賞也是一門藝術,導的,可以是社區,可以是概念,可以是種生活態度。 (閱讀更多)
【字遊行.阿姆斯特丹】借銀燈照荷蘭影像
眾說紛紜可以令人一時迷惘,今次旅遊倒遇到一個例子,來到阿姆斯特丹,眼睛電影館告訴我,西洋鏡由英國數理學家威廉.喬治.霍納發明,分明記得前天在里斯本的青少年電影館,文字顯示西洋鏡的始創人是奧地利科學家西蒙.馮.斯坦普費爾,手頭上沒有百科全書可以翻查,一時又不方便上網叩問《維基百科》,難免興起「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慨嘆,繼續走下去,對眼睛電影館的資料也有點存疑。公平起見,常設展覽「廣角鏡」倒是經過精心設計,縷述電影史前史,資料旁邊都有儀器示範,桌面的數碼熒幕又詳細解釋器材的結構,另外「捕影網」縱容觀眾追蹤電影,豆莢廂座讓觀眾看過經典片段後參加無獎競猜遊戲,綠幕容許遊人自拍後收入手翻書,寓教育於娛樂,既然踏在荷蘭土壤,不如借眼睛電影館作銀燈,一照荷蘭電影的風采。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