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樹劉以鬯:創造的象徵

未命名-2.jpg
凌晨時分的編輯部本來瘋狂——收到劉以鬯先生逝世的消息時,各人當下一起斂了笑容,各自散開去求證、走近書架找書、爬網絡資料。到兩點多由黃淑嫻臉書證實消息,年輕編輯說她手心全是汗,我把原來放上書架的天地《劉以鬯卷》重又拿出來。這就是歷史時刻的感覺,即便是慘然的。三點後復又大雨,不免充滿象徵。
雖然劉以鬯先生慷慨擔任香港文學館顧問多年,但我並不直接認識劉以鬯先生本人,即使年前他接連獲獎、有紀錄片上映之時,我總是不在場;想去認識,又怕打攪,終是等時間來懲罰我。重要的文藝大師,往往遙不可及,但有些作家,你覺得與他非常近,好像他就活在你身邊,劉以鬯就是這樣的作家。所以失去劉以鬯,是一種普遍的失去。是需要做些甚麼去回應的震撼程度。
從作品親近劉以鬯
我是大專兼職漂流講師,常在創作和閱讀的課上教《酒徒》及《對倒》。那些都是非文學專業的學生,部份甚至很不喜歡讀書;於是我更努力地講,口沫橫飛玩魔術跳火圈一般,讓他們覺得劉先生是個有趣而親近的人,《酒徒》、《對倒》是好的作品,香港文學不後於人,就很快樂,卑微而真實。
與劉以鬯的親近是內在的與外在的,而文學閱讀與創作是必經的中介。《酒徒》號稱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將「意識流」這種現代主義技法與香港彈丸小地的社會現實結合在一起,記下了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中文人的痛苦掙扎,成為香港永不褪色的社會寓言。本擁有高尚理想和傑出文學才華的酒徒們,只能賣文維生,寫武俠小說和色情小說這類大眾商品,理想與現實傾軋不止:「不喝酒,現實會好似一百個醜陋的老嫗終日喋喋不休。」無論是文學青年還是一般大眾,紅顏還是老人,都不能了解他、撫慰他。但我認為,《酒徒》的訊息雖是沉溺的,酒徒們或者被現實打敗、靠酒精渡日——但酒的世界褪去世俗常規,一如意識流的世界打破日常溝通語言之常規,如此便在現實維度以外,闢出內心與意識的真實維度。此為藝術創造的勝利,內心超越現實的勝利,語言與意象的勝利。
劉以鬯常寫香港的城巿景象、常人生活,這也是讓我們覺得和他很親近的原因。看過不少南來作家文章會有概念先行的故鄉、與概念先行的客地香港;劉以鬯先生不是這樣的,他筆下是鮮活可感的香港,近到是立足於裡面生活,又有一個客觀一點、抽離一點的外來者觀察距離。《對倒》中以上海來港老人淳于白及香港少女阿杏的平行對接,一條共同的彌敦道,分殊的世界,因對比而產生意義。裡面寫到香港城巿面貌、樓巿金巿之泡沫、生活節奏之急速變幻,至今亦覺適切,讓我們以另一角度了悟所謂永恒。傳說劉以鬯先生時常在餐廳聽鄰桌講話,這與他小說如《島與半島》中大量直接引語的特徵相通,我想像這類所謂「都巿感性」的寫法,乃如將自己浸入都巿現場,完整的吸收,又要讓自己保持中空,讓各種聲音和風景穿過身體。
以前唸書時大專院校裡不多香港文學課,我認識劉以鬯往往是在創作課上,於是印象很深是他追求敘事上的創新。其中我特別喜歡的是〈動亂〉一篇,以物的角度寫六七暴動,多個角度分成十餘節,自白語氣淡漠僅足為證詞,證明亂事是有發生,而對傷害與破損的不滿,是借物品之口低調說出。如果敘事角度是像畫框般圈出著眼描述的範圍,則劉以鬯在選擇方面實是大刀闊斧;種種隱而不發,反讓我們揣想歷史缺失的拼圖。而不少讀者表示喜歡劉以鬯的短篇,就是喜歡在他的風格敘事中重組事件,享受知性的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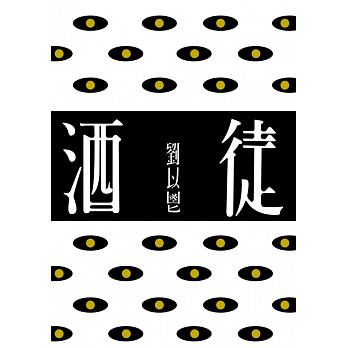

副刊的戰鬥,文人的尊嚴
劉以鬯先生讓我們覺得親近,很大程度上亦因也斯先生常談劉以鬯先生任職副刊編輯時的風格(據說是滬派副刊風格):勇於求新,要最創新的風格,時常提拔文學後進,像西西《我城》在《快報》連載,都是劉先生一力促成,在各種流水專欄中尋一角棲身——被老闆發現了,埋怨這不夠巿場,便收埋幾日,等老闆忘了,重又復載。這種柔軟與機靈,曾庇蔭過多少作家與文學作品。這是我輩文學編輯之典範。我是幸運,少年時常有前輩眷顧縱容才得發表機會,我想像他們都是參照劉以鬯先生開放求新的範兒,讓我得了遮蔭乘涼;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這樣的事。
為了讓學生覺得劉以鬯親近,我常引用《蘋果日報》訪問的「雲吞麵算式」:三毫子一碗雲吞麵,一千字稿費等於三十碗雲吞麵;六十至七十年代報業發展最高峰時,劉以鬯一天為十三間報館另加定期與不定期的雜誌稿約寫稿,以每稿一千字計,每天一萬三千字,一年總超過三百六十萬字。一千字連載小說,最快半小時寫完,一萬三千字就是差不多七小時,這是不少小說家共同的工作規律時數。「當時每間報館每月稿費在三百元上下,月入三千多元至四千元,一年下來,怕已經能賺到五十年代一層樓的價值。夫婦最終於七十年代尾,以十多萬元一次過付款方式購入太古城樓花,六百呎實用面積單位,居住至今。」再引述劉先生說「係做得辛苦,但無捱過窮」,學生聞之莫不對文人肅然起敬。勞動光榮。
我從2004年開始在報章寫稿,當時也的確與三十碗雲吞麵相近,只是後來稿費不漲反跌,雲吞麵倒是愈來愈貴,貴過雲吞麵的東西也太多。《酒徒》中曾談到香港文學發展為何受限,酒徒舉出八點:一,作家生活不安定;二、一般讀者的欣賞水平不夠高;三、當局拿不出辦法保障作家的權益;四、奸商盜印的風氣不減,使作家不肯從事艱辛的工作(按這點可與網絡的影響相較);五、有遠見的出版家太少;六、客觀情勢缺乏鼓勵性;七、沒有真正的書評家;八、稿費與版稅太低。判斷分析至今仍不過時,一針見血,見解不凡,劉以鬯先生最令人心折原是這些地方。
與學生講《酒徒》的辛酸,他們覺得這完全寫實,根本不用解釋,難的倒是要拉開距離,讓他們明白藝術如何勝過現實:文學的勝利不在於作家在現實中獲得多大的利益或榮耀,而在於語言的抽象世界,凌駕於現實之上,開闢新的感受維度,提煉意志原則。香港政府曾頒發銅紫荊勳章予劉以鬯先生,這種所謂「榮耀」遠遠無法對應劉以鬯小說世界的豐富前衛、文學觀點的凌厲高遠。前幾年獲獎的時候,劉先生說「寫作,就是要與眾不同」,我說一個九十多歲的人,仍著重「與眾不同」的藝術追求!如果此時學生面色明亮起來,我便知道多一個人懂得了,現代主義不息的創造追求。讓我們以閱讀、寫作、創造等等,每個人的一己行動,為這位香港最重要的文壇先行者,獻上墓碑的花朵。
劉以鬯紀念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