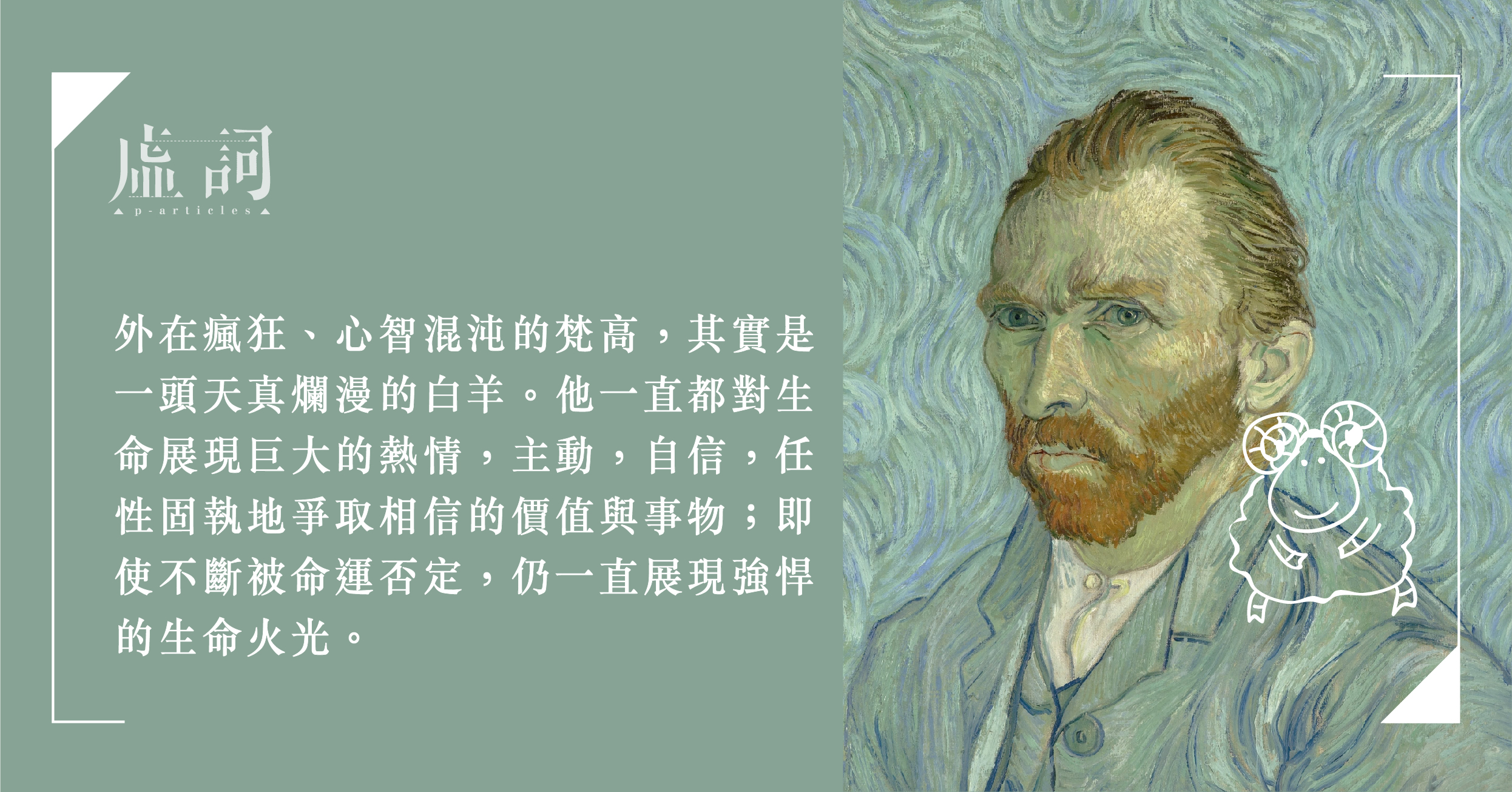《G殺》小輯
專題小輯 | by 虛詞編輯部 | 2019-04-11
《G殺》由新導演李卓斌執導,屬「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得獎作品。電影備受工業和評論界關注,榮獲金像獎六項提名,也被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年度「推薦電影」。它有港片少見的風格,如非線性敍事、細碎的蒙太奇,撕破社會虛偽的道德假面。《G殺》小輯包括台前幕後專訪:編導拍檔李卓斌、蔣仲宇、演員林善、李任燊、美指梁子賢。還有蘇苑姍和陳子雲風格各異的影評。 (閱讀更多)
【單身動物園】施濟美︰東吳莫愁,終身不嫁
單身動物園 | by Nathanael | 2019-04-10
誰是施濟美?從上海培明女子中學升讀東吳大學經濟系,施濟美不但是「東吳系女作家」的領軍人物,四十年代更與張愛玲及蘇青齊名,並稱「三大才女」。1946年,東吳大學某女學生參加《上海文化》月刊舉辦的「你最欽佩的一位作家」活動,「施濟美」三字躍然紙上(當年施濟美只有二十六歲而已!);在後來的「我最愛的一位作家」讀者調查統計中,她更名列第四,緊隨巴金、鄭振鐸及茅盾之後,可見當年她在上海文壇上的地位與名氣。 (閱讀更多)
【教育侏羅紀・伯裘書院】好老師,需要好校長
教育侏羅紀 | by 陳燕遐 | 2019-04-09
大專畢業後,我在元朗著名的私校伯裘書院教書,一教就是五年。 說伯裘「著名」,自然因為它是新界少數的私校之一,而且頗具規模,全盛時期分校多達五所,甚至擴展至九龍美孚新邨。在義務教育還只到初中的時代,它是中三評核試成績夠不上升高中又想(或家長想)繼續升學的同學僅有的出路,也是小學放牛班學生的「收容所」。因此這也是它出名的另一個原因:這些無法適應填鴨式教育的學生,來這裡還是要接受一式一樣的教學內容,與無法做太大改變的教學方法,於是各種各樣課室秩序問題、行為問題層出不窮出現。 (閱讀更多)
【教育侏羅紀・教育制度】香港學校點解搞成咁?
有些事情並不好說。香港學校搞到今日咁,校本條例並不是主因,大家都對錯了焦點。傳媒報錯了焦點,因教師團體或許有意無意轉移了焦點。是甚麼年代了?現今的機構全以分散權力、自我監察為管理模式,難道我們還希望見到「教育局」演變成獨裁的龐然怪物嗎?校本條例只是一連串更深層的結構問題下的助因。但這種深層結構無人敢說,也無人敢改變,因為迫害者和受害者都在同一系統中受惠。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