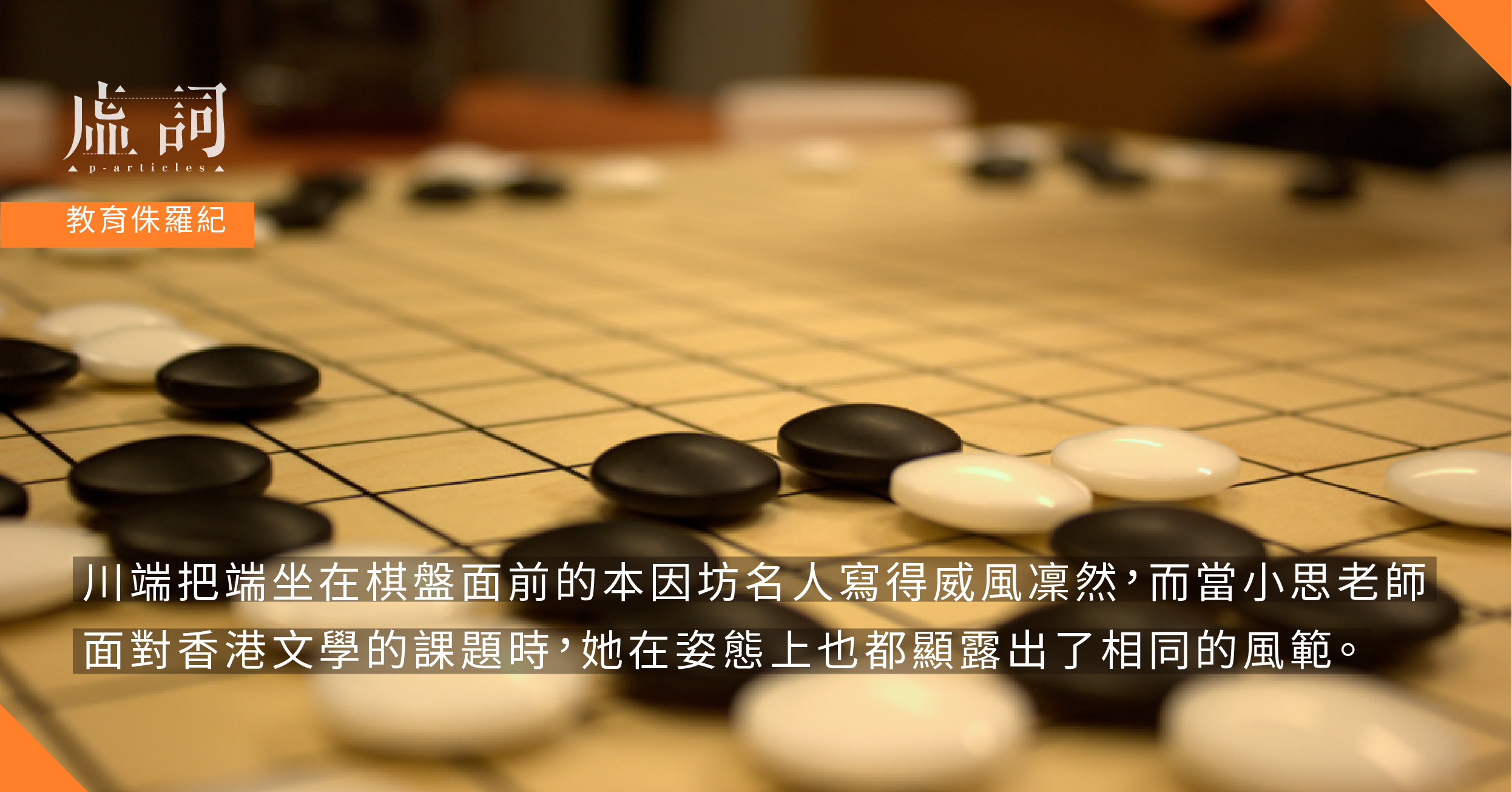【五四百年小輯】鄭振鐸︰風雷中的新探索
現象 | by 書摘 | 2019-05-04
像許多親歷過「五四」的人一樣,從一個學工科的普通學生,到一名優秀的學者和文化活動家,對於鄭振鐸而言,這迥然不同的人生選擇的轉折點,正是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中,不但完全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方向,還為以後的事業開闢了全新的天地。 (閱讀更多)
【五四百年小輯】文人學生入獄:穿梭監獄與研究所,才是最高尚的生活
現象 | by 虛詞編輯部 | 2019-05-07
因傘運入罪而坐監的,不少是學生學者;而細數在五四前後入獄之學生學者,也著實不少。百年已過,兩者的待遇與命運相照,又有何異同? (閱讀更多)
《淪落人》小輯
專題小輯 | by 虛詞編輯部 | 2019-05-04
《淪落人》係由陳果監製、新導演陳小娟自編自導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作品,自去年成為香港亞洲電影節開幕片已口碑載道。陳小娟先後勇奪電影評論學會最佳編劇大獎及金像獎新晉導演獎,而男主角黃秋生更憑飾演半身不遂的中年漢昌榮,眾望所歸第三度奪得金像獎影帝殊榮。電影以低成本溫馨小品格局衝破千五萬票房,絕對是近年不容忽視的香港電影。《淪落人》小輯包括出爐影帝黃秋生深度專訪〈黃秋生,黐乸線〉和幕後製作訪問〈黃秋生評陳小娟,李璨琛講黃秋生〉、兼有由廖偉棠、盧勁池和李顥謙撰寫的三篇角度取態各異的影評。 (閱讀更多)
【教育侏羅紀・公開試】沒事了,考完了
最後一日考試,相熟的朋友即興去吃飯,我居然拒絕了。沒有原因,也沒有人陪我吃飯,我就自己一個買了大家樂外賣回家,一個人吃。考試完結,本來是普世歡騰的事,我卻提不起勁,仍然活在那個頹喪的世界。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