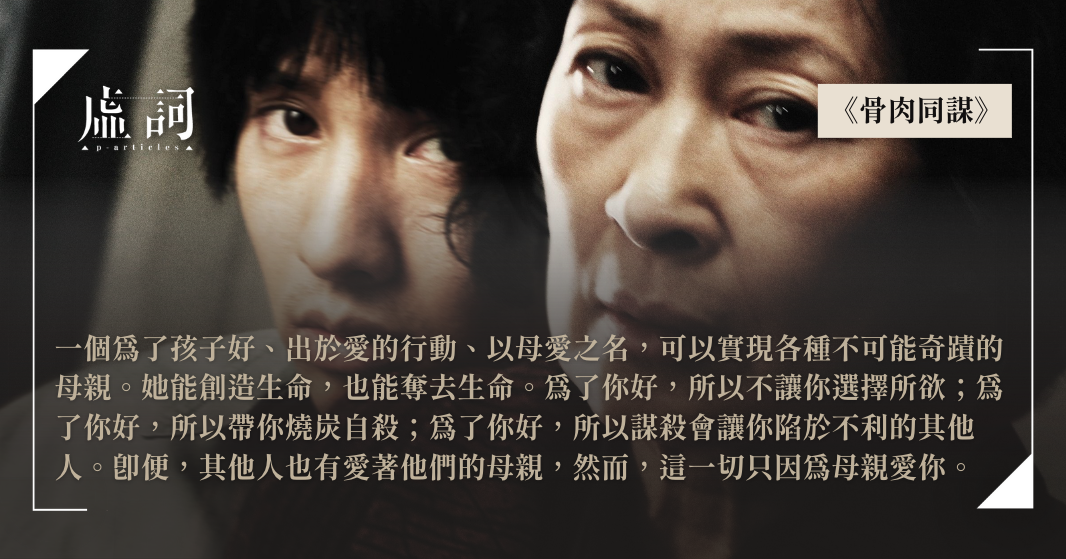在豹眼中相逢:觀萬瑪才旦《雪豹》
影評 | by 小煬 | 2024-04-10
小煬評已故藏族導演萬瑪才旦的遺作《雪豹》反其道而行,以豹眼窺人,以動物視點揭開人類社會的假面,照見人無法自視的盲點。《雪豹》的故事由雪豹與小喇嘛的三次相遇串連,雪豹作為本能與人慾的化身,在相遇中展現出不同樣貌,但雪豹依舊是同一頭雪豹,變了的是人和時代。《雪豹》滿載萬瑪才旦對於藏地的深情厚愛,但同時呈現出時代性,藏地的故事,也是他方的故事,觀眾會發現藏人和我們一樣,「一樣經受著時代衝擊,一樣帶著焦灼與期待。」 (閱讀更多)
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畫繢Netflix《3體》的雜色世界
Netflix的《3體》甫上架,愛國網民口誅筆伐劇集如何渲染文革,當中不無帶有政治和國族性的爭議。江俊豪由此評價「失去原著韻味」和「中國人不配」的批評是否屬實,從文革在劇情上的功能說起,檢視Netflix版有否刻意渲染和醜化,並依據文本的核心理論「宇宙社會學公理」比對,發現《三體》所著眼的是人類整體值不值得被拯救,亦未見「發達的中國」成為普世救主的依據,反而看見劉慈欣秉持著一套跨國族的政制觀。江俊豪所擔心的是,Netflix版在顧全大眾的觀賞意欲下,要對多個重大議題避而不談,恐怕淪為另一部純粹娛樂的地球反抗外星人侵略的俗套劇。 (閱讀更多)
忘了,忘不了:《無痛失戀》與愛的輪迴
影評 | by 黃紀真 | 2024-03-26
失戀時最常聽見的話,不外乎「忘了吧」;忘了那個人,忘了那段時光,彷彿就能忘掉悲傷。記憶似是痛苦的根源,就算戀愛的點滴本身極其美好,在求不得的當下,甜美頓成苦澀。然而忘記的過程總是漫長的折磨,反反覆覆,讓人在捨不得與留不住之間搖擺。如果可以一鍵刪除,把舊情人帶給你的喜怒哀樂通通忘掉,變回相遇之前無憂無愁的自己,你會按下那個按鈕嗎?沒了記憶,也就真的不愛了嗎? (閱讀更多)
從非人間的死後回到不假外求:《周處除三害》的善惡之外
雙雙從周處的典故看出陳桂林並非去惡遷善,而刑警的陳灰也超出了黑白的對立,苦苦追捕陳桂林多年,為的是社會,還是一報右眼之仇?陳桂林多番歷劫,甚至都已經入了土,仍然復活反殺,是因為一路受助於三種形式的「神」。電影的結局最終得到圓滿,在社會的層面上,正義得到伸張;在陳桂林內在層面上,他重新認同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救贖不在槍管或子彈,在自己的雙眼,在他真誠無害地落淚的那刻。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