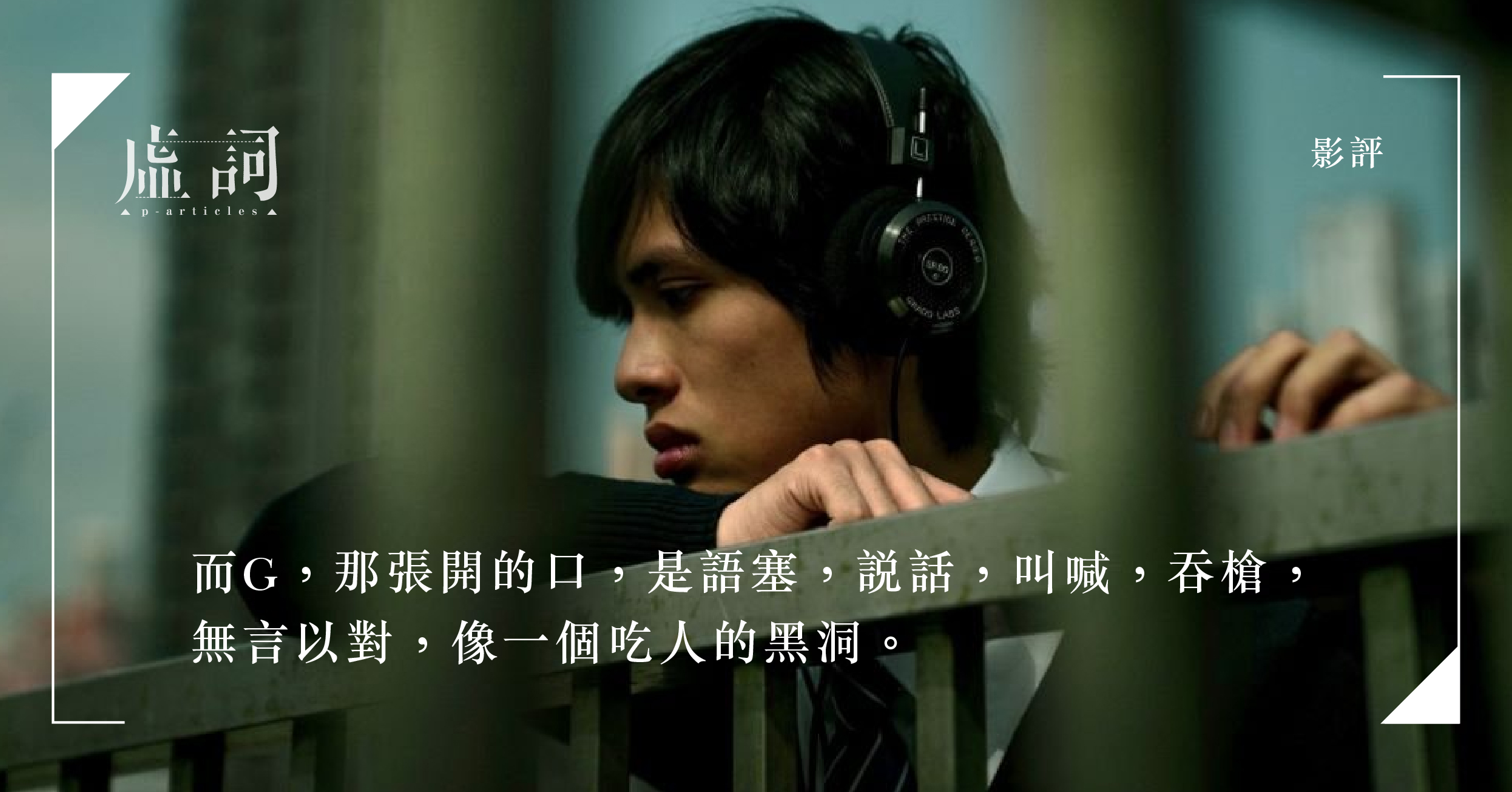《G殺》,一個張開口的人頭
首先是看到一個滾入唐樓的人頭,然後是問為什麼。
若劇情要歸納成一句話,它是關於一個死人頭的懸疑故事。
提出的問題是:社會為什麼把我們逼上絕路。
這也是我始終擺脫不掉的問題。
如何說,說什麼?一個張開口的人頭
《G殺》無疑是有野心的。它的故事框架很有生命感,以連串G字開始的詞語構築出一種氛圍,一種時代質感,去承載當下香港狀態。
斷裂、反常,當下狀態無法簡化成一個簡單現象。
G,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作為隱現的符號,以充滿空隙的語意,拆解大敘事,形構出一個虛實交錯的空間。Gravity,Gum,Gun,Gustav Klimt,Geek,Gospel,Gastric cancer……字與字之間浮現連結,像以大佈局的方式,串接、推演情節,同時擴大思考格局,連起當下香港狀態,在港產片來說,有一定新鮮感。
循此,《G殺》的重點並非查案,它要給我們的,不是關於幾個角色的故事,而是藉角色之口,映出這個世代的狀態(或感受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像G。用雨婷的話形象地說: G的輪廓,像一個人頭,一個張開口的人頭。
無力叫喊:暗黑青春
青春電影有兩條路,一是勵志陽光小清新,一是暗黑暴力殘酷。若把《G殺》放到香港的青春電影脈絡,追溯到的,當然就是暗黑青春。
十年一代,從1997《香港製造》2008《烈日當空》到2019《G殺》,青春哀歌依然繼續。雖說青春好像沒有另一種過法,必然包括夢想、成長、反抗。但現下風雲變色,躁動愈發擴張,已不能再以「無聊抵抗無聊」(《烈日當空》)。故此,青春版圖必須走出校園,融入更公共的社會議題。
比起《烈日當空》,《G殺》更接近《香港製造》。它更對準成人世界,更關乎社會政治與世代矛盾。電影以懸疑包裝,用一個死人頭導向社會議題,開宗名義已有一種變態成常態,超現實看成現實的象徵意味,宛若當下縮影。
雨婷,以泰,Don仔,故事從他們的視角分別展開,造就如複調小說一樣的眾聲(heteroglossia)。黑警父親、新移民妓女後母、斯文敗類的校長教師、政棍、道德塔利班;欺凌、卑屈、偽善、不公、踐踏、唾棄……種種被主流壓制了的「真實」在電影聚集、碰撞,見出無法含糊的社會氛圍。「底層愈臭,面層愈美」,愈是荒誕愈是蘊含對理想的幻滅,時代裂縫裡,權力無法反轉,青春無力叫喊,被壓迫得異質、殘破、碎裂。
渴:惡,疾病,隔膜
龍爺,小梅,Markus成年人都有惡的一面(除了雨婷生母),但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惡人,他們都呈現著一種困境:身不由己。龍爺人在江湖,小梅生活所逼做妓女,Markus的性壓抑。或者在暴力或欲望面前,人性都是軟弱的,一旦放下思考,便化身如鄂蘭所說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
機械化的社會秩序裡,麻木是維持運轉的重要齒輪。從社會學角度,適合社會結構的現象是常態,不適合的就是病態,若社會持續運轉,電影裡的淋病,胃癌,亞氏保加,種種疾病就是在說病態已成常態,或,我們常聽到的,新常態。性病會傳染,癌近乎絕症,亞氏保加難以溝通,病各有其象徵意義,都是由社會引發的,已經病入膏肓。
也因此,青春再容不下放肆與揮霍,也無法落入虛無,而是以一個旁觀者的姿態,抽離痛苦當下,築起重重隔膜:成績優異的雨婷因父母被同學排斥,與周遭表現疏離;以泰不理世事,自我隔離在藝術世界;Don仔有亞氏保加(選擇vs天生,兩者的隔離是種對比)。三人都以自己的方式[1]建構自己的世界,渴望的,是如《2001太空漫遊》裡靜到一粒聲都冇的世界。
弔詭的是,人總無法完全隔離自己與世界,因為渴求。
電影開首,雨婷拿著樽裝水,後也因淋病不停喝水。喝水,一方面是解生理上的渴,也是解內在的渴,渴求與人溝通。渴,疾病,隔膜,都像在說這一代青春快要窒息死亡[2]。
凡是喝過這水的人將永不感口渴
中小學讀天主教學校,很記得領聖餐時唱的,就是Markus哼唱的〈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大概婚前性行會被譴責(所以只是口交),Markus召妓,搞師生戀(但又帶李小梅回教會)。愈壓抑,愈反抗,在一片唔啱音的「主能夠,主能夠,我知祂能夠」反差下,便見出人的自欺。
若從「罪」的角度思考,Markus一邊死抱對錯界線,一邊淡化所謂道德標準。(所以折磨他的,到底是道德,還是罪惡?)掙扎如此,是偽善,亦是悲慘。在其中,「主能夠」似乎是一句空話。
不過,「為什麼我們要比基督嚴厲呢?這個世界為了要顯示它的強大,故作嚴厲,我們也就頑固地接受了它的成見。為什麼我們要和它一樣丟棄那些傷口裏流著血的靈魂呢?從這些傷口裡,像病人滲出污血一樣滲出了他們過去的罪惡。」
社會「異象」之中,無縫嵌入的一段《茶花女》或是回應。
無言:一代人死去
生命最後階段,患病的生母問:「我們最終都回到這裡,和樹一樣,和海一樣。究竟一切是為了什麼?」
「人說人生如夢,我說夢如人生,短短的一剎,你快樂你興奮……當你從夢中醒覺,你已走完了人生」。李小梅跳著舞,在歌中憶起童年的自己,一路走來的身不由己,曲終之後,人散。
這兩段話可理解為對生命虛幻的最終感悟。疾病,意外,自殺,他殺,大概經歷過死亡,我們才明白甚麼叫無可挽回——真正意義上的GG。
一代人或缺席,或死去;一代人被迫面對真相,進而成為自己。電影尾聲,以泰那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就是做好所有事」,顯得無比安定,堅決,而且青春。
一個吃人黑洞,Gravity
最後一幕,雨婷與以泰手牽手從天台躍出,然後消失在熙來攘往的繁華街道。
彷彿在電影與現實遊離。
結局開放詮釋,「我要走出我一片天,但世界要你妥協,命運被迫上錬……」片尾曲鐵樹蘭的〈一片天〉這樣唱著,我想起開首黑板上的大字,gravity。因為重力而下墜。
回到開首,如果《G殺》問的是:社會為什麼把我們逼上絕路。我希望自己能夠這樣解讀:青春是一個關口,重生或死亡,走過去,就好。
可是,我們知道,形式上的自殺掩蓋不了實質上的他殺[3]。而青春,也並非一如所願地成長。有時,我們無法越過關口,已不能再活一次。
而G,那張開的口,是語塞,說話,叫喊,吞槍,無言以對,像一個吃人的黑洞。
[1] 以藝術(《茶花女》,《異鄉人》,巴哈(Cello Suite No.1 in G Major),《2001太空漫遊》),或電腦世界隔離自己。
[2] 它甚至不是青年一代的狀態,更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集體狀態。
[3] 不僅年青的雨婷,以泰,還有上一代的李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