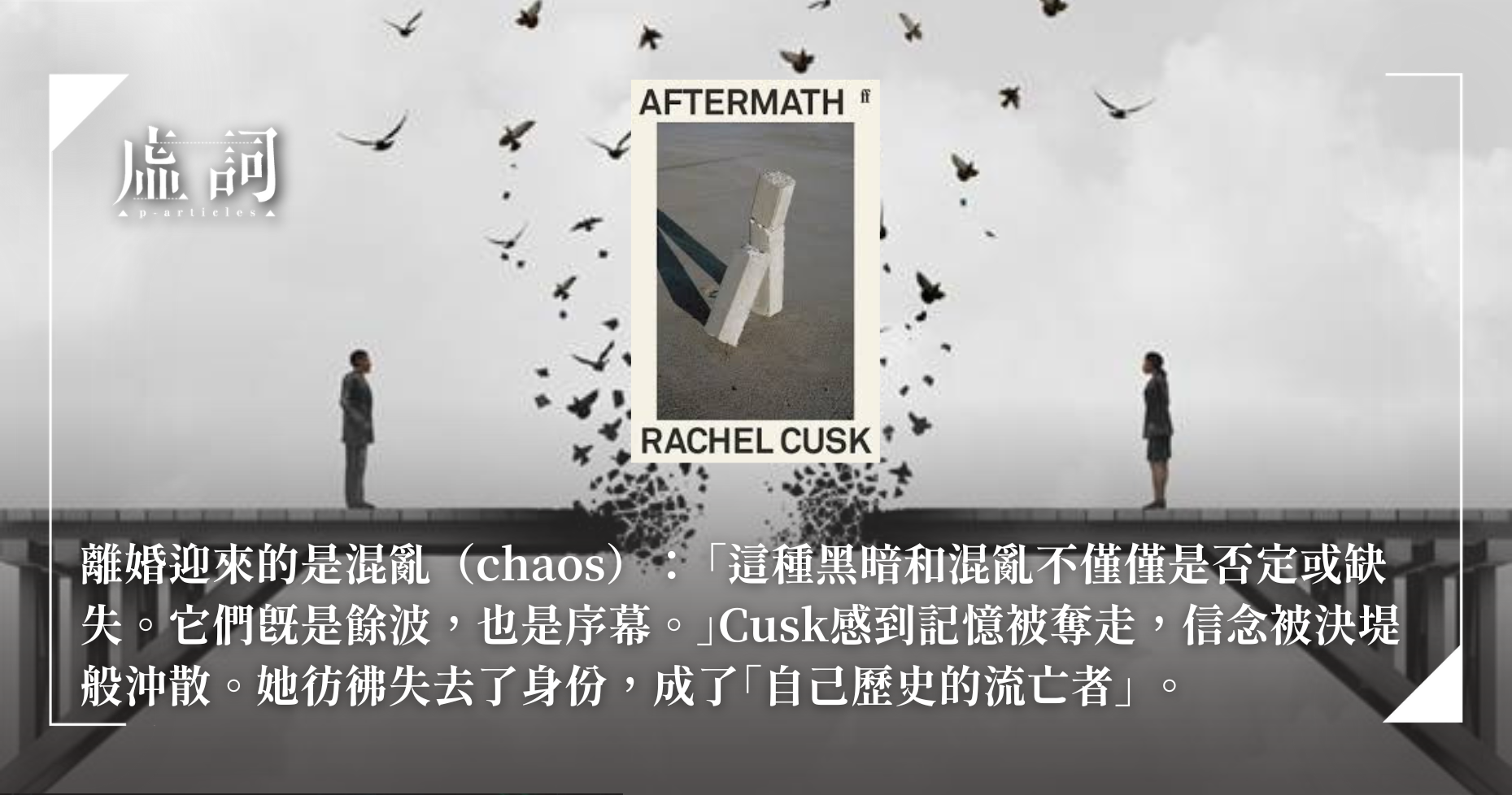餘波中的掙扎,如何拔除離婚滋生的腐朽回蕩?——讀Rachel Cusk的《Aftermath》
書評 | by 王駿業 | 2025-03-26
編按:文章標題由虛詞編輯部擬定
在一次歐遊之旅閒逛書店,筆者因一頁設計精緻的書封而認識到英藉作家Rachel Cusk。她的敘事風格冷峻而幽默,有著哲學性的洞察力,卻處處流露身為兩兒之母的溫度。《Aftermath》是Cusk個人經歷離婚的記錄,通過一連串人物相遇和對話,作品揭示出離婚對價值結構的衝擊,以及在災難餘波後活下去的可能。
婚姻破裂後,Cusk重新獲得一個局外人的凝視觀點;但今次,無知之幕已經被撕毀。「婚姻有一個公開的面孔,一種表演的面向,就像身體有皮膚一樣。」(Most marriages have a public face, an aspect of performance, like the body has its skin.) 這種「表演」是婚姻的外在形式,它「吸收混亂並將其表現為秩序。」(It absorbs disorder and manifests it as order.)
根據婚姻的秩序,生命力自然而然地湧現:孩子出生,權力積累,關於未來的各項規劃茁壯成長。這份力量的根源,不僅是一紙法律或社會契約,更是一種信念,相信家庭包含的一切都是正確和真實的。基於這份信念,人們願意在婚姻中付出、容忍,甚至原諒許多原本難以接受的事情。
當形式和信念被破壞後,關係裡本來難以接受的事情,像破繭而出的癌病,一發不可收拾。第一個故事裡,夫婦怨懟的爭吵被赤裸呈現。前夫指控她為「女權主義者」,這促使Cusk反思:假若「女權主義」可以是導致離婚的罪名,莫非她破壞了婚姻裡那套潛在的性別觀念?
婚姻的浪漫表象,隱藏著關於女性角色的隱喻:「那個既美麗又會做飯和打掃的生物 。」在傳統婚姻中,女性往往被期望承擔更多家庭責任,而男性則被視為經濟支柱。她憶起自己的父親,多年來每天規律地上班,「就像上帝一樣,父親通過缺席來表達自己;或許,對一個不在場的人心存感激更容易。」相反,母親的女性身份則成為了近乎原罪的禍根,因為她在家庭的「揮霍與苛索」,理順了男性外出工作的「天職」。
到Cusk組織家庭時,她要求兩性平等,堅持不捨棄自己的寫作事業;但她很快發現,兼顧工作的母親需要採取一種英雄式的存在模式。英雄相信自己與眾不同,但這層偽裝底下,掩蓋了她日漸積累的孤獨。孩子滲透全職母親的生活,「就像染料滲透水一樣:沒有一部分能保持原色。」孩子的勝利與失敗就是她的勝利與失敗;因為經營孩子是她的工作,她對世界的經營也透過孩子來實現。然而對丈夫而言,孩子似乎是他給妻子的替代品,一種過渡性物件(transitional object):男人利用嬰兒,作為逃離妻子的工具。他獲得自由了,因為嬰兒的誕生象徵男女之間的浪漫已經結束。女人曾經以為擁有骨肉會增進感情,現實卻事與願違:「她終究不想要一個玩偶——她想要的是一個男人,一個愛她、渴望她的男人。」
承繼自原生家庭的兩性定型太根深蒂固了,以致當她在婚姻中追求平等時,所謂「平等」也不過是定型的反色負片而已。Cusk如此總結:「我所經歷的女權主義,實際上是我父母傳遞給我的男性價值觀。」這就是婚姻的雙重面向:它既是穩定的象徵,也是壓抑的來源。
當結構崩潰時,扭曲的真相被暴露,家庭系統的秩序亦隨之瓦解。離婚迎來的是混亂(chaos):「這種黑暗和混亂不僅僅是否定或缺失。它們既是餘波,也是序幕。」她感到記憶被奪走,信念被決堤般沖散。她彷彿失去了身份,成了「自己歷史的流亡者」。
在《Tooth》這篇散文裡,Cusk用拔牙來比喻離婚的痛楚:
「起初是漫長的腐朽過程,日復一日在根部的黑暗中醞釀;然後是痛苦的誕生,像一顆種子生長並分枝,尋找意識與覺知,就像植物尋找光卻因此遮蔽了它;接著是協商,意識與痛苦協商,試圖安撫和緩解它,控制並限制它,使其鈍化,從而與之共存;然後是批評、決定、行動,確定一個日期和時間,進行拔除,讓這一切結束。但金屬與肉體接觸的那一刻,有其自身的現實。事情正在發生:現實正在被改變,因為它們無法改變自身。」
(First there was the long process of decay itself, brewing day after day in the darkness of the root; then the birth of pain, a seed that grew and branched, seeking out consciousness, awareness, like a plant seeks light and thereby blots it out; then the negotiations, consciousness negotiating with pain, trying to pacify and mollify it, to control and contain it, to dull it and hence live with it; then criticism, decision, action, a date and time decided on at which extraction would occur and the situation be brought to an end. But the contact of steel with human flesh has a reality of its own. It is happening: things are being changed, having been unable to change themselves.)
比起Kubler-Ross提出的哀傷五階段,Cusk以更切膚的第一人稱,剖析她在離婚餘波裡的掙扎。她形容,痛苦起初具備一抹自耗的魅力(consumptive glamour),帶有離經叛道、挑戰常態的意味。她曾在小鎮的酒吧裡目睹這樣一幕:一位芳華已逝的女子,臉上塗抹著厚重的妝粉,在舞池中孤獨地扭動著羸弱的四肢。她的身影與周圍的喧囂格格不入,卻正是這份格格不入,成了她對這個遺棄她的世界的控訴。剛完成離婚的時期,Cusk刻意出席朋友們的家庭聚會,彷彿從別人的慰問中能支取療癒的力量。但漸漸地,她意識到「一種巨大的寒冷,一種寂靜,像陰影一樣蔓延開來。在我意識到痛苦的嚴重性的同時,我也明白自己再也無法逃避它。」在別人的家裡,她意識到自己的赤裸;就如那個孤獨的舞者,她還誤以為那種赤裸代表自由。看穿了自己的否認心理後,她隨即進入了下一個階段——見到幸福家庭便會煩躁的抵抗期。
《Aftermath》儘管行文流暢,卻非一本易讀的書。兼負作家和母親兩個身份,Cusk對於敍述與真相的張力有着極敏感的自覺,而標題「餘波」其實已經暗示了她的選取:「I no longer have a life. It’s an afterlife; it’s all aftermath.」因為這份直視真相的勇氣,讀者沒有旁觀他人痛苦的特權,被迫一同拷問靈魂:先不論劫後重生的可能,要將自身腐朽的部分拔除,你做好準備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