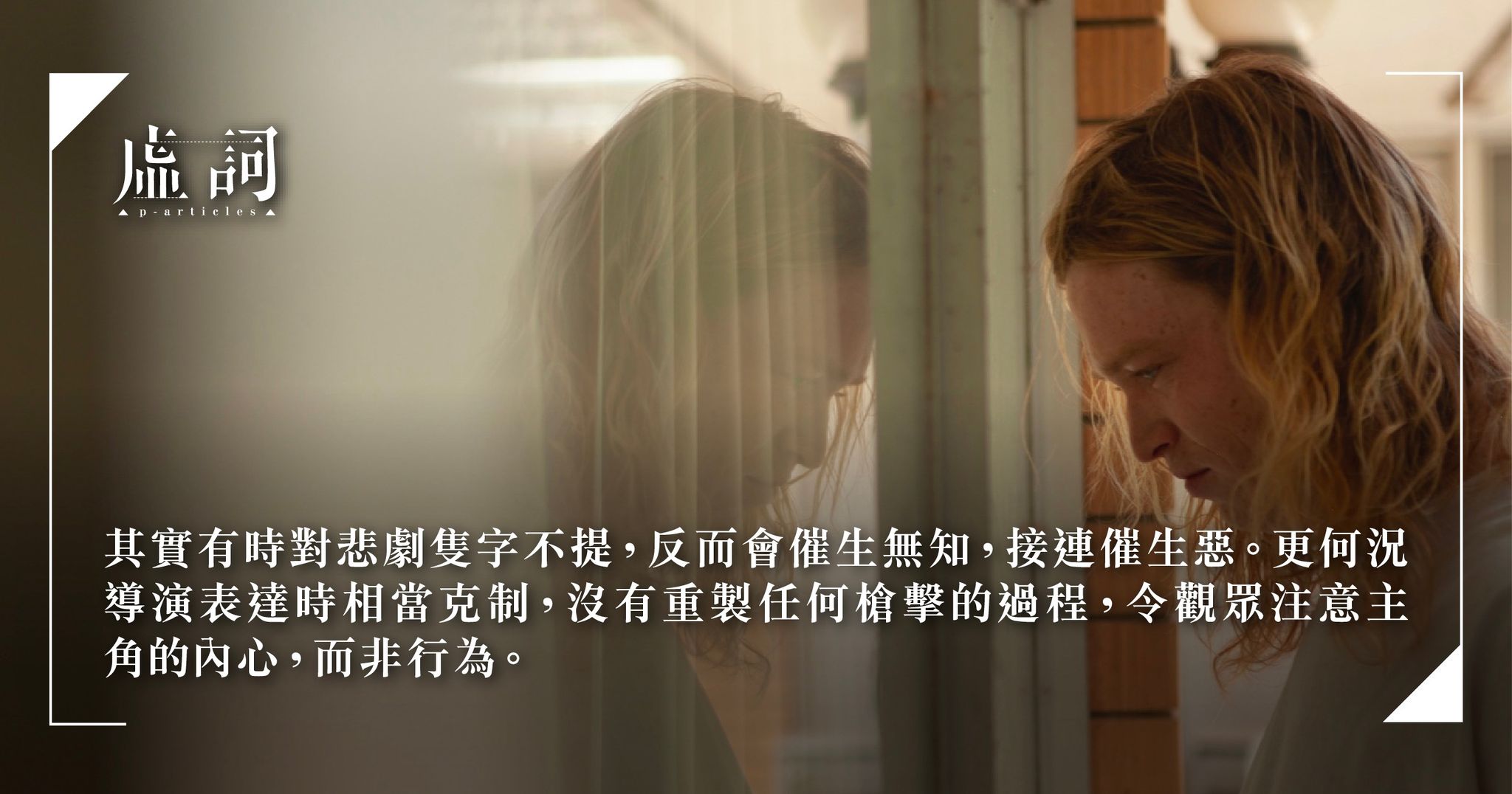《惡的序章》:無名的人,無聲之惡
影評 | by 逸文 | 2022-09-27
講起塔斯曼尼亞,你會想起甚麼?根據 Google 推薦的相關字,看來香港人會聯想起「車厘子」、「移民」、甚至「極光」。身處澳洲最南端,當地風光明媚,天氣宜人,是不少人心中的天堂。眾多相關字中,卻有一組字格格不入:「塔斯曼尼亞惡魔」。原來這是該島獨有的瀕危袋獾,亦塔斯曼尼亞的吉祥物,因為殖物者最初登陸時,在草叢中聽到牠的神秘哮聲,誤以為是惡魔的聲音,故此命名。
但對老一輩的當地人談起惡魔,他們可能聯想起那個,曾經將世外桃源變成人間煉獄的惡魔化身。
《惡的序章》(Nitram)講述一位居住塔斯曼尼亞,患有心理疾病的男子,如何成為一位無差別襲擊平民的殺人犯。然而全戲 112 分鐘卻一個暴力鏡頭都沒有,全程只描述主角的心路歷程,讓觀眾見證惡如何逐步萌生。
至於電影海報中,主角在黃昏中低着頭,凝視窗內自己的倒影。這扇窗既反映着惡,同時含蓄地影射電影的主題:因為電影標題「Nitram」的鏡像,正是「Martin」—— 1996 年發生在塔斯曼尼亞的亞瑟港槍擊案的主謀,他也是電影主角的藍本。當日他造成 35 死 23 傷,令他的名字至今仍是不少澳洲人心中不能撫平的傷口、不可提及的禁忌,所以導演 Justin Kurzel 選擇低調處理,導致全劇沒有透露主角一家中任何人的名字,只是以「Nitram」作為主角討厭的童年暱稱。縱使製作團隊處處謹慎,澳洲內部依然有不少抵制電影的聲音,令這部獲得康城電最佳男主角的電影都只能在澳洲有限度上映。
虛幻似真的 「真實犯罪紀錄片」?
這部以罪犯為題的電影,它完全放棄了主角犯罪和被捕過程,選擇集中刻劃角色的心理轉變,所以內涵更似是富文藝色彩的角色傳記。而這點上,《惡的序章》確實十分出色。由第一頓家庭晚餐,憑藉幾句閒話家常,就有效建立 Nitram 的處境:一位格格不入的男孩,生在一個扭曲的家庭。一個凡事有求必應的父親;與一個則對他充滿不屑的母親。父母二人看似南轅北轍,但都態度上放棄了 Nitram,把抗抑鬱藥塞給他就當解決問題,任由他孤立自己,從來沒有嘗試理解他。
就在這個家庭不能再沉淪時,出現一個重要角色:Helen,而她是唯一有用真名的角色。她和同樣孤獨的 Nitram 產生一段奇特的關係——既是母子、又是朋友、也像戀人。她展示出另一種與 Nitram 相處的可能性:一方面以金錢滿足他一切物慾;另一方面會訓斥他對槍枝、暴力的執迷。這些高壓懷柔並重的手段,都建基於一個前設,就是 Helen 願意理解 Nitram。
可惜,Nitram 因貪玩而釀成的一次交通意外,將 Helen 害死,加上寵愛他的父親自殺離去。經歷了雙重打擊的他繼承了 Helen 的巨額財產,卻沒有了她的制衡,真正成為了一頭破籠而出的怪物,變得暴戾、為所欲為,慢慢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然而,以上劇情只是導演和編劇的演繹,與現實是否相乎呢?
其實現實 Martin 和 Helen 的相處無人知曉。坊間認為 Martin 接近 Helen 是別有用心,為了她的遺產而佯裝一次交通意外,甚至有澳洲的犯罪紀錄片提出這個理論。相反,電影將 Martin 塑造成一個較無知的問題青年,立場較為中肯。
而導演 Justin Kurzel 受訪時指出,他們確實有盡力搜集資料,還原角色經歷,但當中一定有空白之處,而他認為這套劇不是追求百分之百的真實,應該是帶出更重要的訊息——家庭對孩童成長的影響等等。
而飾母親一角的澳洲演員 Judy Davis 都指,劇本的感覺不像是紀錄片,因為全劇只用「母親」、「父親」、「兒子」去稱呼大家,少了紀錄片的求真;反而更像一套與現實碰巧相似的戲劇,去探討惡的誕生。
平凡不過的技巧:造就喘不過氣的壓逼感
這部電影沒有特殊的運鏡或特效,看完後卻處處讓人心情難以平息,這要歸功於音效、演技和劇情鋪排。
導演經常配合劇情發展和角色心境,而倍大環境音,去烘托氣氛。就像母親不讓兒子搬進 Helen 同住時,窗外不斷響着低頻的引擎聲,如同 Nitram 的噪動不安;Nitram 在海灘衝浪時手足無措,同時海浪拍打着耳膜的聲音,使人屏息的無助感;犯案當日的鬧鐘吵過不停,響得戲院的觀眾都被逼掩耳,好像警示災難將至的鳴笛聲。大部份電影會想辦法縮小環境音,但這部電影將周遭常見的「雜音」作為一種無形的配角,與戲劇相輔相成,既自然而又添加壓逼感。
戲中還有另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聲音,就是 Nitram 低沈、急速的喘氣聲。每當他遭受重大挫折,例如與母親爭吵時;或在醫院得知 Helen 逝世時,他的喉嚨和鼻腔就會發出引擎般的共鳴聲。即使觀眾聽不到演員 Caleb Jones 的一句一話,甚至只看到他的背面,亦可透過他的哮聲而感到那種難以言諭的悲憤和掙扎。
此外,戲中有不少懸疑情節,而這點更顯導演功架。他用簡單不過的場景,平淡不過的演技,便塑造出張力十足的氣氛——兒時同學在車中不斷叫「Nitram」一字去挑釁他,Nitram 就像會隨時突襲他;傷心的 Nitram 在練槍後將獵槍朝天,鏡頭只見手雙持着槍管,令人懷疑他想吞槍自殺。當然,觀眾所猜所的事情沒有發生。導演卻將全劇的衝突放在大家意想不到的時間—— Nitram 探望虛弱的父親,上一秒還在沙發旁輕撫他的臉,下一秒就揮拳毆打着他;當 Nitram 還在餐廳在吃着水果杯,觀察四周人群時,便拿起身旁的自動機槍,扣下板機(電影立即黑幕,沒有顯示任何行兇過程)。巧合的是,以上兩幕 Nitram 動武後,鏡頭都影着母親的反應,她表現得異常冷靜,任由惡發生。全劇最後一幕更是電視播着 Nitram 作案的新聞報道,母親獨自一人坐在露台外抽煙,絲毫不動地望向遠方。
以藝術面對創傷 以客觀取代偏見
其實由開始製作時,這部電影已被不少澳洲人批抨,認為他們消費這宗慘劇,對死者不尊重,而可幸的是上映後外界普遍接納這套電影。導演也就此抒發己見,不理解大眾為何接納以紀錄片形式描述此事,但反對以藝術角度理解此事。
其實回望不少電影經典,如《舒特拉的名單》(Schindler's List),都以歷史悲劇為題,難道大眾會說這是對猶太人不敬嗎?其實有時對悲劇隻字不提,反而會催生無知,接連催生惡。更可況導演表達時相當克制,沒有重製任何槍擊的過程,令觀眾注意主角的內心,而非行為。
而導演另一處用心之處,是對精神病的處理。現實 Martin 被指患有亞亞氏保加症,但導演刻意輕描談寫地帶過這點,因為他認為 Martin 作惡的成因十分複雜,不將他的問題歸究於他的病之上。
而從中段詳細地紀錄 Nitram 買槍的經歷,到最尾那三段有關澳洲槍枝泛濫問題的文字,不難發現他認為問題更有機會出於槍枝身上。的確,這份劇本源於編劇 Shaun Grant 旅居洛杉磯的經歷,他目睹該區十日內發生兩宗槍擊,所以想探討社會對暴力的取態。
但一如導演所言,大家有沒有想過其實槍枝泛濫是否問題所在呢?或者槍枝是否泛濫呢?
雖然現時澳洲的槍械數目比二十五年前確實多了,但當中有九成三都是已經註冊,規格上亦相對低殺傷力,同時槍械牌照數目亦比二十五年前下降一半。更可況 2014 年造成 2 死的悉尼人質危機,行兇者是用 3D 打印手槍,而非傳統槍枝。
這並不代表澳洲的槍械政策完美無瑕,只是想讓大家思考時更縝密,不好將所有問題歸究於某幾個數字。其實惡就藏在每個人之中;而惡的體現,亦是大家的責任。為何槍械店的老闆可以讓一個無牌青年買下數枝半自動機槍呢?心理醫生接見他們一家時,除了例行公事的問題外,能不能主動了解更多呢?他的兒時同學可不可以善待他呢?
當所有人踏前一步,雖然未必可以消除 Martin 心中的惡,但起碼可以不用讓惡以最壞的形式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