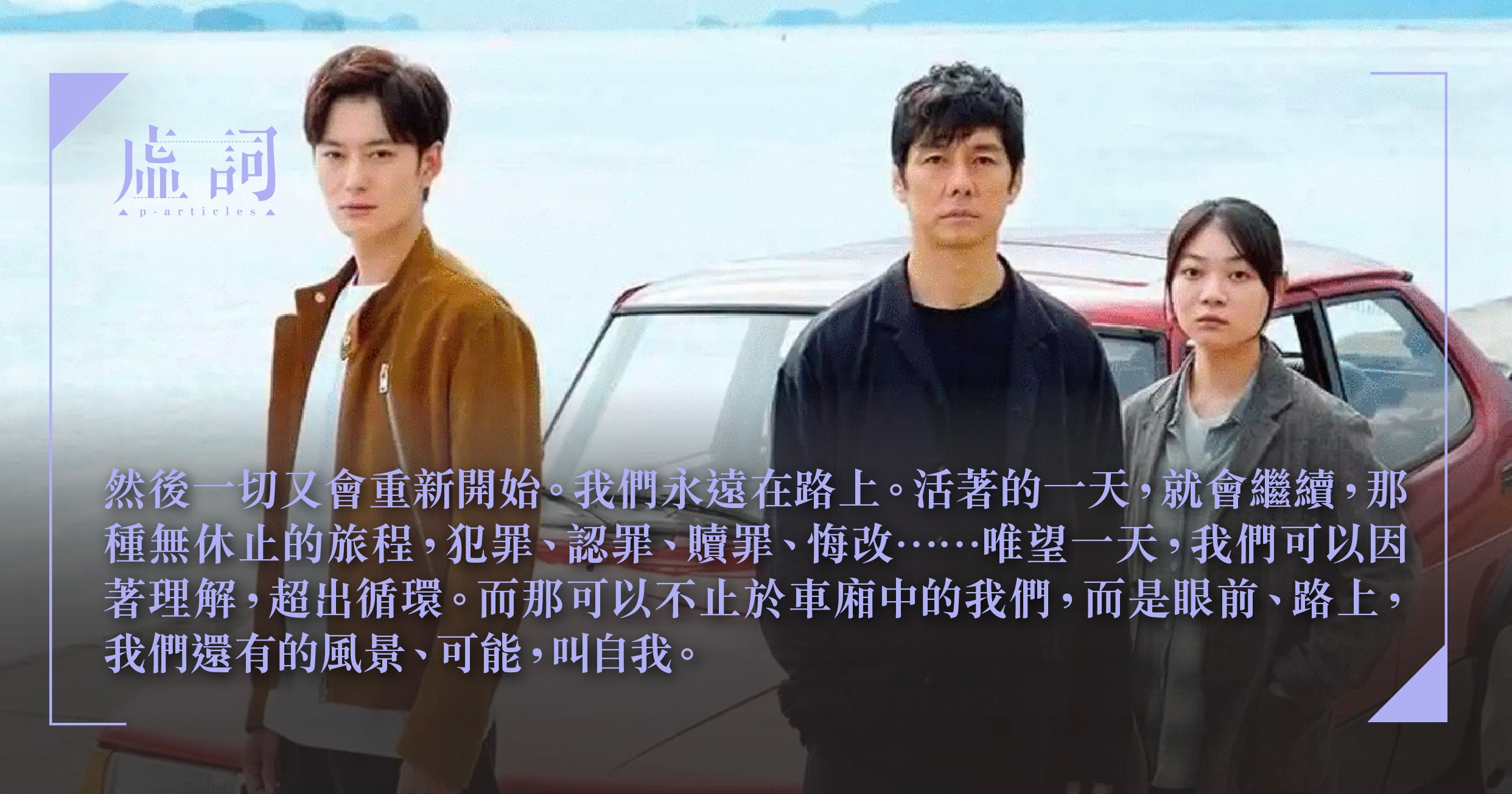《Drive My Car》Hit the Road
《Drive My Car》是那種一層旋進一層的結構,直探人心底蘊,挖開瘡疤的同時,也是在解著結。
某程度上,它都是一種失語的電影,很多事情的發生、經過、感受,都被強力的壓了在人物的底層以下,卻仿如「房間裡的大笨象」一樣,是一種不存在的存在。我們就好像一直在看著那仿似平靜的表面下,隱藏、蘊釀著的暗湧,如何找到它合乎情理的出口宣洩。是的,它必然不是一種抑壓後的爆發、或「擦槍走火」,它那冷靜、有條不紊、克制的調子,就像在等待著一個完好的契機,將一切混沌、隱忍的情感,有序的從體內釋出,近乎一種精密計算、執行後的 sophistication ,一分不多、不分不差。如像齊齊伸手到車的天窗外,逸出的煙絲,那樣的輕巧纖弱、那樣的心領神會、彼此共通;又或是那個「我們要活下去」的擁抱,恰到好處的力度。
其實兩個人之間,就是那種拿捏得宜的對偶性的存在,輕對上輕、重對上重、深對上深、沉對上沉、虛對上虛、實對上實、痛對上痛、罪咎對上罪咎、失語對上失語、釋放對上釋放。各自複雜深層的底蘊,形成了一種相互對照性的需要,才能夠互相碰觸,層層下解至最核心的真實,彼此救贖。就像是兩個人的相遇,是從一種抑壓、隱藏、不存在的狀態,到彼此交託、釋出,而尋回自己、存在的過程。短暫的車廂,是他們寄放失語的自己片刻的所在,不問什麼。有些相遇,是相遇在恰好的狀態。
戲中戲的《凡尼亞舅父》,就像一道螺絲型階梯,帶著戲中角色緩緩的旋進、深入。他要求演員一次次的反覆誦讀劇本,不帶感情,只管機械化的唸出。像在等一次次反覆唸著的句子 sink in 到身體、血脈裡頭,內化成一種自動反應的存在,看它會如何 kick in。或者說,他更是耐心地在玩著遊戲,把一些東西溶進個體裡去,然後等待發生,看看它會如何與每一個不同的個體交互,然後帶出我們自身所不自知的東西。像他說的,契訶夫的劇本、台詞,有讓人看見自己的魔力,它會帶出人內在深處的真實。而演員是以這一個自己,來與戲共通的。
像兩個女演員在公園試演一幕,他說有些東西在她們之間發生了,但只有她們自己知道,也只限於她們。所在說的,其實是 “be” 與 “act” 的差別,而這不單止是演出方式的不同,卻更是目的的迴異。他重視的是如何在戲裡面,找到、交出我們自己,戲,其實更是一個過程、手段,而不是終極的目的。他是在用戲,來成就人的真實,而不是用人來貼近戲。或者就是,要非真實指涉的存在,所有的戲亦都會失去意義。戲,終極就是對人生的模仿、貼近、濃縮示現,而大多數時候,是因為人意識不到真實,才會誤將戲,當作是所有的目的。歸根究底,我們為什麼需要戲,不論是導是演是看是評,是因為它貼近了一部分的自己,這樣而已,這才是我們做所有事情的意義。而不是因爲它有名。
而有趣的是,《凡尼亞舅父》的戲中戲,不單止是一道讓演員不自覺、逐漸旋進去的螺旋梯,它更是在不斷建立成型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的,把觀眾也一同拉了進去。也就是說,我們是一同的在走這一整個熟悉、內化的過程,等待它發生作用的。而什麼時候,我們會發覺自己需要它?居然是我們隨著它層層深入,到人物那些如同風暴中心的漩窩核心、風眼處被抽了真空、無聲絕對的存在時,我們發覺自己需要它——出口。
在那深不見底的所在,人物釋出了最核心內在所是後,我們發覺自己同樣需要一道階梯,去重新攀爬、拾級而上,讓我們看見盡頭的光照,是有可能灑在我們身上的。救贖。是的,像在絕處的真實裡,我們還能夠活得下去,這種近乎虛渺的信仰。扣著人在釋出陰影黑暗以後的虛軟真實,好像把自己的靈魂,也透過痛苦悄悄提昇、如一縷輕煙般的蒸發掉,順著那蜿蜒的階梯,迂迴行進上揚,從來時路,向著光。而那細細蒸發過後的平緩,彷彿溫暖的淚水劃過臉龐,撫慰著還在生的人。
「我們要活下去,我們要活下去……」嘗問如何,這無疑是給在盡處的人,最後一種人性的確立。絕處裡唯一僅有的救贖、力量。如像活下去,才是我們此生懺情悔罪的方式。We reedem ourselves along the path, as the only way possible. 如此,我們才有望去到上帝的跟前悔罪,獲得憐憫和寬恕。人啊, pity on us, humans, sinners.
我們需要救贖、重生,如像一部分的自己,已經隨之而死去。We died with our sins, right at the scene. 像美沙紀,她說知道被留在山泥塌瀉的小屋裡頭的,不單止是她母親,還是她最好的朋友。就像我們在轉身當下,深深知道,被遺留下來的,不單止是我們的恨,還有我們的愛。而有時,它們是如此難分,像一者是披著另一者的身份面目而出現。愛以恨的面目,恨以愛的面目;真實以謊言的身份,謊言又以真實的身份。Can you tell the angel from demon, or demon from angel? Lucifer, the fallen one. At times, we are just them both without even knowing and reconciling. 大地因而才會有這麼多的罪惡。
而活下去,是帶著這種全新的認知,we are them both. And knowing is the part where we can choose not to act on it?
有些時候,它只是那樣無心輕忽的存在,然後一切就發生了,甚至我們未必會知道它是如何發生的,constant ignorance;又有些時候,在事情發生的當下,我們是如此明明白白的,像一種突如其來的「現形」——那些在一瞬間被決定而發生的事、隱藏著而被辨認出的自己,隨過去每每累積而不再抑壓的時候,一瞬間變得無比合理、成立,以致它像是那樣的自然而至,每一個瞬間都能被定格、拉上慢鏡、逐格檢視的。而你在其中是明晰的,knowing that it will happen exactly the way it is. 這就是一種「命定」,也像是一種認知:我就是會如此反應,歷史的當下,沒有任何別的可能。如此,我們步向自己最深層的真實。我們需要救贖,因為我們是罪人,in the very first place.
All of us. We just come to pick ourselves up. 我們只是去認出自己來。如此,我們才得到真正的生之可能。雙重人格,都只是一種隱喻,我們一直帶著分裂的自己,去尋找出口的可能;我們隱身其下,摸索著可能存在的方式。直到一些自我不經意的逸出,我們以為那是某種自我終結、死亡的方式,但其實它指向生。全新,全生。Knowing who you really are. 而那需要我們凝視深淵的勇氣。未曾死去(經歷意義上的消亡),我們如何能真正活?
常在想,如何為《Drive My Car》譯出一個好的中文名字。它本身有著情感寄託、交出控制的意味在內,但有趣的是,隨著劇情的發展,你會發現,最後那並不存在著任何權力的高下,而是每每是一種對等。所有的承接,都是因為對等、理解而存在的,因此他們才會看見對方。這是一個互相陪伴,去走一趟自己無法的旅程。因深入自身,而給予了對方存在的空間。這個車廂中,隨著彼此的深入,就不再存在著單方面權力的高下、寄託、行使,而是一種情感的共性。那種你我皆需要一時的存在,在我們雖死猶生時。暫託。於是乎,那個齊齊在車上把手伸到天窗外、讓內裡一切隨煙絲融進夜色中的畫面,才會如此美麗。那說了一切,我們之間無須言明的一切。
如何在不存在之中尋得存在。
如像戲中一個場景,莫名的吸引到我的注意。他叫她隨意駛到她喜歡的地方,她就帶他往垃圾處理場的設施。那是她從前工作的地方。隔著一塊大玻璃,海量的垃圾無聲的被機械巨臂抓起、遷移,到另一些地方,等待被進一步處理。這個畫面,好像回應了我心中某個一直帶有的疑問:垃圾,其實去向何處?像我只是把那些已變壞了的東西,帶離自己的家門,到垃圾站,遠離我的視線範圍,但天知道,那不是終站。這這麼麼多的垃圾,我的你的他的她的,聚合起來,最終會歸向何處?在地球上的哪一個角落?不像它從此與我無關,因為我知道,它仍然會在這個地球上的某個角落,比我丟棄它的時候,更加腐爛墮落,更加令人厭惡。而自我把它丟出家門開始,我知道它就只有往下的方向,沒有別的可能。我好像看見自己,往那條不可止的道路上,墮落下去。
我想,我其實是感到親切的。它證明了我所想,一種眼見為實,它們不是就此就不存在的。它們一直一直在的,端看我們要如何處理,甚至是要看它不看。認回它,是一種暴烈的溫柔來的。A piece of shit.
And I will say, drive my car and we fucking go. To where we not know ourselves. Hit the road.
忽然之間,我想把它叫作「漂車」,在漂動的車速之中,尋回自身。唯有一種速度,教人忘卻自身的行進,而得片刻喘息;也唯有一種速度,教人認回內裡同樣正處失速的自己,而得止住。
然後一切又會重新開始。我們永遠在路上。活著的一天,就會繼續,那種無休止的旅程,犯罪、認罪、贖罪、悔改……唯望一天,我們可以因著理解,超出循環。而那可以不止於車廂中的我們,而是眼前、路上,我們還有的風景、可能,叫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