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寶兒:無盡星塵》——有所尋覓的人,不在目的而在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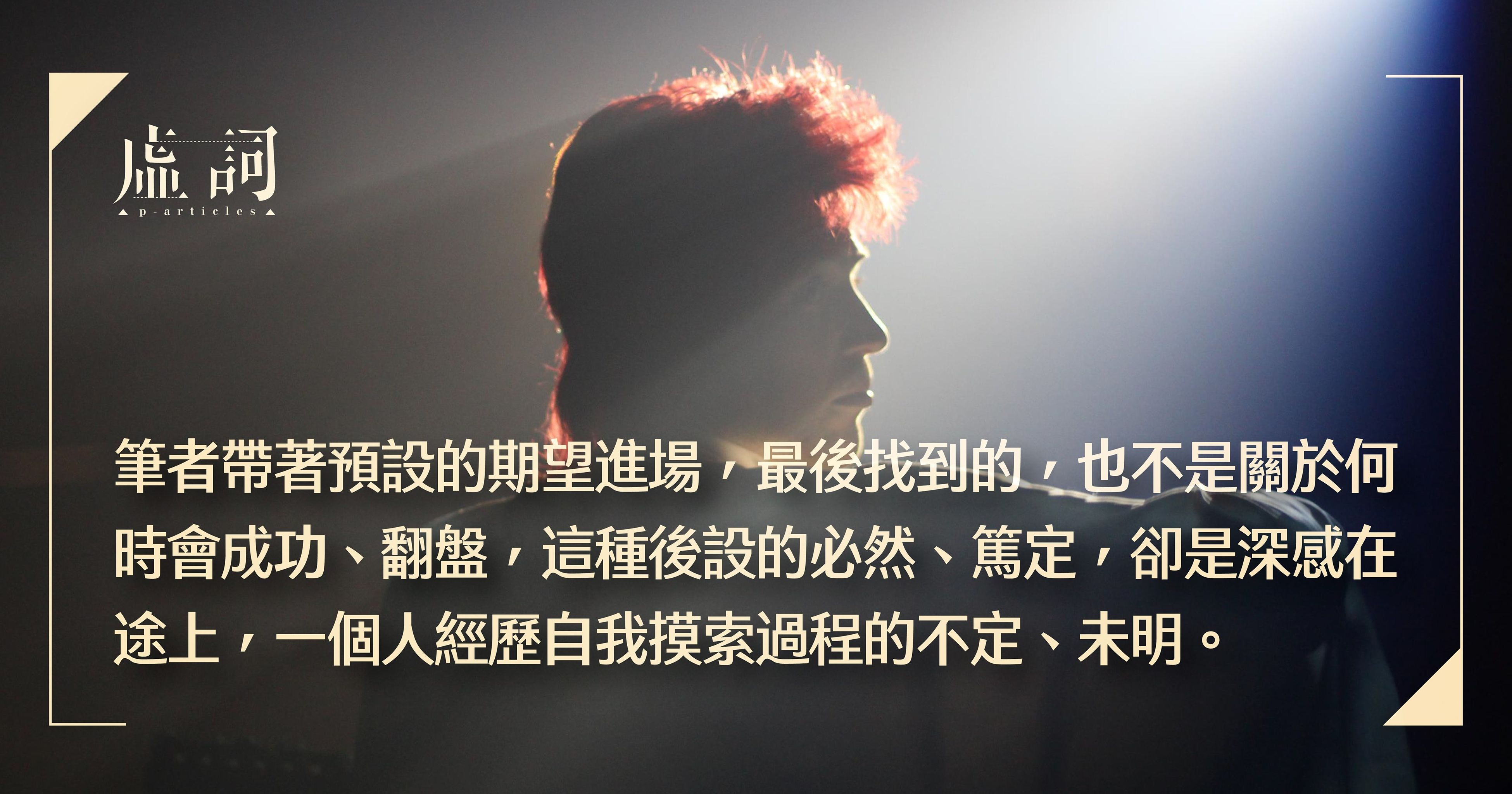
173958035_1832821456885696_4595732523687501508_n.jpg
最真實的,其實都是那些乏人認受的階段。
看trailer的一種滿足在,所有對自我的想像期望、性格中破格突出、不為人所接納、屢遭挫折跌碰的部分,好像通通都會在電影的收結裡,得到「翻盤」的可能。就像是之前跌得愈低,都只是電影鋪墊的手段,藉以反襯人物角色後來空前的成功。有多抑壓,才有多絕地反彈。看一些傳奇人物改編的故事,好像這幾乎都成了一定的方式、套路,予觀眾欲望投射的可能,但卻不是在於那些無法成為的自我,畢竟矢志追求自我存在,根本就是一件少之又少的事,大部分的人,更多都是在投射一種Wanna-be 的可能,卻不要搞錯,非關成為片中角色那樣的人物,不論其有多具顛覆、開創、啟發性,卻是在於那種搖身一變的可能──默默無聞的人,都能有望成為廣為人知、具影響力的誰的可能。Wanna be 的 be,並不實指誰,卻只是相對於nobody的somebody。Some significant one,就像人們愛看英雄電影的心理一樣,彷彿現實中如你如我般的普通平凡,亦有望透過電影所提供的短暫窗口,投射寄托一些自我的想像,藉以填補現實裡自我的無法、不能,那些深重的無力感。就如近年城中瀰漫那股「造星」的熱潮,其重點其實是在,普通人如果不具備「做星」的材料資質,仍可擁有透過參與「造星」的過程,得到一種權力欲、控制感。相似的過程,究其目的,其實同樣是為了要暗自轉移看的人自己身上會有的無力感。於是,在真正看電影之前,筆者就是帶著trailer建構的這種期望心理進場,等看一個人何時、如何「絕地翻盤」,從屢遭挫折否認忽視,到贏得世人的目光認可。尤其是片中角色所代表的,本來就是一種極其邊緣少數、備受壓抑的存在。"Misfit",如同所有極力爭取自我存在的人,與主流大眾間必然存在的矛盾分歧──如果那之間的落差不是以鴻溝去形容的話。變相,也就給予了看的人無限欲望投射空間的可能,不管自己是有多不被社會大眾所接納,姑勿論兩者的自我間可能差之甚遠。
帶著這樣的期望進場,等著看片中的人物角色何時會得遇伯樂之恩,從此展開星途人生,然後?然後,片中人物尋覓的途上,一次次所遭遇的打擊挫折,好像亦都來到看的人身上一樣:他的失望,就是我的失望;他的懷疑擺蕩,就是我的懷疑擺蕩;他的自我破碎,就是我的自我破碎。忽然好像與他同呼吸、同命運的經歷著一切。關於那些過程中自我的期許、可能。
「你要如何的述說、形容自身?你的定位是什麼?」在巡迴宣傳的途上,一個記者對他各種的怪異遊離摸不著頭腦,作出如此一問。而他一貫的施施然,好整以暇,模稜兩可的,卻始終說不出所以然來,讓對他心懷希望、想給予他一線生機的人,亦打消告退念頭。巡迴宣傳,也像是一個人能否成功、繼續的最後掙扎。那是在他推出《Space Oddity》一曲,成為一時佳話後,欲再度加推個人專輯,卻遭遇市場反應冷淡、唱片公司冷待之時。基本上,除了身邊人,就是沒人認為他的專輯能賣得出,稱得上創作,有成功的可能。就像是要為自己奮力一搏,他提出要從倫敦到美國巡迴演出去,親自爭取觀眾、市場的注意力,然而卻在簽證問題各樣情況下,演出不能,演變成個人宣傳。說是巡迴,其實也只是合計兩人一車,穿州過省這樣的彆腳;說是宣傳,也只是名不經傳,幾經辛苦鋪橋搭線,幾近挨家挨戶,找上稍具影響力的記者雜誌、民間電台,毛遂自薦的欲搏得些許宣傳版面介紹的文字。出發前,以為有著什麼盛大的場面等著自己,身邊人說著 he is gonna be the greatest hit;出發後卻只是一切不如預期的瘦削現實。自己的一切,以為是性格特色,都成了可笑而讓人大惑不解的存在,像那一襲精心預備的女裝,自己的draq,都顯得如此不倫不類,哪一頭的世界都無法靠攏。自己是什麼?那並不是一時用以宣傳定位所給的答案,卻是一路上歷經自我跌墮,自己也反覆在問、在思疑的,需要時間,長久摸索才得以成型的。
時間以外,一個人經歷再多的拒諸門外,自我定位始終得訴諸個人,而非外在。而那牽涉的,卻是人自身也無法輕易更易的,家庭、歷史的痕跡。最大的恐懼所在,也是自身最不接納的部分。有人說,聽他的創作專輯,就好像聽一個瘋子所述,精神失常的邊緣,有何價值?殊不知,這也是一個人真實的爭持所在,在面對著恆常隱匿拉扯在內、蟄伏而出的恐懼、陰影。陰影,是恐懼自身所是的,家族血統所流傳的因子。Bad seed,壞種,他們這樣形容。自我的糾纏,像徘徊於壓抑迴避自身所是,與任其開枝發芽,成為不折不扣的lunatic。而所謂的自我摸索、尋覓與創作,其實就只是在這兩者間維繫著一條清醒界線的嘗試而已。Maintaining that very fine line,就像站在一扇門的中間,看到兩邊各自的所在,卻不向任何一邊傾側、傾頹,這種時刻奮力的所在。明知背後的恐懼陰影常在,而與它不失常性的共存、共處。創作的許多作品,只是在這邊緣上所開出的花。而這也因而給予了他那種疏離孤獨,無法靠攏歸屬到世間任何所在,永遠只有自己為自己所覓的半點邊緣上的存在。這世間的路註定不適合他,要存在,他只有用自己雙手開拓屬於自己的路,這樣的命。憑自己,獨立特行的人都註定如此,就是要走比別人更多的路,才會有自己的安身之處。
往後,跨國之旅黯然失敗夢碎,逼視自己的邊緣,如何撿拾自己的破碎,重構自己所在,已成後話。片中換成萬千狂迷呼喚,只消一個年份的轉換而成,像中間一切如何經過也可供省略。或許,又再如何沉澱整頓,都只是自己的過程。只是看畢至此,台上所有燈光璀璨、星途燦爛的所在,都竟覺不實虛幻,像不知道狂迷著的人到底能看見、懂得多少,角色背後尋覓、搖擺掙扎的那些過程。筆者帶著預設的期望進場,最後找到的,也不是關於何時會成功、翻盤,這種後設的必然、篤定,卻是深感在途上,一個人經歷自我摸索過程的不定、未明。但也是這種不定、未明,叫人感到無比真實,對比起萬千呼喚,沒有比這更叫人感覺到個人的存在。有所尋覓的人,大概都能懂這種心情。一個成功的答案,比不上途中無數生起的個人、自我疑問。就是到最後,看的人所尋覓的都不在目的,而盡在過程裡。
(標題為編輯所擬)
